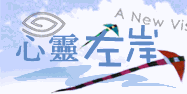 |
||
 |
每個人都是獨特的,這正是人性美好之處。世間沒有任何標準可以評量任何人,除非你自願接受標籤,或替他人貼標籤。每個人都是生命的鬥士和品嚐者,生命的發展,端視你如何自我覺察和成長。──許添盛 (摘自身心靈健康的10堂必修課) |
|
|
|

|
||
|
(二) 再往前走,山徑變窄,我得穿過兩塊座落在兩百呎深的峭壁邊的大圓石。一走過這兩塊圓石,就可聽到菲利普斯噴泉(Philips' Spring)的潺潺水聲。這個噴泉的名稱,是根據十七世紀晚期最早在此紮營的毛皮獵人而命名的。噴泉水緩緩鑿過好幾層岩石,最後開展進入寬十呎、水流悠緩的池塘中。這個池塘最早是人工挖掘而成,後人又再添加一些風景,例如在入口處栽種了幾株蘋果樹,另外擺放一些灰泥接合的石塊,用來穩固這個池塘並增加它的深度。我走向噴泉,伸手捧起一些水。當我俯身向下的時候,輕掠了一根不尋常的小樹枝。這根小樹枝繼續移動,搖搖擺擺地爬上岩石,最後鑽進一個洞裡。 水棲腹蛇!我大叫,往後退了好幾步,冷汗從我額頭冒出。現在,住在野地裡還是有相當的危險,雖然已不再像幾世紀前老菲利普斯所面臨的那種險境。那個時代,很可能某天走在路上,轉個彎,就正好撞見一頭護衛著幼獅的大美洲獅,或更糟的,是碰到一群露出三吋獠牙的野豬,如果不立刻爬到樹上,那麼這些長牙就會把你的大腿肉扯裂開來。如果這一天實在是倒楣透頂,甚至還可能遇到一位憤怒的契洛基人(Cherokee),或一位移居此地的賽米諾爾人(Seminole)。他們最不能忍受的,是在自己最喜愛的狩獵區內,不斷看到新的移居者……因此他們會想,如果把你的心臟咬下一大口,或許就能一勞永逸地阻擋白人入侵。不過,在那個時代, 所有活著的人--美國原住民和歐洲白人--都同樣必須直接面對危險,這些危機,考驗著事發當時個人的應變能力與勇氣。 我們這一代所要處理的似乎是其他的問題。這些問題比較是關於我們對人生的態度,以及掙扎在樂觀與絕望兩者間的戰役。這個時代,末日之說甚囂塵上,這類論調舉證歷歷地告訴世人:當下西方的生活方式已無法再持續下去;地球氣溫升高,恐怖主義者的軍火日益強大,森林枯萎,科技失控地發展至某種虛擬世界,驅使我們的下一代發狂,也威脅著要讓我們逐漸陷入精神渙散與漫無目的的超現實主義中。 反擊這種論調的,想當然爾是樂觀主義者,他們聲稱散播末日之說的人在歷史上比比皆是。他們認為,所有的問題,都可以用科技--也就是製造出這些危機的始作俑者--來解決,因此,人類的世界才不過剛開始要發揮潛力。 我停下腳步,再次望著這片山谷。我知道,西勒斯廷憧憬(Celestine Vision)就存在於這兩極之間。這種憧憬相信,人類可以持續成長,科技是可以人性化的,但它也認為,唯有以朝神性邁進的直覺,加上對這個世界的走向抱持樂觀的心靈看法,持續的成長與人性化的科技才有可能實現。 但有件事倒是可以肯定的。如果那些相信憧憬力量的人想要發揮影響力,那就必須從現在開始行動,因為我們正處於新千禧年的奧祕當中。新千禧年到來的事實仍令我心中充滿敬畏。 我們怎能如此幸運地活在這一刻?千禧年不只代表一個世紀、一百年的轉變,也代表了整整一千年的變化。為什麼是我們?為什麼是這一代?我有種感覺:更遼闊的答案仍待我們去發掘。 好一會兒,我在噴泉旁四處張望,心想娜塔莉也許會出現在這裡。 我確定這就是我之前感應到的:她在噴泉這裡,不過我似乎是透過某種窗口看著她。我實在不懂這隱含著什麼意義。 她家到了,但好像沒人在家。我走上深褐色呈「A」字型的前廊,使勁地敲門。無人應答。我轉頭看了一眼房屋左側,注意到那裡有些異樣。從這裡望去,有一條石頭小徑,這條小徑穿過比爾的大蔬菜園,直指向山頂上那一小片青蔥的草原。是光線變了嗎? 我抬頭看著天空,想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那一片青蔥的草原上,光線似乎起了變化,彷彿原本藏身雲後的太陽霎時露出臉來,照亮了那一塊草皮。但天上一片雲也沒有。我漫步向那片草地,發現有個小女孩坐在草地邊。她身材高,髮色烏黑,身上穿著一件藍色的足球制服。我走近時,她嚇了一大跳。 「我不是故意要嚇妳的,」我說。 有一會兒,她並不敢正視我,就像十幾歲的小女孩會出現的矜持舉動,所以我蹲到她可以平視我的高度,主動向她介紹自己。 她看著我,眼神比我預期的成熟。 「我們在這裡並未依照覺悟生活,」她說。 我大吃一驚。「什麼?」 「那些覺悟啊。我們並未身體力行。」 「什麼意思?」 她看著我,神情嚴肅。「我的意思是,我們尚未完全了解這些覺悟的意涵。還有更多是我們需要知道的。」 「不過,那並不容易……」 我就此打住,不敢相信我正被一位十四歲的小女孩這樣當面質問。剎時間,一股怒氣湧上心頭。但之後,娜塔莉笑了。她並非露齒笑,而只是略為牽動嘴角的一絲笑容,但讓她變得非常可愛。我放寬心情,坐到地上。 「我相信覺悟所言不假,」我說:「但要做到卻不容易。需要時間。」 她並未放過我。「可是現在確實有人正在貫徹執行那些覺悟的內容。」 我看了她一會兒。「在哪裡?」 「亞洲中部。崑崙山區。我在地圖上看過。」她聽起來情緒很激昂。「你一定要到那裡去。這很重要。事情有了變化。你必須現在就到那裡去。你得親眼瞧一瞧。」 她說這些話時,臉上的表情看起來就像一位四十歲的人那般成熟、權威。我使勁地眨眼,不敢相信雙眼所見。 「你一定要到那裡去,」她又說了一次。 「娜塔莉,」我說:「我不確定妳說的地方在哪裡。那是怎樣的一個地方?」 她轉移目光。 「妳說妳在地圖上看過,妳可以拿地圖來指給我看嗎?」 她忽略我的問題,看起來心不在焉。「現在……現在幾點了?」她慢慢從口中吐出字句,結結巴巴地問著。 「兩點十五分。」 「我要走了。」 「等一下,娜塔莉,妳剛說的地方,我……」 「我得和隊友碰面了,」她說:「快遲到了。」 她跨大步走開,我費勁想跟上她。「亞洲哪個地方呢?妳記不記得確切的地點?」 她回頭看我,可是在她臉上,我只看到一位十四歲小女孩滿腦子想著足球的神情。 返家後,我發現自己心煩得緊。這是怎麼一回事?我直愣愣地瞪著書桌,無法專心。後來我去散步了很久,還到溪裡游了泳,最後決定明天早上再打電話給比爾問個究竟。於是,我提早就寢。 凌晨三點左右,我被吵醒。屋內一片漆黑,唯一的亮光,是從百葉窗底縫流瀉進來的月光。我凝神傾聽,卻只聽到夜晚尋常的聲音:蟋蟀間歇的吟唱,牛蛙沿著溪邊偶爾傳來的低鳴,以及遠處狗兒低沉的吠叫聲。 我猶豫是否該起床把門鎖好,但我平常很少這麼做。我拋開這個念頭,心滿意足地重回夢鄉。我本來可以就這麼沉沉入睡,但就在快睡著時,我又四下看了看,卻注意到窗邊有些異樣。外頭的光線比先前明亮。 ──(摘自《聖境香格里拉》) 最新更新日期:90年7月12日 │看完文章後,你如有任何感想和迴響,請至回聲牆和大家分享。│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