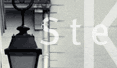|
野依良治說:「人生的百分之一百二十是化學。」一篇只有區區六頁、還曾不被採用的「不對稱合成反應」的論文,竟然讓這位酷愛相撲的日本化學家獲得2001年的諾貝爾獎……。田中耕一說:「不要受常識束縛。」這位普通的上班族(負責質譜儀應用研究的工程師,職位低於課長)是世界上首位成功測出蛋白質重量的人,竟然史無前例的以大學學歷獲得2002年諾貝爾化學獎,猶如好萊塢的《麻雀變鳳凰》在科學界上演……。
回顧過去一個世紀,我們不禁要問:是什麼使得諾貝爾獎具有今天的地位?其實,早在諾貝爾獎誕生之前,也有一些重要的國家級獎項頒發給來自不同國家的個人或團體。但是,就其全球化以及國際性的視野與使命感而言,它們都遠不及諾貝爾獎。諾貝爾的遺囑明確地寫著:「受獎人的國籍不應列入考慮」。這在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抬頭的當時,無疑是一道人文主義的閃亮訊號。的確,在諾貝爾的遺囑中,字裡行間透出的價值觀,正是他哲學觀的真實寫照。
反觀台灣,科研風氣濃厚,校園學術自由,精英密集,社會民主自由、財力充沛。我們已開始努力開發科普領域,進行提高全民科學文化素養的奠基工作。金字塔底部的工程已起動,將會引進對科學有真正興趣的青年人生力軍,參與科研工作。如果政府配合民間,制定出理性的長期科學教育和科學發展策略,台灣的科學家與研究者獲得諾貝爾獎,將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