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崗在他身旁默默地站了很久,他一直看著山峰的臉,他看到那臉上有一種傻乎乎的神色。然後他才轉過身,重新走回臥室。他把存摺放在妻子手中。
「他不要?」她驚訝地問。 他沒有回答,而是走到兒子身旁,用手拍拍他的腦袋說:「跟我來。」 孩子看了看母親後就站了起來,他問父親:「到哪裡去?」 這時她明白了,她擋住山崗,說:「不能這樣,他會打死他的。」 山崗用手推開她,另一隻手拉著兒子往外走去。他聽到她在後面說:「我求你了。」 山崗走到了山峰面前,他把兒子推上去說:「把他交給你吧。」 山峰抬起頭來看了一下皮皮和山崗,他似乎想站起來,可身體只是動了一下。然後他的目光轉了個彎,看到屋外院子裡去了。於是他看到了那一灘血。血在陽光下顯得有些耀眼。他發現那一灘血在發出光亮。像陽光一樣光亮。 皮皮站在那裡顯然興味索然,他仰起頭來看看父親,父親臉上沒有表情,和山峰一樣。於是他就東張西望,他看到母親不知什麼時候起也站在他身後了。 山峰這時候站了起來,他對山崗說:「我要他把那灘血舔乾淨。」 「以後呢?」山崗點點頭。 山峰猶豫了一下才說:「以後就算了。」 「好吧。」山崗點點頭。 這時孩子的母親對山峰說:「讓我舔吧,他還不懂事。」 山峰沒有答理,他拉著孩子往外走。於是她也跟了出去。山崗遲疑了一下後走回了臥室,但他走到臥室的窗前。 山崗看到妻子一走進那灘血跡就俯下身去舔了,妻子的模樣十分貪婪。山崗看到山峰朝妻子的臀部蹬去一腳,妻子摔向一旁然後跪起來拚命地嘔吐了,她喉嚨裡發出了那種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接著他看到山峰把皮皮的頭按了下去,皮皮皮便趴在了地上。他聽到山峰用一種近似妻子嘔吐的聲音說:「舔。」 皮皮趴在那裡,望著這灘在陽光下亮晶晶的血,使他想起某一種鮮艷的果漿。他伸出舌頭試探地舔了一下,於是一種嶄新的滋味油然而生。接下去他就放心去舔了,他感到水泥地上的血很粗糙,不一會舌頭發麻了。隨後舌尖上出現了幾絲流動的血,這血使他覺得更可口。但他不知道那是自己的血。 山崗這時看到弟媳傷痕累累地出現了,她嘴裡叫著「咬死他」撲向了皮皮。與此同時山峰飛起一腳踢進了皮皮的胯裡。皮皮的身體騰空而起,隨即腦袋朝下撞在了水泥地上,發出一聲沈重的聲響。他看到兒子掙扎了幾下後就舒展四肢癱瘓似地不再動了。 那時候老太太聽到「咕咚」一聲,這聲音使她大吃一驚。聲音是從腹部鑽出來的。彷彿已經憋了很久總算散發出來。聲音裡充滿了怨氣。她馬上斷定那是腸子在腐爛,而且這種腐爛似乎已經由來已久。緊接著她接連聽到了兩聲「咕咚」,這次她聽得更為清楚,她覺得這是冒出氣泡來的聲音。由此看來,腸子已經徹底腐爛了。她想像不出腐爛以後的顏色,但她卻能揣摩出它們的形態,是很稠的液體在裡面蠕動時冒出的氣泡。接下去她甚至嗅到了腐爛的那種氣息,這種氣息正是從她口中溢出。不久之後她感到整個房間已經充滿了這種腐爛氣息,彷彿連房屋也在腐爛了。所以她才知道為什麼不想吃東西。 她試著站起來,於是馬上感到腹內的腐爛物往下沉去,她感到往大腿裡沉了。她覺得吃東西實在是一椿危險的事情,因為她的腹腔不是一個無底洞。有朝一日將身體裡全部的空隙填滿以後,那麼她的身體就會脹破。那時候她就像一顆炸彈似地爆炸了。她的皮肉被炸到牆壁上以後就像標語一樣貼在上面,而她的已經斷得差不多了的骨頭則像一堆亂柴堆在地上。 她的腦袋可以想像如皮球一樣在地上滾了起來,滾到牆角後就擱在那裡不再動了。 所以她又眼淚汪汪了,她感到眼淚裡也在散發著腐爛氣息,而眼淚從臉頰上滾下去時,也比往常重得多。她朝門口走去時感到身體重得像沙袋。這時她看到山崗包著皮皮走進來,山崗抱著皮皮就像抱著玩具,山崗沒有走到她面前,他轉彎進了自己的臥室。在山崗轉彎的一瞬間,她看到了皮皮腦袋上的血跡。這是她這一天裡第二次看到血跡,這次血跡沒有上次那麼明亮,這次血跡很陰沉。她現在感到自己要嘔吐了。 山崗看著兒子像一塊布一樣飛起來,然後迅速地摔在了地上。接下去他什麼也看不到了,他只覺得眼前雜草叢生,除此以外還有一口綠得發亮的井。 那時候山崗的妻子已經抬起頭來了。她沒看到兒子被山峰一腳踢起的情景,但是那一刻裡她那痙攣的胃一下子舒展了。而她起頭來所看到的,正是兒子掙扎後四肢舒展開來,像她的胃一樣,這情景使她迷惑不解,她望著兒子發怔。兒子頭部的血這時候慢慢流出來了,那血看去像紅墨水。 然後她失聲大叫一聲:「山崗。」同時轉回身去,對著站在窗前的丈夫又叫了一聲。可山崗一動不動,他瞇著眼睛彷彿已經睡去。於是她重新轉回身,對站在那裡也一動不動的山峰說:「我丈夫嚇傻了。」然後她又對兒子說:「你父親嚇傻了。」接著她自言自語:「我該怎麼辦呢?」 (節錄自<現實一種>,收於《十八歲出門遠行》,遠流出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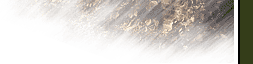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