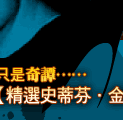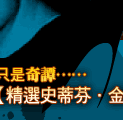安妮將三頁打好的原稿放在保羅旁邊的床斗櫃上,保羅等著聽她評論。他很好奇,但不怎麼緊張──他很訝異自己竟能輕而易舉地返回苦兒的世界。那世界雖然粗俗、乖離,但事實上,回到那裡並沒有他預期中的討厭──老實說,反倒像穿上舊脫鞋,讓人覺得相當舒服哩。
因此當安妮表示「這樣不對」時,保羅忍不住張大嘴,吃驚地問:「你──你不喜歡?」他簡直不相信。喜歡其他苦兒系列的安妮,怎麼可能不喜歡這個開場白?這完全是苦兒的翻版,簡直近乎重抄了嘛,藍蜜奇太太在眝藏室裡張羅,伊安和苦兒則像兩個剛從週末舞會溜回家的高中小鬼一樣黏在一起,這有啥不對,還有──
現在換安妮露出不解了。
「不喜歡?怎麼會,我當然喜歡了。寫得真好,伊安將苦兒擁入懷裡時,我都看到哭了,我忍不住嘛。」說著安妮的眼睛還真有點紅哩。「你用我的名字為湯瑪士的保母命名……真是太窩心了。」
保羅心想:也很聰明──至少我是這麼希望的。順便告訴你,小姐,也許你會對這個有興趣;寶寶的名字本來叫史恩,我把名字換掉,因為覺得裡頭的n太多了。
「那我就不明白了──」
「不,你弄錯了。我沒說我不喜歡,我只說這樣不對,那是在作弊,你得改。」
他竟以為安妮是最完美的讀者?唉,天啊,真有你的,保羅──你不犯則矣,一犯就是大錯。這位孜孜不倦的讀者,已經變成鐵面無私的老編了。
保羅本能地重新調整表情,露出他在聽編輯說話時慣有的誠懇模樣。他稱這種表情為「我能為您服務嗎,小姐?」因為大部分編輯都是那種會把車開到修理站,命令技師限時搞定車蓋或儀表板下奇怪聲響的小姐。這種專心致志的表情通常很有用,因為能哄她們開心。編輯一開心,有時就會放棄一些詭異的點子。
「怎麼會是作弊?」他問。
「嗯,傑佛瑞趕去找醫生這點是沒問題啦。」她說,「那是在《苦兒的孩子》第三十八章裡的事,可是醫生從未趕到,這點你也很清楚,因為傑佛瑞想駕馬從康瑟普那個糟老頭的門上跳過,結果絆到門檻了──我希望那個爛人在《苦兒還魂記》裡得到報應,保羅,我真的希望他不得好死──害傑佛瑞肩膀或肋骨斷掉,在雨裡躺了一夜,直到牧羊的孩子過來發現他為止。就是這樣,醫生才一直沒趕到,對吧?」
「是啊。」保羅發現自己突然無法將眼神從她臉上移開了。
保羅原以為她以編輯自居──甚至自以為是合著者,打算告訴他該寫什麼,該如何寫,但實際上不是這樣。拿康瑟普先生為例吧,安妮希望康瑟普能得到報應,可是並沒有命令他這麼做。安妮雖控制了保羅,卻將小說的創作過程置於自己的權力範圍之外。然而有些事就是做不到,這跟有沒有創作力無關,硬要做的話,就像挑戰重力或拿磚塊打桌球一樣,會徒勞無功。安妮確實是位忠實讀者,但忠實讀者並不等於愚昧的讀者。
她不准保羅殺掉苦兒……可是也不許他用作弊的方式讓苦兒復活。
可是媽呀,我確實已經將苦兒賜死啦,保羅疲憊地想,你到底要我怎麼辦?
「我小時候,」安妮說:「電影院經常演章回電影(Chapter Play),一個禮拜放映一段故事。《蒙面復仇者》、《飛俠哥頓》,甚至還放過《獸神巴克》,那傢伙去非洲抓猛獸,他只要瞪著獅子老虎,就可以馴服牠們。你記得那種章回電影嗎?」
「記得,可是你的年紀不可能那麼大吧,安妮──你一定是在電視上看的,要不就是聽你哥哥或姊姊說的。」
安妮的嘴角在僵硬的臉上牽動了一下。「別亂說話,你這個呆子!不過我確實有個哥哥,以前我們每週六下午都去看電影,那是在加州貝克斯田的事,我在那兒長大的。我雖然一向喜歡看新聞影片、彩色卡通和劇情片,卻更期望看下一集的章回電影。我發現自己一整個星期都在想電影的事,如果上課無聊,或幫樓下克姆茲太太照顧她那四個皮得要死的小混蛋時,我就會想著電影。以前我好討厭那幾個小鬼。」
安妮陷入某種情緒中,靜靜望著角落。她的電源拔掉了,幾天來第一次出現這種情形。保羅不安地想,那是否意味著安妮的情緒跌到谷底了?若是這樣的話,他最好別輕舉妄動。
安妮終於又回神了,而且跟往常一樣,帶著微微的詫異,彷彿沒想到世界依然存在一樣。
「《火箭俠》是我的最愛,第六回《天空之死》結尾時,他在飛機全力俯衝時昏過去了;第九回《火焰未日》最後火燒倉庫時,被綁在椅子上。有時是車子煞車壞了,有時是毒氣,有時是電擊。」
安妮講起這些事來熱情洋溢,情真意切到令人發毛。
「那叫冒險連續片,」保羅插嘴說。
安妮對他皺皺眉,「我知道,自以為是先生。天啊,有時候我覺得你一定是把我當成笨蛋了!」
「我沒有,安妮,真的沒有。」
她不耐煩地對他揮揮手,保羅知道最好別打斷她──至少今天別惹她。「我試著想像他的脫困辦法,那實在非常有意思,有時我想得出來,有時沒辦法。其實我不是很在乎啦,只要劇情沒有編得太離譜就行了。」
她眼神銳利地看著保羅,確認他是否聽懂她的意思。保羅根本不可能沒看到。
「像他在飛機裡昏過去後又醒來,發現座椅下有降落傘,便穿上它,從飛機跳下來,這就編得合情合理。」
只怕所有英文作文老師都會反對你的說法,親愛的,保羅心想,你剛才說的情形有個術語,叫「解危之神」,最早用於希臘圓形劇場。劇作家筆下的英雄遇到沒辦法解決的困難時,舞台上空便會降下一張裝飾著花朵的椅子,英雄坐上去,然後被拉上去,就遠離災難了。就算最笨的阿土也能領略其中的意涵──大英雄被神仙救走啦。可是這個別名又叫「座椅下的舊降落傘」的「解危之神」,終於在一七○○年左右退流行了。當然了,《火箭俠》系列跟《南西杜爾》系列例外。我猜你大概沒看到消息吧,安妮。
在這可怕而令人畢生難忘的片刻裡,保羅以為自己會放聲大笑,照安妮今早的情緒看來,他一定會死得很難看。保羅趕緊用手遮住嘴巴,掩去即將爆發的笑意,然後假裝咳嗽。
她用力拍他的背,拍得他好痛。
「好點沒?」
「好多了,謝謝。」
「現在我可以走了嗎,保羅?你會咳不停嗎?要不要我拿水桶進來?你想吐嗎?」
「不用了,安妮,請走吧。你剛才說的話太有意思了。」
她看來情緒稍緩──不多,只稍稍緩和了一些。「他在座位下找到降落傘,還算合理,雖然不盡然寫實,但還算合理。」
他想了想,心中十分震驚──安妮偶爾展現的洞悉力總是令他驚詫──安妮說得沒錯,合理與寫實在許多層面上也許都算同義字,但在寫作的天地裡則不然。
「結果你另起一個故事,」她說:「你昨天寫的東西就錯在這裡,沒有接著以前的情節寫,保羅,你聽我說,」
「我很努力在聽啊。」
她打量著他,看他是不是在開玩笑,然而保羅的臉色又蒼白又嚴肅──看起來像個乖學生。他原本想笑,可是當他發現安妮其實很清楚「解危之神」的技倆,只是不知其名而已後,就笑不出來了。
「好吧,」她說:「這一章跟煞車有關。有一群壞蛋把火箭俠──但他的身分是個秘密──丟進沒有煞車的車子裡,然後關上車門,將車推下蜿蜒曲折的山路。告訴你,我那天看得簡直如坐針氈。」
安妮就坐在他的床沿──保羅坐在對面的輪椅上。自從他擅闖浴室和客廳後,已經過去五天了,他歷經大難後的復原速度似乎遠超過自己的想像,光憑沒被安妮逮到這點,就令他元氣大振了。
安妮心不在焉地望著月曆,上面的男孩微笑著駕雪橇滑過漫無終止的二月。
「可憐的火箭俠困在車子裡,身上既沒裝備,也沒頭盔。他得同時駕車、設法停車並打開車門,比一個獨臂裱糊工人還忙!」
是的,保羅突然看到那個畫面了──他本能的發現這樣的場景雖然誇張,卻能製造懸疑。畫面上是呼嘯而過的陡坡,接著跳到被男主角踩到底的煞車板(保羅清楚地看到那隻腳上套著四○年代的男鞋)、轉到男主角撞擊車門的肩上、再跳到車門外側,讓觀眾看到焊死的門。劇情雖然又驢又俗,效果卻棒得令人心跳加快。這裡套的不是香醇的佳釀,而是粗烈的私酒。
「接著你看到道路只通到懸崖邊嘎然而止,」安妮說:「戲院裡每個人都知道,如果火箭俠在車子抵達懸崖前無法從車中掙脫的話,就死定了。噢,天啊!車子衝過去,火箭俠拚命煞車撞門,接著……車子飛出懸崖了!然後開始下墜。在摔落途中撞到崖壁,起火燃燒,接著墜入海裡,銀幕上出現結尾的字幕,請收看下集,第十一回,飛龍在天。」
安妮坐在保羅床邊,兩手緊握,豐滿的胸口快速起伏。
「怎麼樣?」她問,眼睛盯著牆壁,沒看保羅。「之後我就無心看其他電影了。接下來的一週,我簡直無時無刻不想著火箭俠,我苦思火箭俠能如何逃脫?卻連猜都猜不到。」
「隔週的週六中午,我站在電影院前,雖然售票亭要一點十五分才開,電影兩點才上映,可是,保羅……後來的事……唉,你永遠也猜不到!」
保羅沒接話,但他猜到了。他明白為什麼安妮雖喜歡他寫的東西,卻覺得不妥當──安妮是以忠實讀者的身分,理直氣壯地在質問作者,而不是用編輯那種有時稍嫌曲高和寡的態度來批判。保羅理解這點,而且他發現自己竟覺得慚愧。安妮說得對,他的寫法形同欺騙。
「新的故事總是先從上一集的結尾演起,火箭俠衝下山,畫面上出現了懸崖、火箭俠猛撞車門、拚命開門等鏡頭。接著就在車子滑到懸崖邊時,車門打開了,火箭俠撲到路面上!車子翻落懸崖,電影院裡所有的孩子齊聲歡呼,因為火箭俠逃脫了,可是我沒歡呼,保羅,我氣炸了!我開始大吼,『上星期不是那樣演的!上星期才不是那樣演的!』」
安妮跳起來開始在房裡快速踱步。她垂著頭,頭髮散亂,一隻手握拳,擊著另一隻手掌,眼中冒出怒火。
「我哥哥叫我別鬧,可是我停不下來,他就用手摀我的嘴要我住口,結果被我咬,我繼續大叫,『上星期不是那樣演的!你們怎麼那麼笨,都不記得嗎?你們都得健忘症啦?』接著我老哥說,『你瘋啦,安妮。』可是我知道我沒瘋。戲院經理走過來說,如果我不閉嘴,就得離開,我說:『走就走,因為那電影在騙人,上星期才不是那樣演的!』」
安妮看著保羅,保羅看見她眼中的殺機。
「他沒有逃出那輛天殺的鳥車子!車子翻出懸崖時他還在裡頭!你明白嗎?」
「我明白。」保羅說。
「你明白嗎?」
她突然一臉兇相地向他跳過來,保羅雖然認定安妮想跟以前一樣傷害他──也許是因為她沒辦法揍那個欺騙觀眾、讓火箭俠在車子翻落懸崖前逃出來的劇作家吧──身體卻動也不動。保羅可以從安妮剛才敘述的往事,了解安妮目前情緒不穩的原因,不過他也對安妮既孩子氣、又純然真實的義憤填膺有些敬畏。
安妮沒有打他,她抓緊保羅的衣襟,將他拉向前,直到兩個人的臉幾乎碰在一起了。
「真的嗎?」
「真的,安妮,我懂。」
安妮瞪著保羅,漆黑憤怒的眼神大概看穿了他的心意,因為一會兒之後,安妮又很不屑地將保羅摔回椅子上了。
保羅痛得肝腸寸斷,片刻後疼痛才逐漸減緩。
「你明白哪裡不妥囉?」她說。
「我想是的。」雖然我他媽的完全不知道要從何改起。
另一個聲音立即響起:我不知道老天是要整你還是救你,保羅,不過有件事我倒是很清楚:如果你不想辦法用安妮可以信服的方式讓苦兒死而復生,這肥婆就會宰掉你。
「那就去改吧。」安妮短短撂下幾個字,走出房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