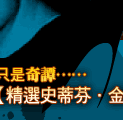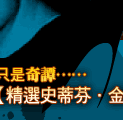「如果可以的話,我想換不同的紙。」安妮回來把打字機和紙張放到板子上時,保羅說道。
「跟這不一樣的紙嗎?」她拍拍紙上的泡棉問,「可是這是最貴的紙啊!我去紙店時問過了。」
「你媽沒告訴過你,最貴的東西未必是最好的嗎?」
安妮臉一沉,原有的抗拒頓時化為不悅,保羅猜想,繼之而來的將會是狂怒吧。
「沒,我媽沒有,自以為是先生。她只告訴我說,一分錢一分貨。」
保羅發現,安妮的情緒就像中西部的春季,滿載著龍捲風,等待隨時狂飆。如果他是農夫,若看到天色變得跟安妮目前的臉色一樣,一定會立即衝回家人身邊,將他們趕到地窖避難。安妮眉頭泛白,鼻孔不住張縮,像聞到焦味的野獸。她的手又開始快速地張開握緊,不斷將空氣抓到掌心裡。
他需要安妮,在安妮面前,他手無縛雞之力,他知道自己應該讓步,及時安撫她──如果他還有時間的話──就像哈格德的小說中,對神偶獻祭,以安撫憤怒女神的部族一樣。
可是他心中還有另一股更精明也較勇敢的聲音提醒他,如果每次安妮發脾氣,他就害怕而軟語相應,他便無法勝任莎赫札德的角色了。如果他態度硬一點,安妮會更生氣吧。那聲音分析道,若不是她對你有所求,應該會立即將你送到醫院,或將你殺害,以免被雷蒙斯發現──因為對安妮來說,世上的人全都是雷蒙斯,他們躲在每一株樹叢背後。保羅啊,如果你現在不跟這臭婊子周旋,我的孩子,你就永遠也辦不到啦。
安妮的呼吸開始變得急促,幾乎要換氣過度了;她的手跟著加速張闔,保羅知道她很快就要失控了。
保羅鼓起僅剩的一丁點勇氣,狂亂地想著如何用堅定而略帶慍色的方式表達。 他說:「還有,你最好別再那樣,發脾氣並不能改變什麼。」
安妮登時僵住,彷彿挨了保羅一巴掌,她一臉受傷地看著保羅。
「安妮,」保羅耐著性子說:「這件事沒什麼大不了。」
「你在耍詐。」她說:「你不想幫我寫書,所以你就耍詐不寫,我就知道你會這樣,天哪,你休想得逞,這──」
「這太荒唐了,」保羅說:「我有說不寫嗎?」
「沒……沒有,可是──」
「那就對了,因為我正要去寫。如果你過來看一看,我會讓你明白問題出在哪裡。請把韋氏罐一起拿過來。」
「韋什麼?」
「就是那個放筆和鉛筆的小罐子,」他說:「報上有時會稱這種罐子叫韋氏罐,那是以丹尼爾.韋伯斯特命名的。」這是他臨時編的謊言,不過確實收到了預期的效果──安妮變得更困惑無措了,在專家面前,她顯得非常無知。困惑令她更有怒氣(因此也獲得了發洩);保羅發現安妮甚至不確定自己有發脾氣的權利了。
安妮拿過筆罐,重重放到板子上。保羅心想:好耶!老子贏了!──不──不對,是苦兒贏了。
但那也不對,是莎赫札德,莎赫札德贏了。
「怎樣啦?」她不悅地問。
「看著!」
保羅拆開紙包,拿出一張卡洛奈紙,用削尖的鉛筆在紙上畫一條線,然後用原子筆在旁邊又畫了一道平行線,再用大拇指擦過微粗的紙面,兩條線便順著拇指擦過的方向糊掉了,而且鉛筆線比原子筆線模糊得更厲害。
「瞧見沒?」
「那又怎樣?」
「色帶的墨水也會模糊掉。」他說:「雖然沒有鉛筆線糊得厲害,可是比原子筆糟。」
「難道你要坐在那兒用拇指去擦每張紙嗎?」
「光是紙張之間的摩擦,幾星期或甚至幾天內,就會讓很多字變模糊了。」保羅說:「作家在寫初稿時,會經常調動紙張,回頭去找姓名或日期。天啊,安妮,幹我們這一行的,一定要知道編輯最痛恨讀手寫稿跟用卡洛奈紙打的原稿。」
「別那樣說,我最討厭你那樣說話。」
保羅一頭霧水地看著她,問:「說什麼?」
「褻瀆上帝賜給你們的創作天分,把寫作說成一種行業。我最恨那樣了。」
「對不起。」
「你是該抱歉,」安妮冷冷地說:「你乾脆說自己是妓女算了。」
保羅突然怒由心生,不,安妮,他心想,我不是妓女。《快車》的創作就是在拒絕當妓女。現在想想,把苦兒這個人物幹掉,也是在拒絕當妓女。我開著車要去西岸慶祝自己從良,而你卻在我撞車後,硬把我從車子裡拖出來推回火坑。幹一次兩塊,四塊錢老子就包下你了。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心底其實也明白。陪審團可能會因為你是瘋子而放你一馬,但我不會,安妮,老子可不會。
「說得極是,」保羅表示:「好了,我們再回來談紙張的問題──」
「我會去幫你弄那天殺的紙。」她寒著臉說:「只要告訴我該買什麼,我自然會去弄來。」
「只要你明白我是站在你這一邊的──」
「別說笑了,打從二十年前我媽去世後,就沒人站在我這邊了。」
「隨你怎麼想吧。」保羅說:「你若那麼不放心,不信我真心感激你救我一命,那是你自己的問題。」
他細細打量安妮,再次從她眼中看到猶疑,看到她掙扎著想要相信。很好,非常好。保羅盡可能裝出心誠意正的樣子去瞅安妮,心中想的,卻是將碎玻璃刺進她喉嚨,讓她那瘋狂腦袋裡的鮮血噴賤而出的情景。
「至少你應該相信我是站在書本這一邊的吧。你說過要裝釘書,你應該是指裝釘原稿?裝釘打好的紙稿,是嗎?」
「當然了。」
是啊,當然嘍。因為你若把原稿拿給印刷工人,可能會啟人疑竇。你雖不懂出版,卻未必無知。保羅.薛頓失蹤了,印刷工人難道不會想起作家失蹤不久後,曾收過一部長篇小說厚度的稿子,裡頭有保羅.薛頓最知名的角色嗎?工人當然會記得客戶的指示了──因為太怪異了,令人印象深刻。長篇小說的稿子,對方竟然只要印一本。
只要一本就好。
「她長什麼樣子啊?嗯,那女的塊頭很大,看起來有點像哈德格故事裡的石像,等一等,我檔案裡有她的名字和住址……我去查一下收據的副本……」
「那樣並沒什麼不好,」保羅說:「裝釘好的手稿看起來會很漂亮,就像好看的對開紙釘本。不過既然是書,就應該能長久保留。安妮,我若用卡洛奈紙打這本書,十年後,你就只剩下一堆空白的紙頁了,除非你把書供在書架上不動。」
可是安妮不會只想把書供在架上,對吧?拜託,哪有可能!她會想每天拿下來,也許每隔幾小時就拿下來,歡天喜地地翻看。
安妮臉上泛著一種奇異冷峻的表情,保羅很不喜歡這種近乎誇張的冷酷,令他非常緊張。他可以估算安妮有多生氣,但這個孩子氣的新表情卻讓他摸不著頭緒。
「你不用再說了,」安妮表示:「我說過會幫你弄紙了,你要哪一種的?」
「你去的那間文具店──」
「是紙店。」
「是的,紙店。跟他們說你要兩令──一令有五百張紙──」
「知道啦,我又不笨。」
「我知道你不笨。」他越來越緊張了,疼痛又在他腿裡竄上竄下,骨盆那邊尤其痛得厲害──他已經坐了快一個鐘頭了,脫臼的地方在跟他大聲抗議。
冷靜點,拜託拜託──千萬別功虧一簣!
可是我有贏過什麼嗎?或只是我自己的希望而已?
「要他們拿兩令白色的直絲油印紙,『漢米坊』的很不錯;『現代』的也不賴。兩令油印紙的錢比一包卡洛奈還便宜,而且應該夠整本書跟重寫的用量。」
「我現在就去。」安妮突然站起來說。
保羅戒慎地看著安妮,知道她打算再次拋下他,不給藥吃,而且這回還讓他坐著。他已經坐到開始痛了,就算安妮用趕的回來,只怕他早痛掛了。
「你不用急著馬上去。」保羅慌忙地說:「用卡洛奈起草稿就夠了──反正我會重寫──」
「只有呆子才用爛工具展開工作。」她拿起那包卡洛奈,一把抓起畫了兩道糊線的紙揉成一團,統統扔到字紙簍中,再回頭看著保羅。那冷酷執拗的神情像面具般鑲在她臉上,安妮的眼睛如失去光澤的鑽石,閃著黯然的灰光。
「我現在就去鎮上,」她說:「我知道你希望盡快展開工作,因為你跟我是站在同一邊的。」──她重重吐出最後幾個字,語帶諷刺(而且保羅認為還有著不自覺的哀怨)──「所以我沒時間扶你回床了。」
她微微笑道,雙唇像木偶一樣詭異地咧著,說完踩著白色護士鞋,悄然無聲地溜到保羅身邊。她用手指觸摸他的頭髮,摸得保羅渾身哆嗦。他努力不躲,卻不由自主。安妮皮笑肉不笑的表情更僵了。
「看來我們得把《苦兒還魂記》的開工日往後延一天……或兩天……甚至三天了。是的,也許你得再三天才有辦法再坐起來,因為太痛了。真可惜,我在冰箱裡冰了一瓶香檳,看來我得把它放回畜欄裡了。」
「安妮,真的,我可以立刻開始寫,只要你──」
「不,保羅。」她走到門邊,然後回頭冷冷看著他,臉上只有那對失去光澤的眼睛還泛著生氣。「有件事我希望你搞清楚,別以為你能唬我或耍我,我知道自己看起來並不俐落,但我不笨,保羅,而且也很靈光。」
她的表情丕變,原本的冷若冰霜化為烏有,突然像個暴怒的孩子一樣。保羅還以為自己會被活生生嚇死,他竟然以為他占了上風?是嗎?你若被瘋子囚禁,還有可能扮演莎赫札德嗎?
安妮越過房間朝他衝過來,肉墩墩的肥腿踩地有聲。她屈著膝,手肘像活塞似地在窒悶的空中來回擺動。她的髮夾鬆開了,頭髮散亂在臉上,她咚咚踏地而來,如同歌利亞踩在以拉谷中,牆上的凱旋門照片也跟著劈啪震動。
「喝──呀!」她尖叫一聲,舉拳往保羅.薛頓左膝上的鹽丘夯去。
保羅仰頭慘叫哀呼,青筋在脖子和額上突跳,痛楚從膝蓋竄出,刺得他全身發顫。
安妮將打字機從板子上攫下,用力摔在壁爐架上,沉重的金屬到了她手裡,竟輕若空紙箱。
「你給我乖乖坐在那兒,」她咧嘴笑道:「好好想一想這裡是誰在當家作主,還有你若不乖乖聽話,想耍我,會有什麼後果。你坐好,想叫就叫,因為沒有人會聽到你的叫聲。我這兒不會有人來的,因為他們都知道安妮.維克斯是瘋子,知道她幹過啥事,雖然他們查不出罪證。」
她走回門邊後又轉身。保羅一看到安妮回頭,便尖叫起來,以為她又要打過來了。安妮見狀笑得更開懷。
「再告訴你一件事,」她輕聲說:「他們覺得我逍遙法外,他們想得沒錯。趁我去鎮上幫你拿那該死的紙時,你好好考慮考慮吧,保羅。」
安妮走了,門被摔得連屋子都跟著搖晃,接著就只剩下鐘聲滴答響了。
保羅仰靠在椅子上,全身顫抖。他極力忍住,否則會痛,卻又無計可施。淚水止不住地流下。他不斷看到安妮大步踏過房間,不斷看到她舉起拳頭,像憤怒的醉鬼用鐵錘搥打木製吧台般地痛擊他僅存的膝蓋,而他也一再地被痛苦吞噬。
「求求你,上帝,求求你。」他哭著,外頭的吉普車發出轟轟聲。「求你,上帝,求求你──放了我或殺了我……放我脫離苦海,或殺了我吧。」
引擎聲漸行漸遠,上帝袖手旁觀,任保羅困在淚水與病痛中,此時痛楚已全然被喚醒,惡狠狠地折磨他的全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