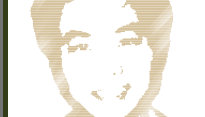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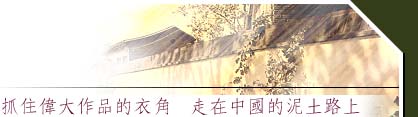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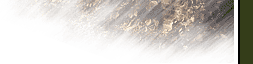
|
文/駱以軍(作家) 如同奈波爾在《抵達之謎》裡,充滿惆悵地回憶,他十八歲第一次遠離故鄉千里達,在紐約的城市高樓間踟躕晃逛,看到一家電影院的廣告,片名和演員皆顯示那是一部法國片,他寫道:「我這輩子從沒看過法國電影。但我知道不少法國電影。那是我從書上看來的,我甚至會以某種方式『研究』它……就像一個人,他拒絕去一些著名的城市玩,只看那些城市的街道地圖……我認得那些書中所有的劇照。他精闢的文字內容,以及我對法國之身為文化大國的濃厚興趣……讓我從那些反差大、複製效果又差的小劇照中看出了特殊的優點。」 奈波爾將之(他的「十八歲出門遠行」)描繪成一趟「自我剝奪、刪除記憶,卻又充滿欣羨在想像中比照『巨大』西方現代實景」的旅程。余華則在《我能否相信自己》中,像「年輕一些的波赫士聽年老的波赫士說話」,他必須從波赫士「四倍的子彈」的現實講起。那和他置身、面對並且必須為自身作品解釋的國度如此陌生。 一些巨大的名字。那很像是馬奎斯在〈我遇見了海明威〉裡所說:「我們這些小說家讀別人的小說只是為了了解那些小說是怎樣寫的。……我們不滿足於小說正面暴露出來的祕密,還要把它翻個面兒,看看它的接縫。我們以某種難以解釋的方式把小說的主要部件拆卸下來,等了解了它那獨特的鐘錶似的結構之奧祕後再把它重新組裝起來……」這是讀一個一流小說家飽含感情談另一位一流小說家作品精微妙處的美好經驗。譬如我們讀到波赫士用芝諾「飛矢辯」談卡夫卡或是昆德拉用主題賦格談卡夫卡,我們當然知道卡夫卡不止於此,但常常我們記下的就是某一個作家在另一個作家的作品中,靈光乍現勾指出那不可思議的天才段落。譬如馬奎斯說福克納「像一群公羊在一家玻璃店裡撒野」,卡爾維諾說波赫士「每件作品皆包含了宇宙的一個模型或特質」。余華的《我能否相信自己》確實是一本「溫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我們顛倒迷離地跟著他穿過那二十世紀上半葉,現代小說黃金時光,那些偉大小說家在搏擊「真實」與時間、大屠殺與孤立個人的信仰崩毀、語言或記憶……他們穿行過的山谷之陰影或是橋樑反面的脊骨。余華的「小說時間」鐘面恰迥異於王安憶的「心靈世界」。王安憶的後俄小說素養使她在某一階段的書寫實現上避開了現代主義的文字白化症與一種早於他們現代性經驗、僅只內向封閉於小說中的「觀念性的解釋世界的衝動和為世界製造一次性的圖像模型」。而那恰正是余華的起點。 這樣的(朝向不同時代的西方典律)時差、濃縮擠壓、錯雜並置──包括八○年代同期產生於尋根之後的「新寫實小說」和「先鋒小說」──令人不能置信地在二十年間(余華二十歲最初讀到川端《伊豆的舞孃》,二十五歲在浙江海鹽一間臨河的屋子裡讀到了卡夫卡),將西方近百年來的小說(或如昆德拉所說:歐洲小說一種對於人的存在處境之描述熱情),「超英趕美」,繁花簇放集中實現在大陸這一批黃金世代的中文小說實踐上。那個過程或已難立分一邊界──或正是奈波爾哀傷感慨,或是早於六○年代便由王文興、郭松棻他們開啟的現代主義──他們在五四以後,中文小說書寫的另一次接軌西方文藝的現代化高峰,觸撞到了怎麼樣的牆?(黃錦樹說?「哲學?」) 因為波赫士是《我能否相信自己》的核心關鍵詞,所以串連著每一詩意飽滿的篇章,每一位提供了不同的敘事的現代性體驗或「當代小說對技巧的深刻需要」的大師名字,便無可避免地環繞著「虛構」這個小說國度與真實隔河相望的詞語之王。「真實可信的存在方式是因為它曲折的形象。」(《一千零一夜》)「描述細部的方式,幾乎抵達了事物的每一條紋路。」(川端)「他們都是在人們熟悉的事物裡進行並且完成了敘述。」(卡夫卡)。當然全書最動人的章節是福克納、杜思妥也夫斯基他們在小說中殺人後,如何「停止描寫內心的語言」;以及講到布魯諾•舒爾茨那「父親變成螃蟹被煮熟後復逃跑」的段落。「虛構」在這裡成了小說家素樸尊嚴的工匠技藝,而非昆德拉式的碎裂犬儒或艾可的電腦爆炸知識百科之熵。 【本文原刊載於《聯合報•讀書人》每周新書金榜 (2002.12.01),經作者同意後轉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