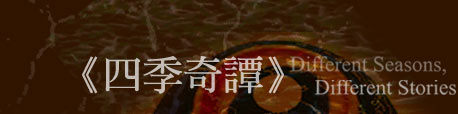俱樂部裡的奇幻空間,讓人不寒而慄的詭怪場景
〈呼-吸-呼-吸〉
幾個人不定期在一個酒吧聚會,並規定每人要說一個故事,而本故事便是圍繞在其中一個醫生講述他與病人之間的互動故事,該名病人為未婚懷孕婦女,在產檢過程後期,醫生教他呼吸方式,就在即將臨盆時候,該名孕婦搭車前往醫院準備待產,結果遇上車禍,孕婦從車裡被彈了出來,屍首異處,但當醫生趕到現場時,發現無頭的孕婦竟然用著他教的呼吸法在呼吸,而且胎兒仍有心跳,於是就在雪地上為這名孕婦接生,順利產下小寶寶。
書摘
十年來,我不斷來到位於東三十五街二四九B的這幢黃褐色砂石建築物報到──斷斷續續地,幾乎可以稱得上規律。我私下覺得這是一個「紳士俱樂部」,沿襲了女權運動興起之前的傳統。但即使是現在,我還不敢確定是否真是如此,以及當初俱樂部究竟是如何成立的。
麥卡朗講呼吸方法的故事的那天晚上──我們俱樂部總共有十三位會員,不過在那個強風怒號的雪夜,只有六個人如約前來。我記得有些幾年,俱樂部只有八位常任會員,有些年則有二十位,或許還不止。
我猜史提芬大概知道俱樂部是如何成立的──我之所以如此肯定,是因為自從第一個會員以來,他就一直在那兒,也不知道究竟待了多久……我相信史提芬的年紀一定比他外表看起來大得多。他講英文帶了點布魯克林腔,然而除此之外,他辦事精準,無懈可擊,堪與訓練有素的英國管家相媲美;他的沈默與含蓄時常令人切齒,但這也是他獨特魅力的一部分,而他的淺笑更像一道上了鎖又閂住的門,難窺其中之奧妙。我從未見過俱樂部的紀錄──如果有的話,也從未接到會費的收據──因為我從來沒有繳過會費,俱樂部秘書也不曾打電話給我──俱樂都沒有秘書,東三十五街二四九B也沒有電話,還有,這俱樂部──如果真是個俱樂部的話──也一直沒有名字。
我第一次去俱樂部(我只能這麼稱呼了),是華喬治先生請我去的。一九五一年以來,我就在華先生的法律事務所工作──這是紐約三大法律事務所之一;我在事務所中的發展,雖然稱得上穩定,卻慢得不得了。我是個刻苦實幹的人,工作相當賣力……但不具備足以傲視群倫的天份;我見過一些跟我同時起步的人平步青雲,而我仍然按部就班地一步步慢慢往上爬。而我對這一切,並不真的感到訝異。
華喬治偶爾會和我開開玩笑,每年十月,我們都會參加事務所主辨的晚餐會,除此之外,就沒有什麼交往了。一九六幾的秋季,十一月上旬有一天,他突然造訪我的辨公室。
光是這樣就已經夠不尋常了,我不禁往壞處想(我被開除了?),又往好的方面想(也許我得到意外的升遷?),他的來訪真是令人困惑。華喬治倚在門口,別在他背心上的大學優等生榮譽會章散發著柔和的光芒,他嘴裡隨便東扯西扯──都是些無關緊要的事,我一直在等他說笑完畢,直接切入手邊正在處理的案子,但他好像壓根兒不想這麼做。他瞥了一眼手錶,表示跟我談得很愉快,現在他得走了。
我仍然一頭霧水,然後他又回過頭來順口說道:「我差不多每星期四晚上都會去一個地方──俱樂部之類的地方,裡面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紀的老頭,不過有些人倒不失為談天的好對象。如果你對品酒有興趣的話,那裡有個很不錯的酒窖,而且偶爾還會有人說好聽的故事;哪天晚上過去看看如何?算是我的客人。」
我結結巴巴地回答了一些話──直到現在我還不確定自己說了什麼,他的邀請完全把我弄糊塗了;他的建議乍聽之下,似乎是偶發之論,然而只要一看他兩道灰色濃眉底下一雙冷冰冰的藍眼,就知道這絕非偶發之論。如果說我不記得自己究竟是如何回答的,那也是因為我突然覺得這個建議──儘管語焉不詳又莫名其妙──就是我一直等著他說出的正題。
那天晚上,愛倫的反應是又好氣,又好笑。我在華喬治手下已工作了大約十五年,顯然我不可能升到比現在的中級職位更好的位置,她認為這是事務所安撫資深員工的新花招,可以省下買金錶的花費。
「一群老人家說說戰時的故事,玩玩撲克牌,」她說道。「過了這樣一晚,他們就認為你應該安於在公司裡坐冷板凳,直到他們給你一份養老金,打發你走路,我猜……喔,我替你留了些東西吃。」接著她親吻著我,我想她在我臉上看出什麼了──在一起過了這麼多年以後,她可以一眼看穿我的心事。
過了幾個星期,什麼事也沒發生;每當我想到華喬治奇怪的建議──當然奇怪啦,我一年見到他的次數不會超過十二次,我們在社交場合見面的機會一年頂多也只有三次,包括事務所在十月份主辦的那個晚宴在內──我想我大概會錯他眼神中的涵意了,或許他真的只是隨便提提,不久就忘了,或許事後還頗後悔。後來有一天傍晚,他走到我面前;雖然他已年近七十,但肩膀仍然又寬又厚,一副運動家的架子;當時我雙腿夾著公事包,正穿上大衣。他說道:「如果你還想去俱樂部喝酒,何不今晚就去?」
「我……我……」
「很好。」他塞了一張紙到我手裡。「這是地址。」
那天晚上他就在俱樂部的階梯底下等我,史提芬為我們拉開門。俱樂部的酒正如華喬治所說的一般好;他一點都不打算介紹我給大家認識──我原本以為是因為他很勢利,後來才不作如是想──不過有兩、三個人主動向我作自我介紹,其中之一即是麥卡朗,當時他也已經坐六望七了;他伸出手,我匆匆握了一下,他的皮膚又乾又粗,幾乎像龜皮一樣。他問我會不會玩橋牌,我說不會。
「他媽的好東西。」他說道。「本世紀以來,這種他媽的遊戲取代了不少賣弄知識的飯後閒聊。」說完他便走到陰暗的圖書室,裡面滿是一列列高大的書架。
我四下張望,想看看華喬治在哪兒,可是他卻不見了。我有一點不安,覺得格格不入,於是就慢慢踱到火爐旁;相信我在前面提到過,這個火爐極其巨大──尤其在紐約似乎更顯得是龐然大物,因為像我這種住在公寓裡的紐約客,實在難以想像這麼大的壁爐是打哪兒來的,一般人的壁爐可以爆米花與烤麵包,就很不錯了,而東三十五街二四九B的壁爐足以烤一整隻牛。它沒有壁爐架,只有一塊堅固的拱形石覆於其上;拱形石的中間有一塊裂縫,其間是一塊微微凸出的拱心石,恰好與我的眼睛平行,儘管燈光昏暗,我仍然可以毫不費力地看見刻在石上的字:故事本身才是主角,而不是說故事的人。
「你的酒,大衛。」華喬治在我身邊說道,我驚跳一下;他畢竟沒有棄我而去,只是到什麼地方拿酒去了。「你喝威士忌蘇打,是嗎?」
「是的,謝謝你,華先生──」
「叫我喬治,」他說。「在這裡叫喬治就行。」
「好,喬治。」我說道,雖然我還是覺得直呼其名有點瘋狂。「這些都──」
「乾杯。」他說道。
我們喝酒。
「史提芬負責調酒,他的酒調得棒極了,他總愛說調酒雖是雕蟲小技,但卻非常重要。」
靠著威士忌的威力,我不再覺得那麼格格不入。(我為了這個約會,在衣櫥前面整整站了半個鐘頭,不曉得該穿什麼衣服,後來終於決定穿深棕色的西褲,與一件勉強可搭配的軟呢上衣,暗自希望我要見的一群人既不會穿燕尾服,也不作短夾克、牛仔褲打扮……不過在衣著方面,我穿得還不算太離譜。)新的社交場合總會使人非常留心每一個禮儀小節;禮貌性地乾了一杯之後,我非常希望確定自己沒有疏忽任何禮節。
「我是不是應該在來賓冊上簽名?」我問道。
他看來有點詫異。「我們沒有那種東西。」他說道。「至少我不認為我們有。」他環視著陰暗安靜的房間;尤漢生把他的《華爾街日報》翻得刷刷作響,我看見史提芬從房間另一頭走過來,他穿著白色上衣,真如鬼魅一般。喬治把酒杯擱在茶几上,然後將一根木條丟進火裡,火花衝上了煙囪黑漆漆的頸部。
「那是什麼意思?」我指著拱心石上的文字問道。「你知道嗎?」
華喬治細心地讀著,彷彿他是第一次看到這些文字。故事本身才是主角,而不是說故事的人。
「我大概知道。」他說。「如果你以後再來,可能就會明白;嗯,到時候你就明白了。好好享受吧,大衛。」
他走開了。雖然好像有點奇怪,人生地不熟的,他竟然把我我一個人丟在這裡自生自滅,但我的確好好享受了這一晚。一來我向來喜歡看書,這裡有許多有趣的書可看;我沿著書架緩緩走著,在微弱的燈光下,費勁地檢視每一本書,時而抽出一、兩本來瀏覽,其間我還停了片刻,站在狹窄的窗前,望著第二大道的十字路口。我站在那兒,從結了霜的玻璃窗望出去,注視十字路口的紅綠燈來回變換,先從紅到綠轉黃,然後又恢復紅色,驀地我有一種怪異至極──但卻非常可喜──的祥和感,這種感覺並不是猝然湧到,而好像是偷偷襲上心頭。喔,是的,我可以聽見各位在說:你說得太美妙了,大家只消對紅綠燈望上兩眼,就會有一股祥和感了。
好吧,就算我在胡說八道,我不介意你會這麼想,不過我還是照樣有這種感覺;它使我多年來第一次回想起小時候在威斯康辛州的農家度過的冬夜。冬天的晚上,我躺在二樓一個會漏風的房間裡,屋外的寒風挾著乾透沙子般的白雪呼嘯不斷,我緊緊裹著兩層被子,身上暖呼呼的。
書架上有一些法律書,但每一本都相當奇怪,《二十大肢解案在英國法律下之判決結果》是我記得的書名之一,《寵物案》是另外一本。我打開這本書,內容果然是針對寵物相關案件的法律論述(這本探討的是美國法律)──從繼承大筆遺產的家貓,一直到掙斷頸鍊、嚴重咬傷郵差的豹貓都有。
還有一套狄更斯的作品,一套狄福的作品,特洛普的作品更是數不清,還有一套小說──共十一本──作者叫施維里,書殼包著是漂亮的綠皮,燙金的字上寫著出版商為「斯德罕圖書公司」,作者與出版商的名字我都沒有聽說過,其中第一本小說《他們都是我們的兄弟》出版於一九一一年,最後一本《暗礁》則出版於一九三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