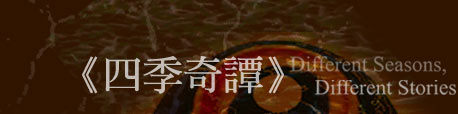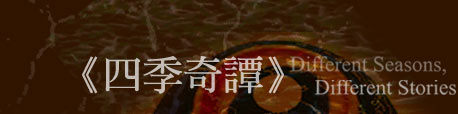�O�s�b���~�������O�СA�G��֦~���ͱ��P�_�I
�q�`�n���A�r
���e�y�z�@�ӧ@�a�^�ХL�P�B�ͦb�~�֮ɭԤ@�P�M�����A�䤤�����ߥ�ԻP�~���ҹJ�Ʊ����g�L�C���g���q�v�m���b�ڳo��n�]Stand
by Me�^����ۤp���C
�ѺK
�@�@���O�q�@�E���C�~�H�ӳ̰���B�̪������L�Ѣw�w���ȤW�O�o���F�Ұʸ`�g�����e�@�ӬP�����A�s�Ǧ~�Y�N�}�l�A�s�a�W�����Q���P���Ǫ������ݰ_�ӳ����ڤڪ��C���~�S���H���[�j�Ωݼe���F���Y�j�i���M�i��ۡA���Y�W�]�n�F�@�h�ǡA�o���M�F�H�ݬz�C���~�L�ѡA�S���H�@�N�y�n����F��A�γ\�Z���^�s�O�ߤ@���ҥ~�C
�@�@���ӬP�������W�A���}�B�_���M�ڳ��b�Ѽֳ��̡A�����Y�N�}�Ǫ��Ƶo�T�A�ڭ̤@�䪱�P�A�@�����@�Ǧѱ��������ܡC�A��D�k��H�ӹL�A����|�O�H²��A�A���U�����ŪŦp�]�A�ӧA�����o�j���K�K�C���}�C�^ť�F�A���˥X�@�ƥͮ𪺼ˤl�A���L�C���m�۱��U�h���H�`�O�L�A���L�]�ȶȧ�k��H�����i���H�}�F�C
�@�@����U�D�`���D�A���L�ڭ��٬O��FŨ��A�K�o���y�H�I�A��A���óz�F�C�ڭ̪����O�Q�I�b�A�O�Ҧ��P���̵̳L�᪺�@�ءA���ڭ̮ڥ����o���Q����������P���C�K�뤤���H�e�A�ڭ��ٯ�ꦨ�@���٤������y���A����j�a�N�����F�A�Ѯ��b�Ӽ��F�C
�u�E�I�C�v�_�����C
�u�Q�I�b�C�v���}���ۡA�@�y�O�H���c�������C
�uç�Q�C�v���仡���P����W�@�ϡC
�@�@�u��̿�F�A��̤j��S��F�C�v���}�����z������}�ڪ����W�W�A���۫K�o�X�L���|�@�L�������}���l���w�w�������K�K�A�����@�ڥ��ת��v�l�Q�H�q����Y�̺C�C�ޥX�Ӥ@�ˡC�����A�L���T�Dz��A�ڭ̳����D�C�L��ڭ̤@�ˡA�֤Q�T���F�A���ѩ�L���p����P�Uť���A�L�ݨӤ�ڭ̤j�o�h�C�C�^�O���p�Ħb��W�ݨ��L�A���c�δc������L�n�ҡA���LŨ�m�f�U�̬�_���@�����O�ҡA�u�O�Uť�����q���}�F�C
�@�@���ޮ��}�����W���F����p����A�զ��̤S��F�Uť���A�L���M�ݤ��ӲM���A�]�ɱ`ť���O�H���N��C�n�O���_�βy�ӡA�A�u�����L���b�]�樺�̡A��_���P���������~���M�k�~���٭n���A�åB��ë�S���H�|��y���쨺���a��A�]���L���}���S���ݨ�y�A�L���|���g�K�ʪ��b���Y�r�l�C��L�Ө��A�@�Y����]�O�`�ơF���@�^�L�@���]�ۡA�K����Ϊ��]�漲�L�h�A�ߨ襢�h��ı�F�L�N�������ۥղ����b�a�W�A�������F�������A�u����~�ˤF�C�L���L�Ӥ���_���A��l�W�y�ۨ�D�A��A�B�Y�W�h���_�@�����⪺�j�]�A���M�������Ѩ��O�Ӭɥ~�y�C
�@�@�L�ѥ͵��O�t�A��ť�O�t�ˬO�ƥX���]�C�H�e�j�a�����w���Y�v�űo�u�u���A�S�X�Ⱖ�զ��A�N��~�������զ��@�ˡC���}�o�O�����ɲĤ@�ӯd���Y�v�����H�A���ɬ���H�s���Y�O��诫�t���٤����D�C���}��զ��\������]�A�O�L���զ��N������n�I�I�����@�ˡC
�@�@���}�K�����ɭԡA���@�ѥL���ˬ��F�L���}�L�l�Ӥj�o�p�^�A�Ʊ��o�ͮɥL���˥��b�c�t���u�A���o���^�ӮɡA�@���w�g�L�h�C
�@�@���}��������L���p�Ы᭱���j�l�l�e�A�M��@�����L�����ߡA���b�l�x�W�Q�����A�M��A��_���}���Y�v�A���Y���t�@�䩹�l�x�@���C����A�L�K���q�ܵ���Ϥ��ߡA�n�L�̨ӱϥL���Ĥl�C���W�q�ܤ���A�L������o�e�A���X�L���I�@���f�|�y�j�A�K���U�Ӭݹq���A�y�j�N��b�j�L�W�C�j�������ӤӹL�Ӱݮ��}���˪��ɭԢw�w�oť�����}�y�s���n���w�w���}�������ݰ_�y�j��Ǧo�C���Ӥӥߨ�L�N�]�A�N�ۤv��b�a�̡A�S���q�ܳ��Fĵ�C���@���ӤF����A�����������@���i�ӡA�ξ�[����}��i�������ª����@���̡A�ۤv�h�q�᭱���Y���X�h���ĵ�١C
�@�@���}����������@�L�����A�����ǸӦ������ŭx�x�i�D�L�ĤH�w�g�²M�A���G�L�o�o�{��B���O�Ѽw�������L�F�o�ɨ䤤�@����@�L�N�ݥL�������o���A���}��������i�a�L�L�@���A���L�Y�ϾԦ��F���A�]�b�Ҥ����C��O���@�L�¥L�q��§�A���}���Ѫ��ߨ�^�q�@�ӡA���@�����}�X������A�{ĵ���]�H���ӦܡA�Ѱ��F���u�F�������հҪ�¾�ȡC
�@�@�L�ɱ`���@�ǥj�Ǫ��ơA���κj�g���ߡA�άO�b�l�c���I���C�o���h�ݨ�l���ƥ�o�ͫᤣ�[�A�L�̫ܧֿ�F�@��ť�ҷ|�A�P�L���i�@�Һ믫�f�|�C���}���Ѫ��L�h���b�n���հҲĤ@�Фj�X���Y�A���}�N�`�`�o��ήe�L���Ѫ��A�Y�ϥL�Ѫ��o���ݥL�A�L�٬O��Ѫ��ܨؤ��w�A�C�ӬP����������h�ݥL�C
�@�@�ڲq�L�O�ڭ̳o�@�s���Ҹ̳̲ª��@�ӡA�ӥB�]���X�������C���ɭԥL�|�_�I���Ƿ��ݺƨg���ơA�C�^�o��������Ӱh�C�L�̬z�z�ֹD���@��j�ơA�Y�O�u�{���v�F�L�|��۪ﭱ�ӨӪ����l�g�b�A�n�X�����t�I�Ӥ��ΰ{�}�A�Ѫ��D�L�`�h�֤H��Ŧ�f�o�@�A�ӥL�o�b�@�䯺�Ӷ}�h�A�e�p�ӹL�����l�걲�_������L����A�j�o�p�i�����\�ʡC�ڭ̨C�����Q�L�~�o�b���A�]���L�Y�����F���i�ֲ~�l����p������A���u�٬O�@���ҽk�F�ڭ�ı�o�L�`���@�ѷ|���⼲�W���l�A�o�u�O�𦭪����D�A�r�L���ɭԱo�p�ߡA�]���L�i�ର�F���A�������C
�u��̿�F�A���w�w���w�w���I�v
�u�ַФF�C�v�ڻ��ۡA���_�@���m�j�����n�A���L���~�C
���}���_�L���P�A���t�h�F�@���A���D�G�u���F�I�v
�u�A�o�|�������I�v�_���۹D�C
�@�@�u�ڳo�|���������@�d�������C�v���}���e�Y�¦a���A�_����ګh�T�����g���C���}�K�۬��Y��ۧڭ̡A�ϩ��q���z�ڭ̦b����������F�o�]�O���}�t�@�ө_�Ǫ��a��w�w�L�`�|���@�ǩ_�Ǫ��ܡA���u�ڳo�|���������@�d�������v�@���A�֤]�����D�L�s���O���N�ޤH�o���A�٬O�H�K�����A�M��L�N�K�_���Y�A���۱����j�����H�A���O�b���G�ѤѡI�o�^�S�O����Ʊ��o��n���H
�@�@ ���}�©�a�~�P�A�ګh�ݨ�ѱ��ת���m�����C�o�ɶǨӦ��H�֨B�n�W��l���n���A���۷t�����U���K�T�_�V���n�C
�u�֡H�v�_���q�D�C
�u�ڬO�Q���I�v�Lť�ӫܿ��ġA�ӥB�W�𤣱��U��C
�ڨ���t����ԤU�����A���}�B�O�Q���A�]�O�ڭ̩T�w�������@�C�L���@���A�K�W�F��ΡA���W���y�H�I�A�V�Ӿ����������z���l�Y�A�]�F�@�q��@�q�H�b�@���C
�u�z�A�U��C�v�L�ݵۮ�C�u�n���nť�ڪ��j�����H�v
�u��������H�v�ڰݡC
�u���ڳݤf��A�ڬO�q�a�̤@���]�L�Ӫ��C�v
�u�ڤ@���]�^�a�A�v���}�H��ť���ݭ����ۡA�u�u���F���ګܩ�p�w�w�v
�u�h�A���C�v�Q�����C
�u�A���A�q�a�̶]�Ӫ��H�v�_�����H�a�ݹD�C�u�ѥS�A�A�u�O�ƤF�C�v�Q�����a�b�������A����Φ��G�����C
�u�ܭȱo�C�v�Q�����C�u�ѤѡI�A�̤@�w���|�۫H�A�u���C�v�L����祴�ۺ��O�������B�Y�W�A���ܥL���{�u�C
�u�n�a�A����ơH�v
�u�A�̤��ߥi���i�H�X�ӡH�v�Q�������ӿE�ʦa�ݧڭ̡A�����N����ɸ��尮�����C�u�ڬO���A�̪������|���|��A�̦b�ڮa��|�f�b�O�L�]�H�v
�u�ڷQ�i�H�C�v�_�����ۮ��_��o���P�@�ۡC�u�i�O�ڪ����b�s�a�̡A�j�ܯS�ܡA�A���D���C�v
�u�A�@�w�n�h�C�v�Q�����C�u�u���A�A�̵����|�۫H�C��̡A�A�O�H�v
�u�]�\�C�v
�@�@���ڴX�G����Ƴ��i�H���w�w���~�L�ѡA�ڴN�����ΤH�S��ˡC�|��A�ڪ����������b���פ���͡A���ɥL���b��v�Ȧ{��B�����s�L�V�m�C�L��t�@�ӳå�r�ۦN�����h�l���A�o�Q�@�����x�d���d�y���W�A���������f�R�A���W�t�@�ӤH��{�b����M�e���g���A�C�Ƶo����Z�������G�Q�G�����ͤ�u���X�ѡA�ڤ]�w�g�R�n�ͤ�d�dzƱH���L�C
�@�@��ť������ɭ��F�A��§�ɧڭ��o��ˤߡA��b���H�۫H�����h�F�A�H�e���ӦѷR�V�ڸ��U�B�ξ�ֻj�����~���B�άO�ڶ^�ˮɿ˿˧ڡB���������\�B�b�ڦ��仴�n���u�O���F�I�v���H���M���s�b�F�w�w���g�N�L�ګ��L�ڪ��H�~�M�|�����C�����~�M�|�����A�o�Ӯ����O�ڬJ�ˤߤS�`�Ȣw�w���L�ڪ��������G�w�����Y��C�ڸ����O�ˤ⨬�A���ѩ�L�j�ڤQ���A�ڭ̴N�q�B�ͤ@�ˡA�ӥL���ۤv���B�ͻP�P�ǡC�ڭ̦b�P�@�i��l�W�A�Y�F�n�X�~�����A���ɭԥL�O�ڪ��B�͡A���ɭԥL�]�|��ڡA���L�j�b�ɶ��L�u�O�A�A���D�A�@�ӧڻ{�Ѫ��å�}�F�C�L�����ɭԡA�w�g���a���@�~�A�u���𰲮ɦ^�a�L�⦸�A�ڭ̬Ʀܳs���۳������C�L�F�n�[�ڤ~�oı�A�ڪ��\����곣�O�������Ӭy���C
�u�Q���A�쩳�O���ơH�v���}�ݡC
�u���F�C�v�_�����C
�u����H�v���}�y�s�D�A�ߨ���Q����b�@��C�u�A�o�U�y���F�l�I�����b�P�̰���}�I�v
�_���H�H���D�G�u��P�a�I�v
��H�q���@�n�a�~�U�h�A���s���߰_�ڪ��������x�C
�Q�����G�u�A�̭n���n�h�ݫ���H�v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