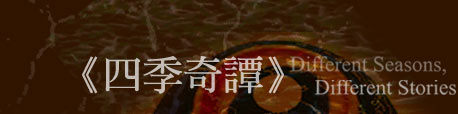老人和少年的狂暴角力,幽黯心靈正在沈淪侵蝕
〈納粹追凶〉
本篇故事描述一位成績優異的男孩,為了誘使一個曾在納粹集中營極盡屠殺之能事的老軍官回憶過去種種的罪惡行為,結果在回憶的過程中,也讓自己墜入人心最險惡的深淵。本篇故事於一九九八年登上大銀幕,名為《誰和跟我玩遊戲》(Apt
Puil)。
書摘
他騎著那輛二十六吋高、有彎把的腳踏車,在郊外住宅區的路上行駛時,就像個典型的美國小孩。塔德.包登是個十三歲、五呎八吋高、一百四十磅重的健壯少年,頭髮是熟透的玉米色,藍眼睛,一口整齊潔白的牙齒,微微曬成褐色的皮膚上,長著幾粒青春痘。
帶著放暑假的輕鬆心情,他微笑踩著腳踏車,在陽光下、樹蔭間,穿梭在離家不遠的街道上。他看起來像個送報僮,沒錯,他的確在送報;他也像個賣賀卡賺取學費的少年,沒錯,他也兼賣賀卡。他看起來還像會邊工作邊吹口哨的那種人,他的確常常吹口哨,而且也吹得相當好。他的父親是個建築工程師,年薪四萬元,母親念大學時主修法文,當時塔德的父親迫切需要法文家教,兩人便結識了。母親利用閒暇替人代打文件,她把塔德所有的成績單都保留起來。其中她最喜歡的是塔德小學四年級的學期成績單,老師在上面的評語是:「塔德是非常優秀的學生。」塔德確實是個高材生,小學一路念下來,成績單上不是A,就是B。要是他全得A的話,朋友可能會把他當成怪胎。
現在,他把車子停在克雷門特街九六三號。這是一幢小平房,房子漆成白色,有綠色的百葉窗和綠色的矮樹籬。
塔德撥開前額的金髮,把車子推到台階邊,臉上仍然掛著開朗、企盼和美麗的微笑。他把腳踏車的腳架踢下來,停好車子,再從台階下撿起摺疊的《洛杉磯時報》,夾在腋下,走上台階。台階上,隔著紗窗是一扇厚重的木門,門框右首是門鈴,門鈴下有兩個小牌子,整齊地釘在木門上,外面還包上一層塑膠紙,免得牌子發黃或水漬。塔德心想,德國人真是講求效率,他笑得更開朗了。這是成年人才會有的想法,每當他這麼做時,總是在心裡暗暗稱許自己。
上面那塊牌子寫著:亞瑟.但克。
下面的牌子寫著:禁止小販、推銷員入內。
塔德一面微笑,一面按鈴。
他隱約聽見鈴聲在小屋內迴響。他把手指放下,側耳傾聽是否有腳步聲,結果沒聽到聲響。他看看天美時錶(這也是他賣賀卡賺來的),十點十二分。這傢伙該起床了,塔德平常都七點半起床,即使在暑假,依然如此。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他又聽了三十秒,房內依然沒有動靜,他再按門鈴,一面按鈴,一面看著手錶上的秒針,足足按了七十一秒,終於聽到腳步聲緩緩拖啊拖的走過來。塔德從那陣踢躂踢躂聲推斷,來人穿的是拖鞋。他立志長大後要當私家偵探,因為他長於推理。
「來啦!來啦!別按了,來了!」那個假裝是亞瑟.但克的人嚷道。
塔德停止按門鈴。
門內傳來一陣鍊子和門閂拉開的聲音,門打開了。
一個老人馱著背,縮在一襲浴袍中,站在紗門內往外看。他手中夾著香菸,塔德心想,這人的樣子介乎愛因斯坦和卡洛夫(Boris
Karloff,英國演員,因在電影中飾演科學怪人而成名)之間,一頭長長的白髮,而且白中泛黃,那種黃好像尼古丁薰過的那種讓人看了不舒服的黃,而不是象牙黃。他的臉滿佈皺紋,而且因為剛睡醒而略顯浮腫,鬍子已經有好幾天沒刮了,面容可憎。塔德父親常說,「每早刮鬍子,看起來容光煥發。」塔德的父親不管上不上班,每早一定刮鬍子。
看著塔德的那一對眼睛警覺而深沉,不過卻滿佈紅絲,而且眼眶陷落。塔德的失望之情油然而生。這傢伙是有一點像愛因斯坦,也有那麼一點像卡洛夫,但他更像在鐵路調車場附近遊蕩的邋遢老酒鬼。
不過塔德提醒自己,這人才剛剛起床。塔德以前看過但克好幾次(但他都非常小心地確定但克沒有看到他),在公開場合中,但克都打扮得整整齊齊,典型的退休軍官模樣,若是塔德在圖書館看到的出生資料沒錯的話,他已高齡七十有六了。當塔德偷偷尾隨但克去購物或搭公車去看電影時(但克沒有買車),不論天氣有多熱,他總是穿著三件頭西裝,如果是陰天,他一定會把傘捲好,夾在腋下,好像枴杖一樣,他偶爾也會戴一頂呢帽。但克出現在外面的時候,總是把臉刮得乾乾淨淨的,一嘴灰白的短髭也修得整整齊齊(他留短髭的目的是為了遮蓋兔唇。)
「小鬼,」他說,聲音濁重,充滿睡意。塔德瞥見他褪色而寒酸的浴袍,感到更加失望。浴袍的一邊圓領翻了起來,領子上沾上了辣醬或牛排醬,塔德還聞到菸味和酒味。
「小鬼,」他重複道,「我什麼都不要,看看上面的牌子,你認得這些字吧?你當然認得,美國所有的孩子都能認字。別來煩我,再見。」
門正要關上。
他也許會就此算了,事後,塔德曾在晚上睡不著覺時,想起這件事。因為初次這麼近距離看到這個人,看到他卸下了在街上的那副外表(可以說,他把那張臉和雨傘、呢帽一起放進衣櫥了),可能讓他就此打消了原本的念頭。但是,但克觀察的沒錯,塔德是個典型的美國男孩,師長一向教導他「鍥而不捨」是一種美德。
「杜山德先生,別忘了你的報紙,」塔德說,很有禮貌的把報紙遞過去。
門關到一半就停住了,古特.杜山德臉上頓時閃現緊張和戒慎的表情,或許還夾雜著懼怕,但隨即恢復平靜。塔德感到第三度失望,他並沒有預期杜山德是個好人,但他原本期望他很偉大。
天哪!塔德內心生起一股真正的厭惡。
老人再度把門打開,用患了關節炎的手拉開紗門的門閂,然後把紗門推開一點點縫隙,像隻蜘蛛般伸出手來,準備接過塔德手中的報紙。塔德厭惡地注視著他又長又黃的指甲,終日一根接著一根的菸不離手,才會如此。塔德認為抽菸是骯髒而危險的習慣,他絕不要沾染上菸癮。這個杜山德竟然會活這麼久,還真是奇怪。
「報紙給我。」老人說。
「當然,杜山德先生,」塔德鬆開握著報紙的手。滿佈青筋的手把報紙使勁一拉,把門關上。
「我姓但克,」老人說,「不是什麼杜山德,看來你是真不識字,可憐呀!再見。」
門正要關上時,塔德對著門縫嚷道,「一九四三年一月到一九四三年六月,波根貝森集中營,一九四三年六月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奧許維玆集中營──」
快要關上的門又再度停住,門縫中露出老人鬆垮垮而蒼白的臉,像個洩了氣的皮球。塔德微笑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