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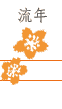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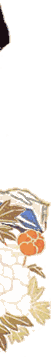
|
姚立群/前實學社主編 v.s 許錫慶/《藏》譯者
姚立群(以下簡稱姚):也是高齡的名作家一次返樸歸真的表現 許:這是因為能在懷舊的題材上,注入新的活力,使自己的創作,不致僵化。
姚:宮尾在這部小說中,運用了大量的古語與方言。就你翻譯的立場來看,這是一種由內而外的風格呢?或者祇是為創造語文的奇觀,所進行的堆砌? 也因為復古的語言,好像要引領讀者更真切地進行文化性的歷史之旅。於是,語言便像一種氣息相符的導覽,渲染更醇的懷舊感覺,提供道地的「美的饗宴」,使讀者走入日本文化的精髓所在,而不祇是光駐足在潮流的表面。 姚:當然,現代潮流的表面是日本,而厚積的底層也是日本── 許:也許可以更大膽地說,這才是「真正的日本」!日本文化界曾有「在東京找不到真正的日本文化」的說法,認為日本文化應該是在超級大都會之外的地區,或者更進一步說,在日本海的這一邊。
姚:不過,以《藏》這部描述過去一段已成終戰前歷史的小說,卻在日本成為暢銷書──這樣的事實,是否祇是恰好與「分眾」的消費有關? 許:無寧說是一種回歸鄉土的新潮流。 姚:新潮流? 許:是新潮流。在長期的西化過程中,強大的西潮把日本人文化的記憶沖淡了。像宮尾等作家就把傳統、鄉土之美,以小說的形式表現出來,使年輕人能體認到自己的文化特質,重新檢視價值觀,尋找新的動力。
姚:宮尾的小說,常常是針對某一專門行業、技藝,先有很深入的田野研究,再加以小說化。《藏》講的是「酒」。酒是日本文化,尤其是常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員,是生活的象徵。 許:酒與文化並不祇在於「飲酒」,尤其在日本,「釀酒」更有等量齊觀的重要性與系統化。釀酒又與鄉土有關,尤其是在日本東北地區,多雪而少污染形成甘甜水質,是釀酒的先天條件,有這些條件才能開始談釀酒。但釀酒的首要因素是人:相信只有勞資一心合體,才能釀成美酒。坊主與酒工全心奉獻、全力投入,才能使流程順遂,沒有差池。 以此來比喻文化的保存,也是很適切的。因為,如果不是全心全力,那麼,一點點人為的疏忽,可能導致前人千百年來費心維護的資產,如同腐釀一夕生成,使得一季、甚至一生的心血都會毀於一旦,無可挽回。 姚:從酒與文化密不可分的關係中,很清楚看到了日本的性別/階級問題;這些問題時至今日仍是普遍存在的。 許:的確還是個問題。在日本那樣重父系威權的社會,女性的地位一直是很低落的,女性主義至今仍不時權充社會大眾說笑話的佐料。但是我們也看到小說中的女性。雖事事與男性有別,卻不全然唯命是從,也就是,平常大概都可以妥協,但碰上某些事情、某些方面,就會表現無比的剛強。以阿烈為例,她以失明的身體狀況,在父親意造心灰意冷之際,主動想一肩挑起釀酒的家業,宿命也好,使命也好,這確實是傳統日本女性,尤其是日本海這一邊,所特有的強韌精神。
姚:阿村、賀穗、佐穗、阿關都在不一同的事情上表現出來。 許:一遇事就把強韌的一面顯現出來──這種強弱的隱現,正把日本文化的層次很巧妙的表現出來。這也是做為鄉土作家的宮尾,深諳文化的特質而展現的功力。 姚:宮尾是否此過於專注,卻忽略掉她的小說所處理的時空背景,其實是一個巨變的時代──這個世紀最初的二、三十年──在中國,正是動盪的大時代,而日本是參與動盪的主角之一。但是「大時代」在宮尾筆下,竟是隱晦不彰的。 許: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就朝著富國強兵的政策挺進,努力成為軍事強權。但老百姓的觀點不盡然與此疊合。離鄉背井去殖民,或有擴展族群生存空間之義,再說軍國主義的立足與日本文化本質也不無淵源,但是在女性沒有參政權的昔日,不免也淪為一種畸形的政策。 姚:所以我們看到一位女性作家的「態度」了──《藏》也許不是激動地怒吼抗議,卻是小說家用全力關注人的生活、文化的細節,清晰、持久地發出聲音。(蘇小平整理) (節自《藏》〈雙邊對談〉,1996,實學社) |
【回首頁】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