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來西亞報上刊載不少我訪問時的照片,其中有些人被蔣家班特務認為是左派份子。回台北後不久,警備司令部就派人詢問我,為什麼在海外專找左派來往。我於是向他們建議:調查局既然有的是錢,最好每年派人出國,帶著給牛馬烙印的烙鐵,把華人分為左右兩派,一一在面頰上烙出印記,這樣的話,政治犯再出國時,遇到烙有「左」字烙印的人,就望風而逃。
新馬回來半年,我接到世界詩人大會將於七月在美國舊金山召開的邀請函,試探著向警備司令部申請出入境證,竟然獲得批准,同樣的由蕭桃庵把出入境證當面交給我,仍是一句「國事維艱,請多體諒」的吩咐。
這是我第一次美國之行,除了發現「大人小孩都會說英語」外,使我最驚訝的是,美國人的禮貌多端(後來才發現日本人的禮貌更為多端),和交通秩序有條不紊,並且了解:斑馬線在此邦竟然有使汽車禮讓的功能,而台灣的斑馬線卻是專門引誘行人深入埋伏,以便汽車撞死的陷阱。
詩人大會後,我在舊金山史丹佛大學、柏克萊大學,以及在洛杉磯,各作一次演講,最後紐約一站演講,安排在孔夫子大會堂,當我再一次把傳統文化形容為「醬缸」時,聽眾中一位先生提出:
「世界各國到處都有唐人街,中國人應該感到驕傲!」
「唐人街不但不是中國人的驕傲,」我說,「應該是中國人的羞恥,看它的髒、亂、吵,和中國人對自己中國人的迫害與壓榨,實在是應該自顧形慚。」
一位聽眾激動的一躍而起,斥責說:
「你從台灣來,原希望你帶來鼓勵我們的好消息,像反攻大陸已經準備完成之類,想不到你卻來打擊華人的民心士氣,羞辱我們祖國。」
我呆了一下,時到今日,竟然還有人相信反攻大陸,實在難以理解,我不是政府官員,也不是文化打手,所以不能撒謊。但這項行動立刻引起嚴肅的關切,紐約《華語快報》在社論上呼籲華人社會對我不可提出尖銳的問題:
柏楊來紐約市,在紐約知識份子圈中,捲起了一個熱潮。不管是右派、左派,或自由派的知識份子,都爭著和他談話,都爭著邀請他舉行座談會,於是柏楊夫婦忙得團團轉。但是也有很多真正愛戴柏楊的讀者,憂心忡忡。
憂心忡忡的原因很簡單,紐約市華人社會,是一個五花八門的社會,在政治上有左、右、中、獨,各種派別,這些人各有各人自己的一套想法,都希望能和柏楊交換意見,從好的地方來看,這是柏楊吸收新看法的一個好機會,但是如就柏楊本身的安危來看,這也可能包含有使柏楊回台灣後再坐九年監獄的危機。
台灣在民主與人權上,最近雖然有一些進步,但是在對付共黨和台獨份子這兩方面來說,常常是有理說不清的。在台北與左派份子接觸就可能是滔天大罪,但在美國來說,和左派份子接觸的機會實在太多了,何況人人都想接近的柏楊。雖然在一次右派舉行的座談會中,我們可以聽出這位對台灣的社會與政治批評很強烈的作家,對共產主義是反對很強烈的。但是柏楊在台灣,也曾被安全方面的工作人員,戴過紅帽子。這一次柏楊接觸了那麼多各種政治意見的人,在公開場合說了那麼多的話,如被斷章取義,要戴他紅帽子,也不是很困難的事。
有的人認為,這是台北方面的錯誤,應該要台北方面改正,不應該自我約束。但也有人認為,如果真正愛護柏楊,便應該為他著想,為他的安全著想,儘量使台北方面不要誤會他。
回台北後的第二年(一九八二),我和香華又去了泰國北部。《異域》寫作的時候,我並沒有親自到過異域現場,寫作的
內容又被忠貞份子指控為挑撥人民與政府之間的感情,這句幾乎在每個政治犯判決書上都會出現的話,是一頂足以致人於死的鐵帽。想不到時代在變,現在反而激起讀者急於追問大撤退後孤軍的命運,《中國時報》副總編輯高信疆先生要我往泰國北部走一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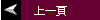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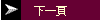
[ 野生動物 ][ 山崩地裂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