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種情形一直到二十世紀八○年代,都還是如此。我出獄後,曾收到海外幾封邀請函,政府當然不准,連在報上登廣告都不准出現柏楊二字,要想拿到出國護照,簡直比登陸月球還難。而且,警備司令部如果不發出入境證,即使拿到外交部一百張護照也沒有用。白色恐怖時代,警備司令部是政府中的政府,能不能出國,它的裁決才是最後定案。
然而,天下事難以預料,在很多邀請函中,新加坡共和國《南洋商報》的邀請函,發生了力量。一九八一年元月份的一天晚上,警備司令部接伴我回台北的蕭桃庵先生,請我和香華吃小館,當場拿出外交部發的護照和警備司令部發的出入境證,這真是又一個意外,蕭桃庵並沒有特別交代,只是告訴我: 「國事維艱,請多體諒!」
去新加坡,並不是我生平第一次出國。一九五七年,我曾經乘登陸艇護送回國參加青年救國團暑期戰鬥訓練的留日和留韓學生,分別送返長崎和釜山。不過,那一次是純公務的旅行,匆匆登岸,又匆匆回船,對日本的唯一印象就是:「哇!大人小孩都會講日本話!」到韓國後雖然對那裡的大人小孩都會講韓國話不再驚訝,不過我實在想不通,世界上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迥然不同的言語,和這麼多稀奇古怪的文字。
這次出國,除了香華同行外,還帶著佳佳,和比佳佳小一歲的香華的女兒碧心。我們受到新加坡讀者熱烈的英雄式的歡迎,人潮洶湧,中英文報紙全幅報導,對一個剛剛從屈辱的監獄出來、還不太習慣自由生活的重刑囚犯而言,簡直不可思議,只有青蛙變王子的童話裡,才有這種強烈對比的奇遇。蔣家王朝加到我身上的迫害,想不到在萬里之外,竟還給我百倍的溫暖和百倍的榮譽,使我終生難忘。
而我的和香華的女兒,更被當地讀者寵昏了頭,以致碧心要求佳佳說:
「妳可不可以跟妳媽媽講,在新加坡多玩幾天?」 佳佳驚訝的叫起來:
「那是妳媽媽,不是我媽媽。」
我們當然不能多作停留,因為行程早已安排。不過,這一趟歡樂的旅行,卻種下了佳佳永遠離開的種子。她在飛機上認識一位澳洲航空公司工作的青年,回台北後,決定放棄她在台灣大學法律系已讀了三年的學業,前往澳洲結婚。我勸她先完成學業,她一心早日離去,父女更生齟齬。佳佳遠嫁後,音訊漸少,終於一年不過一封。
在吉隆坡,我們接受《馬來西亞通報》董事長周寶源先生招待,廣大讀者群的歡迎盛況,簡直使我要再感謝一次幸而有這場長達十年的文字獄。
過去,在「華僑是革命之母」口號的引導下,我總以為東南亞各國華人,是一個強勢族群,現在我親眼看到的,卻不盡然。各地華人在經濟上、商業上雖然佔有優勢,但是卻忽略了文化、政治上的發展,以致稍微有點風吹草動,都會造成不安。馬來西亞建國之初,華人身負「好男不當兵」的傳統文化,拒服兵役,拒進軍校,自己阻止自己成為社會主流。我回台北後,寫了一系列的〈新馬港之行〉,口吐真言,說出我的憂慮。在馬來西亞,有些朋友認為是暮鼓晨鐘,有些朋友則反唇相譏說:「柏楊是老幾?竟跑這麼遠來教訓我們!」
歸途中經過香港,會晤到香港菸草公司總經理何關根先生。一般人印象中,商業和文化不能相容,財富和愛國也幾乎有尖銳衝突,然而,何關根身上兩者融化成為一體。一九六八年,我被捕的兩個月前,那時《異域》一書,正在海外發行。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何關根一信,他對被接到台灣孤軍的悽慘遭遇,深感悲痛,捐出一筆巨款,要我轉交。就在被捕前夕,剛好把它轉發完竣,而且在報上一一徵信。所以這次到香港,第一件事就是拜訪他,向他致謝。何關根不像一位資本家,而像一位教授,他溫文儒雅,指著辦公室牆壁書架,告訴我說:
「你看,這全是你的作品,我已擺了好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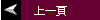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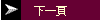
[ 野生動物 ][ 山崩地裂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