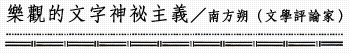
一定有許多人無法理解,看起來不那麼玄奧,而且一般的文學評論裡也似乎很少理會的紀伯倫,他的著作會那麼持久的在全世界,當然包括台灣在內,受到從不衰懈的歡迎。
因此,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圓滿的解釋。紀伯倫的作品到底打動了以前的人和現在的人,哪一根神經?他的作品要被歸類到哪一個範疇才對?
而答案似乎只有一個。那就是紀伯倫乃是當代已愈來愈稀少的「文學神祕主義」最後一顆亮眼的明星,他以一種非常人間性的方式,把希伯萊—-基督教裡的神祕主義,腓立基的古代智慧,以及中東伊斯蘭文化的積澱,做了浪漫熱情的綜合,因而變成一種照亮,一個永恆的叮嚀和啟示。無論淵博的雅士,或是略識之無的俗人,都或多或少能從他的作品裡掬取到一些可以打破人生執迷的活潑泉水。
紀伯倫的老師,法國大藝術家羅丹(Auguste Rodin, 1840-1917)曾說過,紀伯倫和英國神祕主義詩人兼畫家布萊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有著驚人的同質關係。羅丹的這種說法,可以說是所有的紀伯倫的評價裡最精確的一個,也顯示出羅丹確實慧眼如炬,一下子就掌握住了紀伯倫的本質。紀伯倫和布萊克相同,都是「文學神祕主義」裡的智者與勇士。他們對生命有著一種神聖的執著,相信真、善、美的互為一體。在英語裡有一個字vision,它被我們狹義地譯為「願景」,這其實是非常的片面與不準。它真正的涵意是一種帶有神聖、渴慕、虔敬的心,在這樣的心引導下,所看到的世界圖像。布萊克和紀伯倫相同,都給了我們這樣的vision。他們都能詩能畫,他們詩畫同趨,尤其是那些充滿了神祕訊息的繪畫。在繪畫裡,他們都展布出了莊嚴的聖容;讓人足以飛躍的天使與鳳凰之翼,燦爛的生命之樹,以及走在水上火中的聖靈;還有那只飽含著威儀、慈悲、洞燭一切的宇宙之眼。讀他們的文字,如同看他們的圖繪,都會把人帶到一個比現在處境更高一點的新地。
而更驚人相似的,他們正因為有智,因而敢勇。布萊克因智而勇,差一點就被抓走送到英國海外的監獄之島澳大利亞,因此有學者認為如果當時他真的被送到澳大利亞就好了,可以在十九世紀就讓這裡產生文化與心靈的的啟蒙。而紀伯倫因智而勇,致使他的《叛逆的靈魂》被禁,人也被放逐。
這時候,或許我們就必須對什麼叫做「文學神祕主義」先做扼要的理解了。根據近代幾本著名的神祕主義專題著作,例如:荷蘭學者波切特(Bruno
Borchert)的《神祕主義:它的歷史及面對的挑戰》,以及美國學者派克(Nelson Pike)的《神祕的合一:神祕主義現象學論文集》所述,神祕主義乃是人類最初,但同時也是最後的一種疑惑,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想像和思維態度。它相信人的生存不只是具有現實上的意義,世間萬事萬物所顯露出來的也不是只有跟前的這些浮光掠影,一種內在的、合一的因果通路,才是生命更幽微的目的與本質。
而正是這樣的幽微與探索,遂出現了向外和向內的兩種探索的選擇。向外的有神祕主義的宇宙論,神祕主義的物質因果論等等;而向內,則出現了宗教、大自然、現實人生,以及文學上的各種神祕主義。它在這些地方經由特殊的啟示與感覺,希望對世界一體,生命一體能找到本源與最後。而無論啟示來自何處,這種向內發展的神祕主義都有一個共通性,那就是「愛」。「愛」是一種力量、一種意旨、一種目的。這種對「愛」的啟示,在早期的「靈修文學」或「使徒文學」裡都是重要的元素。在近代浪漫主義文學裡,華滋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對大自然做出神聖的歌頌,即是神祕主義的啟示;濟慈(John
Keats, 1795-1821)把真、善、美合一,也同樣洋溢著神祕主義的呼喚,沒有神祕主義、浪漫主義將成為不可能。神祕主義追求的是「神祕的合一」(Mystic
Union),它可以是上帝意旨的與我合一,也可以是人與終極意義「愛」的合一。由於神祕主義在「愛」裡找到意義,幾乎毫無例外的,神祕主義者也必然浪漫、勇敢、有情,以無謂的心情去面對現實世界裡讓愛被扭曲,或者愛因而失去的黑暗部分。
因此,紀伯倫乃是西方浪漫神祕主義,與東方神祕主義匯聚後的結晶。他受到西方浪漫主義的文體影響已毋庸置疑,但非常用功的他,其實也把東西方靈修及使徒文學,希伯萊和伊斯蘭神祕主義,包括《猶太祕典》(Zahar)以及蘇菲派的許多特點交溶了進來。這是一個新的綜合,造就出了他那種獨特的「文學神祕主義」,文字和話語在他的著作裡滾動如珠,撞擊著人們的眼,打動著人們的心。它不是狹義的文字,也不是狹義的宗教,而是新型態的俗世靈修經典,不管你是西方人或東方人。當我們覺得意義喪落、生命倦怠、被疑惑和憤怒所包圍、對現世覺得很無可奈何的時刻,打開紀伯倫的書,總會得到他的幫忙與照顧。
紀伯倫在《行列聖歌》裡說道:「我的上帝、我的目標、我的成就啊,我是你的昨天,你便是我的明天。我是你地下的根,你便是我天上的花。我們迎著太陽生長在一起。」這段話的重要,乃是因為它反映出了紀伯倫神祕主義的那個基本前提,那就是人要到自己的裡面,去找那個大寫的名字。而後始能像他在《淚與笑》裡所說的,可以免於「一旦失掉了崇高的靈魂,就成了存在於物質世界中的行屍走肉」。
因此,他要的人生是一種昇華的人生,在《草原上的新娘》裡即說道:「我們是在向著更高的思想境界迅速昇華。在那種境界裡,我們將通過心中的情感來了解世界的美,通過我們對美的熱愛來追求幸福。」而「幸福,就是上帝的意願在人類身上的體現。」
神祕主義有兩種,一種是「神祕的沉寂」,它就像是早期教父聖多默(St. Thomas Aquinas,
1225-1274)一樣,在被神祕啟示後,有懍於人類的渺小,即轉趨沉寂,甚或去做離世棄事的隱士,獨自修行。聖多默在被啟示後,對他正在寫的《神學大全》即告廢筆。但紀伯倫並非如此,他不斷地受到啟示與感動,因而他選擇去做一個使者,去宣揚啟示的道理,要和眾生分享。他鼓吹與神聖的那個大名字合一,要用高尚聖潔的心去膜拜自然,找尋真善美的境界。他歌頌愛情,讚揚平等博愛,而對會讓心靈沾染塵埃的不公不義、自私自利,以及壓迫欺侮,則元氣凌厲地加以反抗。積極向善,謙卑自抑,對人可能變成上帝的影子充滿孺慕情懷,而對天主之國可以透過奮鬥而在人間體現,則又努力地要使之成為真的期待。紀伯倫被人們所喜歡,這豈是偶然的嗎?

 烈火焚燒、寒冰淬鍊的靈魂/王季慶(中華新時代協會創辦人)
烈火焚燒、寒冰淬鍊的靈魂/王季慶(中華新時代協會創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