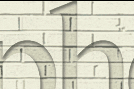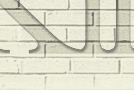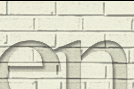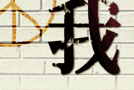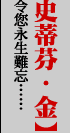【5】
星期六上午早餐時間輪到我的班,我必須去豪優克餐廳洗碗部上工。排到這個班很棒,因為學校餐廳在星期六早上永遠都很清閒。負責洗銀器的女孩凱若站在輸送帶的最前端,我排第二個,工作是當輸送帶上的餐盤經過我面前時趕緊抓住餐盤,把它堆到身旁的手推車上。如果輸送帶上的髒碗盤太多,週末晚餐時間就是如此,那麼我只需把盤子堆起來,等到輸送帶的速度放慢時再說。接在我後面的是「玻璃杯男孩」,他們負責把杯子挑出來,放在洗碗機的格子裡。在豪優克打工還不錯,偶爾朗尼會突發奇想,在沒吃完的香腸上套個保險套,或把餐巾紙撕成細長條,在裝麥片的盤子裡拼出「我上的是一所爛學校」幾個字(有一次,他在湯碗上面用醬汁寫著:救命啊!我被關在笨蛋大學裡);還有,你不會相信有些年輕孩子有多惡劣,簡直就是豬──他們在盤子上擠滿番茄醬,在牛奶杯裡塞滿馬泥薯泥、碎蔬菜──但這份工作真是不差,尤其是星期六早上。
有一次,我的目光越過凱若(清晨的她顯得格外美麗),落在史托克身上,雖然他背對著我們,不過身旁的柺杖和外套背上的圖案都十分醒目。艦長說得沒錯,那圖案看起來像羊腸小徑(一年後,我才第一次在電視上聽到有個傢伙形容這圖案為「偉大的美國膽小鬼之路」)。
「你知道那是什麼嗎?」我指著那邊,問凱若。
她看了很久,搖搖頭說:「不知道,一定是在開玩笑。」
「史托克從不開玩笑的。」
「噢,你是詩人,而你居然不曉得。」
「別這樣,凱若,別瞎說。」
下班後,我陪她走回宿舍(我對自己說,我只不過展現紳士風度罷了,陪凱若走回法蘭克林舍並不代表我對安瑪麗不忠),然後自己再慢慢走回錢伯倫舍,一直思索著誰會知道那羊腸小徑代表什麼意思。直到現在才想到,當時我完全沒有想到要去問史托克本人。走上三樓時,眼前的景象讓我完全拋開剛剛腦子裡想的事情。在我清晨6點半出門、睜著惺忪的睡眼站到凱若身邊工作之後,有人把刮鬍霜抹在大衛的房門上──門邊、把手都塗滿了刮鬍霜,門下面還塗得特別厚,地上有赤腳踏過的痕跡,我不禁莞爾。大衛身上只圍了一條浴巾,他打開門、準備去洗澡,然後一推門!哇!
我笑著走進302室。奈特坐在桌前寫東西,看到他曲著手臂擋住筆記本,深怕我看到,我推測他正在寫信給辛蒂。
「有人在大衛門上塗刮鬍霜。」我一邊說著,一邊走到書架前抓起地質學課本,計畫去三樓交誼廳為星期二的小考稍做準備。
奈特想要裝得嚴肅一點,露出不贊同的神情,但還是忍不住笑了。他當年老是想要表現出一副義正詞嚴的樣子,但總是不太成功。我想經過這些年應該有些改進了,但這樣更令人覺得悲哀。
「你實在應該聽一聽他的叫聲,」奈特說,他哼哼笑了幾聲,然後把拳頭塞進嘴巴,阻止自己進一步發出不得體的笑聲,「還有連連咒罵的聲音──那個時候,他變得和艦長那夥人一樣。」
「說到罵人,我不認為有任何人比得上艦長。」
奈特擔心地皺著眉頭望著我。「你沒有參一腳吧?因為我知道你一大早就起床了。」
「如果我想裝飾一下大衛的房門,會用衛生紙,」我說,「我的刮鬍霜都會塗在自己臉上。我和你一樣是窮學生,記得吧?」
奈特這才舒展眉頭,恢復唱詩班男孩的神情。這時我注意到他身上只穿著短褲,戴著那頂該死的藍色扁帽。「很好,」他說,「因為大衛一直嚷嚷著要把做這件事的人揪出來,看著他受罰。」
「只因為塗抹他的房門就要受罰,我很懷疑。」
「聽起來不可思議,不過我覺得他是認真的,」奈特說,「有時候大衛會讓我想到那部關於瘋船長的電影,亨佛瑞•鮑嘉演的,你知道我說的是哪一部吧?」
「知道,你是指《叛艦喋血記》。」
「嗯,而大衛,這樣說好了,他當舍監就是為了享受發放留校察看通知的快感。」
根據校規,退學是大事情,只有像偷竊、搶劫和持有毒品或吸毒等重大違規行為,才會遭到退學處分。留校察看則是次一級的處罰。如果你把女生留在房裡過夜(當時過了女舍宵禁時間後還把女生留在房裡,就有瀕臨退學的危險,這在今天簡直是難以想像的事情),或在房間裡喝酒、考試作弊或抄襲等,理論上,後面幾項違規都可能遭到退學處分,考試作弊通常都會被退學(尤其是如果你在期中考或期末考作弊的話),但其他違規的處分多半只是留校察看一個學期,我很不願意相信舍監會因為一個無傷大雅的玩笑,而向校方申請對學生處以留校察看的處分……但這就是大衛,他這個人一板一眼,直到現在還堅持每個星期檢查宿舍每個房間,他總是隨身攜帶一個小凳子,這樣才可以查看32個櫥櫃上方的架子上擺了什麼東西,似乎覺得這些櫥櫃也是他職責的一部分;這些觀念可能是從後備軍官儲訓團那兒得到的,他愛死了後備軍官儲訓團,就好像奈特愛辛蒂和靈弟一樣。還有他會把內務不佳的學生名字記下來──當時內務檢查還是學校的正式規定。雖然除了在後備軍官儲訓團之外,大多數人都置之不理,但如果你被打了太多叉而留校察看的話,理論上,你有可能因此遭到退學處分,失去緩役資格,然後收到兵單,最後落得在越南戰場上躲子彈。而這一切全因為你老是忘記倒垃圾,或沒把床底下掃乾淨。
大衛也是靠獎學金和助學貸款上大學的學生,他的舍監工作理論上和我在餐廳洗碗沒什麼兩樣,不過他的理論可不是如此。大衛認為自己因此高人一等,屬於精挑細選出來的少數菁英。他是東岸人,你知道,法爾茅斯人,那兒直到1966年,還承襲了50幾條清教徒訂下的藍律。後來,大衛家遭遇了一些變故,因此家道中落,就好像以前舞台上演的通俗喜劇情節一樣,但是他仍然打扮得像法爾茅斯貴族學校的畢業生,每天穿著法藍絨運動衫去上課,星期日則穿西裝上教堂。他和有一張賤嘴、充滿偏見卻精通數字的朗尼簡直南轅北轍,每當他們在走廊上擦肩而過時,你幾乎可以看得出來大衛拚命縮回身體,對朗尼避之唯恐不及。朗尼滿頭糾纏不清的紅髮下是一張奇醜無比的臉孔,隆起的兩道粗眉下是那雙永遠睜不開的瞇瞇眼和永遠流著鼻水的鼻子……更別提他的嘴唇永遠都那麼紅,好像塗抹了平價商店買來的便宜化妝品似的。
大衛不喜歡朗尼,但是朗尼不需要獨自面對大衛的嫌惡,因為大衛似乎討厭所有受他監管的大學生。我們也不喜歡他,朗尼更毫不掩飾對大衛的憎恨,科克艦長對大衛的嫌惡則帶著點瞧不起的味道。他和大衛一起在後備軍官儲訓團受訓過(至少直到11月艦長退訓為止),他說大衛除了懂得拍馬屁之外,其他什麼都不會。而艦長呢,他高三的時候,就已經差一點獲選為全州高中棒球明星球員。艦長最討厭我們舍監的一點是──他不認真。在艦長眼中,這是最嚴重的罪行。即使你只是在餵豬,也要認真一點。
我和其他人一樣討厭大衛,我能夠容忍許多人性的弱點,但是很討厭愛吹牛皮的人。不過我有一點同情大衛,因為他完全沒有幽默感,相信這也是一種殘障,和史托克下半身的殘疾沒有兩樣。此外,我也不認為大衛喜歡自己。
「只要他查不出這件事是誰的傑作,就不會有留校察看的問題,」我告訴奈特,「即使他找到作案的人,我懷疑蓋瑞森學務長會同意對學生施以這樣的重罰,只不過因為他把刮鬍霜抹在舍監房門上。」不過大衛有時候很有說服力,也許他已經被貶為平民,卻仍然帶著上層階級的傲氣。當然,這是另外一個我們討厭他的原因。艦長叫他「快走男孩」,因為在後備軍官儲訓團受訓時,大衛從來不會真的在足球場上奔馳,他只是快步走。
奈特說:「只要不是你做的就好。」我幾乎要大笑起來。奈特穿著內褲、戴著扁帽坐在那兒,孩子氣的狹小胸部上看不到任何胸毛,只有些微斑點和一身瘦排骨。他熱切地看著我,扮演著老爸的角色。
他壓低聲音問我:「你認為是艦長做的嗎?」
「不是。如果真要猜三樓有哪個人會把刮鬍霜塗在舍監房門上來表示不滿,我猜是──」
「朗尼。」
「對。」我用手對準奈特比著手槍,然後眨一眨眼睛。
「我看到你和那個金髮女孩一起走回來,」他說,「凱若,她很漂亮。」
「只是陪她走一段而已。」
穿內褲、戴扁帽的奈特坐在那兒微笑,一副他比我還清楚的表情。也許確是如此。沒錯,我喜歡凱若,雖然我對她了解不多──只知道她是從康乃狄克州來的。這裡沒有幾個半工半讀的學生是從別州來的。
我手臂下夾著地質學課本,往交誼廳走去。朗尼戴著扁帽坐在交誼廳裡,他把前面的帽緣別了起來,看起來好像戴著軟呢帽的新聞記者。另外兩個也住三樓的傢伙──休斯和艾胥利──則坐在他旁邊。他們一副百般無聊的樣子,朗尼看到我時,眼睛一亮。
「彼特!」他說,「我正要去找你!你知道怎麼玩紅心牌戲嗎?」
「知道啊!幸好我也知道該怎麼用功讀書。」我舉起地質學課本,心裡想著也許應該去二樓交誼廳念書……如果我真的想念點書的話。因為朗尼總是說個不停,他顯然沒辦法閉嘴,簡直就是一台自動說話機。
「別這樣嘛,只要玩一局就好,」他猛灌迷湯,「一個積分算五分錢,這兩個傢伙玩起牌來簡直像老頭子做愛一樣。」
休斯和艾胥利只顧傻笑,彷彿朗尼剛剛是在恭維他們。朗尼損人的時候往往口無遮攔、尖酸刻薄,因此大多數人聽了只當他是在開玩笑,甚至以為他是明貶實褒。其實他們都錯了,朗尼損人時,字字句句都是真心話。
「朗尼,我星期二要小考,而且我實在看不懂所謂的『地槽』是啥鬼東西。」
「去你媽的地槽。」朗尼說,艾胥利在旁邊偷笑。「你還有今天大半天和明後天一整天可以讀你那個什麼他媽的地槽。」
「但是我星期一有課,而且艦長和我明天要去舊市區,我們──」
「住嘴,別說了,饒了我吧,別和我說這些鬼話。聽我說,彼特──」
「朗尼,我真的──」
「你們兩個沒用的東西待在這兒別動!」朗尼狠狠瞪了他們兩個一眼,兩人一聲也不敢吭。他們可能和我們一樣今年十八歲大。但是每個上過大學的人都會告訴你,每年九月,大學校園裡總會出現一些特別幼稚的十八歲大學生,在比較鄉下的州尤其如此。朗尼在這類大學生中特別吃得開,他們對他十分敬畏。他會拿走他們的餐券,在浴室裡用毛巾打他們、指責他們不該支持馬丁路德黑鬼(朗尼會告訴你,他開著捷豹汽車去示威遊行)、向他們借錢,而且任何人向他借火,他一律回答:「屁啦!」儘管如此……而且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愛死朗尼了。他們愛他,正因為他是如此……有大學生的樣子。
朗尼一把抓住我的領子,拚命把我拉到走廊上好私下聊一聊。我一點也不怕他,而且想避開他腋下的濃濃異味,於是努力扳開他的手指,推開他的手。「別這樣,朗尼。」
「噢、噢、噢,好、好、好!只要過來一下就好了嘛,可以嗎?不要這樣扳我的手指,很痛耶!?而且這是我打手槍用的那隻手!天哪!他媽的!」
我鬆開他的手(我很懷疑他自從上次打手槍以後有沒有洗過手),但還是任由他把我拉到走廊上。他抓住我的手臂,浮腫的眼睛睜得大大的,熱切地對我說:「這兩個傢伙根本不會玩牌,」他氣喘吁吁地和我說著悄悄話,「他們是一對呆頭鵝,但都很愛玩紅心牌戲,簡直愛死了,你知道嗎?我不愛玩,但和他們不同的是,我懂得怎麼玩。而且我破產了,而今天晚上學校禮堂要放映兩部鮑嘉的片子,如果可以從他們身上榨出兩塊錢來──」
「鮑嘉演的片子?其中一部是《叛艦喋血記》嗎?」
「沒錯,《叛艦喋血記》和《梟巢喋血戰》,鮑嘉最好的片子,就在那兒等著你,甜心。如果我可以從這兩個笨蛋身上榨出兩塊錢來,就可以去看電影;如果我可以弄到四塊錢的話,就會打電話邀法蘭克林舍的女生一起去,說不定看完電影後還可以爽一下。」這就是朗尼,總是浪漫得一塌糊塗。我的腦中浮現出他好像《梟巢喋血戰》中的史貝德般,叫愛斯特讓他爽一下的畫面,單單想到這件事,就足以讓我血脈賁張。
「但是有一個大問題,彼特。三個人玩紅心很危險。當你還得擔心那張剩下的牌時,誰敢放膽射下月亮呢?」
「你們怎麼玩?看誰最先得一百分,所有的輸家都得付錢給贏家?」
「對,如果你加入的話,我會把我贏的分數減半計算,同時把你輸的錢都還你。」他對我投以聖人般的溫暖微笑。
「萬一我贏你的話呢?」
朗尼似乎大吃一驚,然後咧開嘴笑了,「甜心,你這輩子都別作夢了,說到玩牌,我可是專家。」
我瞄了一下手錶,然後瞥了艾胥利和休斯一眼。他們看起來的確不像我的對手,上帝愛他們。「這樣好了,」我說,「只玩一局,玩到積分達到一百分為止,一分算五分錢。不需要誰讓誰,我玩完這局就去念書,大家都過個快樂的週末。」
「歡迎加入牌局。」走回交誼廳時,他又說,「我喜歡你,彼特,但是咱們公事公辦──你高中時代的同性戀男友絕對沒辦法像我今天早上這樣,帶給你這麼多樂趣。」
「我高中時代沒有交過任何同性戀男友,」我說,「而且我週末多半都搭便車去路易威登幹你老妹。」
朗尼咧開嘴笑了,他坐下來拿起桌上的紙牌,開始洗牌。「我把她調教得不錯,對不對?」
你就算說破嘴也說不過朗尼,他的嘴巴比誰都賤。很多人都試過,但是就我所知,沒有人真的成功過。
(譯者/齊若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