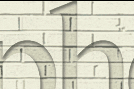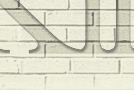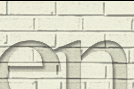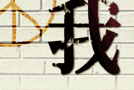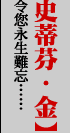【4】
我的室友不玩紅心牌戲。對於尚未宣戰的那場遠在越南的戰爭,我的室友奈特發揮不了一絲作用。奈特每天寫信給還在威斯登中學讀高三的女朋友。把一杯水放在奈特旁邊,那杯水會立刻顯得比奈特還要生氣盎然。
奈特和我一起住在302室,就在樓梯旁邊,正對著舍監的房間(討厭的大衛住的獸窟),和走廊另一端的的交誼廳遙遙相對──那裡擺著撲克牌桌、菸灰缸,還可以遠跳曠野上的宮殿。至少對我而言,我倆的組合表示大家對於大學宿舍的許多可怕想法都是真的。1966年春季,我在寄給緬因大學住宿處的問卷上(當時我滿腦子想的都是畢業舞會結束後,是不是應該帶安瑪麗去吃點東西)寫著:第一,我有抽菸的習慣;第二,我是共和黨員;第三,我對民謠吉他有高度熱忱;第四,我是夜貓子。結果住宿處卻糊裡糊塗地把我和奈特分在同一個房間,奈特就讀牙醫系,不抽菸,而且他在亞如斯托克郡的家人都是民主黨員(儘管詹森也是民主黨員,奈特卻不會因此贊同美國士兵在越南四處征戰)。我的床頭貼著亨佛瑞‧鮑嘉的海報;奈特的床頭則貼著狗和女朋友的照片。他的女朋友臉色蒼白,身上穿著威斯登中學樂隊指揮的制服,手上抓著好像短棍的指揮棒。她叫辛蒂,那條狗叫靈弟。女孩和狗都同樣誇張的咧開嘴笑,真是離奇的很。
在我們看來,奈特最讓人受不了的地方就是,他會小心翼翼依地將唱片照字母順序排列在架子上(就在辛蒂和靈弟的照片下面、小巧可愛的RCA
Swingline唱機正上方)。他有三張米契‧米勒的唱片(《和米契同唱》、《再度和米契同唱》、《米契和幫派樂團演唱約翰‧亨利及其他美國人最喜愛的民謠歌曲》)、《遇見區妮‧洛佩玆》,還有狄恩‧馬丁的唱片、蓋瑞與前導者合唱團的唱片,以及戴夫克拉克五人組的第一張唱片(這或許是有史以來最吵的一張爛搖滾唱片),另外還有許多同類唱片,我沒有辦法全部記得,而這未嘗不是件好事。
「奈特,不要這樣,」有一天晚上艦長說,「喔,拜託,不要。」那是紅心狂熱開始之前沒多久的事,也許只是幾天以前。
「喔,拜託不要什麼?」奈特問,他坐在書桌前,頭抬也不抬。他醒著的時間幾乎不是在教室上課,就是坐在桌前苦讀。有時候我會逮到他挖鼻孔或(把唱片徹頭徹尾詳細檢查後)在抽屜下面偷偷摸摸地擦拭唱片,那是他唯一的缺點……如果不計較他可怕的音樂品味的話。
艦長曾經檢查過奈特的唱片,他每次到別人房間,都會毫不自覺地開始這麼做。現在他拿著其中一張唱片,表情就好像醫生正在研究一張看起來不太妙的X光片……上面可以明顯看到腫瘤的陰影(而且幾乎可以確定是惡性腫瘤)。他站在奈特的床和我的床中間,穿著繡有高中校名的外套,頭上戴著高中棒球帽;我在大學裡從來沒有碰過比他還帥的典型美國大男孩,以後也很少碰到。艦長似乎一點也沒有意識到自己長得好看,但是他不可能完全不曉得,否則怎麼會經常有女生投懷送抱。雖然在那個時代,幾乎任何人都可以找到願意上床的對象,但即使照當時的標準,艦長仍然比別人忙碌。不過在1966年秋季的時候,這一切都尚未開始。1966年夏天,艦長和我一樣,整顆心都放在紅心牌戲上。
「這張唱片很爛,小老弟。」艦長帶著溫和的、斥責的語氣說,「很抱歉這麼說,但是真的很爛。」
我坐在自己的書桌前一面抽著寶馬香菸,一面忙著找我的餐券。我老是找不到那張該死的餐券。
「甚麼東西很爛?你為什麼翻我的唱片?」植物學課本攤開在奈特前面,他頭上歪戴著大一新生的藍色扁帽,正在一張紙上畫著葉片。我相信奈特是唯一會一直戴著這塊愚蠢藍色抹布的大一新鮮人,他會一直戴到緬因大學倒霉的足球隊終於達陣得分為止……那要到感恩節前一星期左右。
艦長繼續研究那張唱片。「這張唱片真是爛到家了!」
「我很討厭你這樣說話!」奈特嚷著,但仍然頑固地不願抬起頭來。艦長知道奈特很討厭他這樣講話,這正是為什麼他要這樣講話。「你到底在說什麼呀?」
「很抱歉我的話惹你不高興,但是我不會收回剛剛的意見,沒辦法,因為這張怀。
唱片真的很爛,爛得讓我心痛,小老弟,爛得讓我心痛啊。」
「什麼?」奈特終於氣得暫時放下正在畫的葉子,抬起頭來,那片葉子被精心刻劃得好像蘭德麥克納利地圖集一樣。「什麼呀?」
「這張。」
艦長手中握的那張唱片封套上的女孩有一張生氣盎然的臉孔,水手領罩衫下高聳著活潑的小小雙峰,似乎在甲板上跳舞。她高舉著手臂,伸出手掌,微微揮著手。頭上則戴著一頂小小的水手帽。
「我打賭你是全美國唯一會把《戴安雷奈唱海軍藍調》這張唱片帶來學校的大學生,」艦長說,「這樣是不對的,奈特。你應該把這張唱片和維納褲一起束諸高閣,我打賭你都是穿著這種褲子去加油大會和參加教會活動。」
如果維納褲指的是那種後面有著毫無用處奇怪釦子的桑斯貝特合成纖維便褲,我猜奈特應該把大部分的唱片都帶來了……因為奈特當時正穿著一條那樣的褲子。不過我什麼話也沒說。我拿起裝了女友相片的相框,發現餐券就在後面,於是抓起餐券塞進牛仔褲袋中。
「那張唱片很好,」奈特義正詞嚴地說,「那張唱片非常好聽,帶著搖擺風格。」
「是嗎?」艦長問,把唱片扔回奈特床上。(他不肯把唱片重新歸位,因為他知道這會讓奈特抓狂。)「『我男朋友說喂,船哪,於是加入海軍』?如果這就是你對『好』的定義,提醒我永遠不要讓你開刀。」
「我以後會當牙醫,不是醫生。」奈特咬牙切齒地說,脖子上青筋畢露。就我所知,在錢伯倫舍,或許在整個校園中,只有科克艦長有辦法惹我室友生氣。「我念的是牙醫預科,你知道牙醫預科的牙代表什麼意思嗎?代表牙齒!艦長,那表示──」
「這倒提醒我了,絕對不要讓你補牙。」
「為什麼你老是要說這種話?」
「什麼話?」艦長問,他明明知道奈特是什麼意思,卻偏要聽到奈特親口說出那句話。奈特終究會說,等到他終於說的時候,整張臉總是脹得通紅。艦長覺得有趣極了,奈特的點點滴滴都讓艦長覺得十分有趣。他有一次告訴我,他還滿確定奈特是外星人,從一個叫「好男孩」的星球降落到地球上。
「他媽的!」奈特說,他的臉頰立刻紅了起來,不一會兒就像極了狄更斯筆下的人物,《博玆隨筆》中描繪的熱情年輕人。
「壞榜樣,」艦長說,「我簡直不敢想像你將來會怎麼樣。萬一保羅‧安卡東山再起怎麼辦?」
「你從來沒有聽過這張唱片,」奈特一邊說著,一邊從床上抓起《戴安雷奈唱著海軍藍調》的唱片,把它放回米契‧米勒的唱片和《史黛拉戀愛了》中間。
「我從來都不想聽這張唱片。」艦長說。「走吧,吃飯去,我他媽的快餓扁了。」
我拿起地質學課本──下星期二要小考。艦長從我手中把書拿走,放回書架上,敲敲我女朋友的相片。她不肯和我上床,但是心情好的時候會幫我打手槍,讓我爽得不得了。信天主教的女孩在這方面最內行了。隨著年齡增長,我對許多事情的想法都改變了,唯有這個想法一直沒變。
「你幹嘛把書拿走?」我問。
「不要在他媽的餐桌上看書,」他說,「即使吃的是學校餐廳裡的殘羹剩飯,都不要邊吃邊看。你到底是在什麼樣的穀倉裡蹦出來的?」
「事實上,艦長,從我出生以來,我的家人真的會在餐桌上看書。我知道你很難相信除了你的做事方式外,別人還有其他的做事方式,但是的確如此。」
他看起來十分嚴肅,他抓著我的手臂,凝視著我的眼睛,然後說:「至少正在吃飯的時候,不要念書,好嗎?」
「好吧。」我在精神上保留了我愛在什麼時候看書(或覺得什麼時候需要看)、就什麼時候看書的權利。
「繼續這樣過日子,你會得胃潰瘍,我老爸就是得胃潰瘍死的。他就是停不下來,拚命往自己腦子裡塞東西。」
「噢,真是遺憾。」
「別擔心,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走吧,免怀。得菜都被吃光了。要不要一起去呀,奈特?」
「我得把這片葉子畫完。」
「去他的葉子。」
如果是其他人這樣說的話,奈特會瞪著他,好像翻開朽木時看到了什麼東西一樣,然後就靜靜地繼續忙著手邊的工作,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他考慮了一下就站起來,小心翼翼地把掛在門後的外套拿下來。他穿上外套、戴好帽子,連艦長都不敢對他執意要戴這頂新鮮人扁帽表示什麼意見。(我問艦長,他把帽子丟到哪兒去了──當時是我到緬因大學的第三天,也是我認識他的第一天──他說:「我拿來擦完屁股後就丟到樹上了。」(他也許沒說實話,但是我也從來不敢完全排除他這樣做的可能性。)
我們連下三級階梯,走到10月的薄暮中。學生紛紛從三棟宿舍裡走出來;往豪優克餐廳走去,我每個星期在那裡打工9次,擔任洗碗工。錢伯倫舍和法蘭克林舍的地勢比較高,曠野上的宮殿也一樣。學生要從宿舍到餐廳的時候,都要走一條凹陷的柏油路,彷彿狹長的地槽一樣,然後才連接到寬闊的紅磚道,繼續往上爬。豪優克餐廳是四棟建築物中最大的一棟,在暮色中閃閃發亮,彷彿大海中的巡洋艦。
柏油路交會的窪地叫做班奈特小徑──即使我曾經曉得這個名字從何而來,也早已忘得一乾二淨了。金恩舍、錢伯倫舍的男生分別從兩條小路走過來,法蘭克林舍的女生則走另外一條小路。到了三條小路交會處,男生和女生一邊說說笑笑,一邊大膽或害羞地四目交接,然後再從那裡一起踏上寬闊的班奈特紅磚道往餐廳走去。
史托克從對面走過來,低著頭穿過人潮,蒼白的臉上掛著他一貫拒人於千里之外的表情。他長得很高,不過你幾乎看不出來,因為他總是弓著背、拄著柺杖,烏溜溜的頭髮(幾乎看不到一絲淡色頭髮)覆在前額上,把耳朵蓋住,還有幾撮頭髮斜披在蒼白的臉頰上。
當時正是披頭四的髮型最流行的時候,年輕男孩都小心翼翼地把頭髮往下梳,而不是往後梳,讓頭髮垂下來遮住額頭(以及臉上一堆青春痘)。史托克的頭髮倒沒有整理得如此一絲不苟,他那頭中等長度的亂髮愛往哪兒跑、就往哪兒跑。他的背弓得太厲害了,即使現在還不是永久性的駝背,可能很快就會變成永久性駝背了。他的眼睛通常都往下看,彷彿在追蹤柺杖揮動的弧線。如果他剛好抬起頭來與你四目相接,你很容易被他狂野銳利的目光嚇一大跳。他是新英格蘭的希斯克利夫,只不過從臀部以下只剩下兩根瘦排骨。他去上課的時候,雙腿通常都包在巨大的金屬支架中,就像垂死章魚的觸鬚般,只能勉強移動。相形之下,他的上半身十分粗壯,形成了怪異的組合。史托克就好像健美先生亞特拉斯的廣告,只不過健身前和健身後的身影似乎全融合在同樣的身體中。每天豪優克餐廳一開門,他就去吃飯,開學不到三個星期,所有人都知道他這麼做不是因為他是殘障,而是因為他和葛麗泰‧嘉寶一樣喜歡獨處。
「他媽的!」有一天我們一起去餐廳吃早餐時,朗尼說──他剛剛和史托克打招呼,而史托克只是拄著柺杖自顧自往前走,連頭都不點一下。朗尼不停地小聲喃喃自語,而我們都聽見了,他說:「跛了腳、跳著走路的混蛋!」朗尼就是這樣,總是「如此」充滿同情心。我猜他是在路威斯登的里斯本街上髒兮兮的小酒館裡長大的,他溫文的舉止和獨特的魅力大概也是這種環境薰陶下的產物。
「史托克,上哪兒去啊?」有一天晚上,史托克拄著柺杖往我們這邊疾走過來時,艦長問他。史托克不管到哪兒,都是這樣拄著柺杖猛往前衝,布魯扥般魁梧的上半身往前傾,好像船首裝飾的人頭像一樣,無論下半身踩到什麼東西,史托克會不停地罵「他媽的」、不停地比中指,用他那聰明狂野的眼睛瞪著你,嘴裡不停罵髒話。
他沒有回答,但是抬起頭來,兩隻眼睛盯著艦長,然後把臉一垮,匆匆地從我們身邊走過去,汗珠順著一頭亂髮滴落臉頰。他悶聲發出「哩噗-哩噗,哩噗-哩噗」的聲音,好像計時器一樣……或許他的嘴裡是在咕噥著咒罵我們的話……或許兩者皆是。你可以聞到他身上的味道:刺鼻的汗臭味,他身上老是帶著汗臭;因為他不肯走慢一點,叫他走慢一點彷彿冒犯了他,但他身上還有其他味道。汗臭味雖然刺鼻,卻不討厭,但底下混雜了另外一種更難聞的味道。我高中的時候是田徑選手(一上大學就被迫在寶馬牌香菸和參加田徑隊之間做個抉擇,我選擇了棺材釘),曾經聞過那種特別的味道,通常是某個學生明明感冒了或喉嚨發炎,卻還硬要來練跑時,就會出現那種味道,唯一比較相似的味道就是當電車的變壓器使用過度時,也會散發出這種味道。
然後卸下腿部支怀。架的史托克就從我們身旁經過,往宿舍方向走去。不久以後,朗尼就為史托克取了「哩噗」的綽號。
「嘿,那是什麼?」奈特問,他停下腳步,轉頭往後望。我和艦長也停下腳步,轉過頭去。我正要問奈特他是指什麼,然後就看到了。史托克的外套背上好像用黑色奇異筆畫上什麼圖案,在初秋薄暮中,只能看出好像畫了個圓圈的形狀。
「不曉得,」艦長說,「看起來好像是一條羊腸小徑。」
拄著柺杖的男孩沒入十月的星期四晚上去餐廳吃飯的人潮中。大多數男孩都把臉刮得乾乾淨淨,女孩子則大半穿著水手衫和裙子。今晚幾乎是滿月,月亮冉冉上升,橘色的月光灑在這群年輕孩子身上。兩年後,嬉皮的盛世才真正來臨。而在那天晚上,我們三個人都沒有意識到,那是我們生平第一次看到和平標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