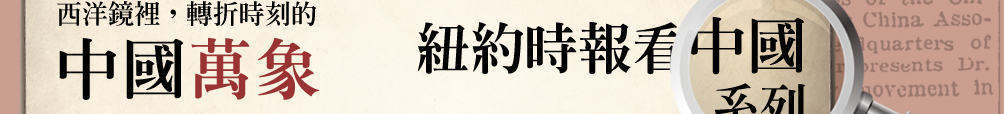|
| 民國以後,雖然各省都下令禁止種植罌粟,但還是有不少地方陽奉陰違。圖為福建省永春縣正在公開焚燒吸食鴉片的煙具。 |
《追蹤罌粟》(On the Trail of the Opium Poppy)
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五日
題記:文科碩士、法學博士、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謝立山爵士(注1)著,本書共兩卷,由波士頓斯莫爾與梅納德出版公司(Boston: Small, Maynard & Co.)出版。
在過去十五年裡,中國一直在與鴉片惡魔作鬥爭。中國革命也對禁止鴉片生產起到了猛烈攻擊的作用。罌粟漿汁在遼闊的中國大地上作惡多端。中國通過了禁止種植罌粟的法律,這部法律中許多條款都意義非凡,各省都下令禁止種植罌粟,許多省嚴格遵照執行。中國人也因此部分地擺脫了罌粟的危害,但危害並未根除。有一些省對禁止種植罌粟的法令陽奉陰違,照種不誤,而且把大量罌粟運到中國各地。
謝立山爵士曾任英國駐天津總領事,他決心調查各省種植罌粟的情況。從一九一○年到一九一一年,他兩次到中國主要罌粟產地,親眼目睹了這些地區在中國政府頒佈禁令後種植罌粟的情況。他在厚厚兩卷《追蹤罌粟》中,以坦率直白的口吻講述了兩趟旅行的經歷。
本書在作者所宣稱的調查目的外,還有更多閱讀價值。因為謝立山爵士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其他一些有趣的材料,他寫到旅行的艱辛、中國內陸城鄉人民生活、奇特的地方習俗和生活方式,以及對中國工業、產品和貿易發表的評論等。毫無疑問,在西方人看來,中國是所有國家中最特別的。歐美人士從哲學和宗教角度審視中國人時會發現,不僅在生活方式上,而且在精神世界方面,中國人也與他們完全不同。到中國內陸旅行幾乎是行走在另一個星球。
革命中斷了禁煙的進程
謝立山爵士一九一○年對華北三省的調查結論是,山西省已完全消滅了罌粟種植,陝西省和甘肅省的種植量比一九○七年分別下降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二十五。而一九一一年,在西南三省中,四川省罌粟種植已絕跡,雲南和貴州的罌粟種植量分別下降百分之七十五和百分之七十。謝立山爵士還說到,罌粟禁令取得顯著成就,但卻被一九一一年十月的革命打斷了。
革命發生後,中央和地方政府失去控制權,一時間無力阻止,罌粟種植又死灰復燃。人們不禁好奇,如果今年再進行一次中國內陸之旅會有什麼新的發現。謝立山爵士觀察了被政府官員援助、輔導的平民百姓對此問題的看法,得出結論是,要使萬惡的鴉片絕跡於世,還需要幾十年而非幾年的努力才能實現。中國人對鴉片的渴求已成為種族特徵之一,鴉片的誘惑超過酒精。人人皆知,要想徹底禁止鴉片需要跨越無數障礙。
中國的罌粟花有各種顏色
謝立山爵士行走於中國六省調查這小小的罌粟花時,經歷許多困難,讀來饒有興味。也許我們應該先描述一下罌粟花。
「中國罌粟花有各種顏色,以白色為主,但粉色、深淡不同的紅色和紫色都十分尋常。各省種植罌粟的季節也不同。在西南各省,人們在十月末或十一月初播種。四川的罌粟三月開花四月熟。雲南、貴州要比四川晚一到兩個月。在西北各省,如山西、陝西和甘肅,罌粟六月開花七月熟。
「用不著多解釋大家都知道,罌粟花花瓣凋謝後,蒴果成熟,切開表皮流出漿汁,即可提煉鴉片。印度人將罌粟花細心收集起來,用來製作包裹鴉片丸的外殼。而中國人把罌粟花直接扔掉。蒴果的切刻有時是水平的,但更多是垂直的。人們在一個短木柄上嵌入三到四片平行排列的小刀片,僅露刀鋒在外,足夠劃破蒴果,但又不會刺穿蒴果內壁。
「在浙江省一些地方,人們使用一種類似於木匠鉋子的小工具,從下往上割破蒴果,只有罌粟花底部還殘留蒴果的表皮。每個蒴果都可在間隔一定時間後再次劃開,如此反覆幾次。按規矩,這些活動都在夜間進行。漿汁剛流出時呈乳液狀,帶一絲粉紅色,而後變成深褐色,最後變成黑色。人們在早上將它們收集起來。收集鴉片的男女或兒童通常用一塊扁平的竹片將罌粟汁漿濃縮成的生鴉片刮到碗內或竹筒中,讓它暴露在空氣裡,多餘的水分將蒸發掉。如有急用,可通過加熱方式烘乾。」
想深入中國內陸是件非常困難的事
中國鐵路很少,營運狀況不太好,開通線路也少。通常情況下,旅客們無法乘火車到達目的地。謝立山爵士為此組建了一支旅行隊,這是在中國內地旅行唯一合適的方式。他常常需要應付政府官員造成的麻煩,因為他們試圖勸說爵士按他們設計好的線路走,那麼他幾乎發現不了罌粟田了。謝立山爵士下決心要獨立完成調查,不許地方官的勸告或他們沿途的刁難阻礙他達到目標。
他的旅行隊由一輛騾車與七匹騾子,以及若干管家、趕騾人組成。四個趕騾人中有二人負責駕駛騾車,另二人負責照管五匹馱運行李的騾子。駕駛騾車非常辛苦,由二人輪流趕車。負責馱運行李的人騎在騾子上,常常搖著搖著就睡著了。正如謝立山爵士所說,「趕騾子的人在上面搖來晃去,讓人看了心驚肉跳。但據我一路觀察,他們從沒失掉平衡摔下來過。」
騾車實際上是一頂大轎子,不由人?著,而由二匹騾子扛著。為避免隨身攜帶太多銀兩,謝立山爵士帶了許多地方錢莊的銀票。熟知中國貨幣的人應該知道,如果謝立山爵士攜帶銀兩和銅錢的話,那麼他這趟旅行大概需要再加上五匹騾子來馱。
一位衣著考究的士紳走過來,正告他此地沒種罌粟
漫長旅行的目的就是要觀察罌粟種植地,逐一記錄並按省分類。儘管謝立山爵士遇到的地方官都保證中國已不再種植罌粟,但他在旅途中還是找到了一些罌粟地。他幾乎沒法更加深入內陸,但仍盡可能接近他計劃要去的地方,而且找到不少罌粟,這讓他很滿足。有時,罌粟地裡還種植著其他作物,如豆類等,來為種植罌粟打掩護。
在大勞山(譯注:位於陜西省延安市甘泉縣境內)一個小村旁,謝立山爵士有過一次有趣經歷。當他走進鄉村旅店的房間時,老闆娘正試圖趕緊擦掉屋子裡陳積了好幾年的灰塵。謝立山爵士連忙從雲霧中逃出來,讓老闆娘把飯菜端到旅店後面露天場壩上食用。他吃飯時,突然看到眼前山谷裡有塊地正種著他熟悉的植物。爵士走過去,發現種的就是罌粟,面積大約有三分之一英畝。他採下一朵罌粟花放進口袋裡,而後返回旅店。
當謝立山爵士準備與自己的旅行隊起程離開這裡時,一位衣著考究的士紳走過來,神情嚴肅地告訴他,這個地方沒種植罌粟。謝立山爵士說,那就奇怪了。然後,他從口袋裡掏出那朵罌粟花。好奇圍觀著洋鬼子的村民們大笑了起來。這位衣著考究的士紳迅速轉身離開。
罌粟種植是公開的祕密,但中國人不希望外國人打探
謝立山爵士遇到的大多數中國人都不願談論種植罌粟的事,總是很小心地將話題引向別處。罌粟種植看起來在中國已是一個公開的祕密,但中國人不希望外國人四處打探。政府官員的態度有些不同。他們談論罌粟,但大部分人都堅決表示,罌粟種植已經絕跡,或已大大減少,幾乎可被忽略。
謝立山爵士來到西安府時,受到陝西巡撫的殷勤招待。謝立山爵士向他打聽前往渭河河谷的道路是否安全。巡撫回答,這一路很安全,但建議只走大路。巡撫提供了好幾條不同路線,但每條路線都小心地避開了渭河河谷。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即當地政府不希望謝立山爵士對那一帶進行調查。事實果真如此,他後來發現河谷裡大量種植著要命的罌粟。
謝立山爵士在漫長的旅途中時常會發現大片罌粟種植地。但大多數時候都只是小塊種植。謝立山爵士在總結陝西調查情況時說,他第一次去陝西,發現了九百八十八片罌粟地。第一次到甘肅發現五百九十五片罌粟地,第二次發現二千零三十六片。
謝立山爵士在蘭州時兩次會見陝甘總督長庚。總督告訴謝立山爵士,甘肅的罌粟種植面積當年減少四成。謝立山爵士輕描淡寫地說,僅在通往總督府沿途十英里內,他就發現了一百八十片罌粟地。總督聞之感到有些驚慌。謝立山爵士相信,總督對轄區情況並不了解。這說明有相當數量的政府官員的確對消滅罌粟雄心勃勃。不過,從謝立山爵士的書推斷,他們的雄心壯志極少落實到行動中。任務交付給了下級官吏,但這些小官吏對禁止種植罌粟並無興趣。
謝立山爵士的書,大部分章節都是據事直書的遊記,書中不時穿插著這樣或那樣的軼事,處處可見中國人的幽默。
《追蹤罌粟》是一份廣泛且可靠的調查報告,對於那些想要了解新中國的生活狀況及現代化運動的人來說,應該極有用。讀者可從書中查到大量資料,這些資料都經過精心挑選,以有趣方式展示給讀者。書中還有兩篇關於事件簡介的附錄及富有啟發意義的插圖,為本書增添了閱讀價值。
【注1】謝立山(Sir Alexander Hosie, 1853-1925),1867年進駐華領事界做翻譯學生,1881年為駐重慶領事。曾多次在華西旅行,搜集了許多商業和博物學資料,後在溫州、煙臺、臺灣等地任代理領事和領事。1893年發表一份關於臺灣的重要報告。1902年4月,首任英國駐成都總領事,後曾任英國駐華使館商務參贊。1908年出席在上海舉行的萬國禁煙會議。1909~1912年任駐天津總領事。後脫離駐華領事界,1919年復被召回,任使館特別館員。著有《華西三年》(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 A Narrative of Three Journeys in Su-ch’uan, Kueichow and Yun-nan)、《滿洲》(Manchuria: Its People, Resource and Recent History)、《追蹤罌粟:中國主要產煙省分旅行記》(On the Trail of the Opium Poppy: A Narrative of Travel in the Chief Opium-producing Provinces of China)、《四川的物產、實業和資源》(Sze-chwan: Its Products,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等書。
——摘自《共和十年(下):〈紐約時報〉民初觀察記(1911-1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