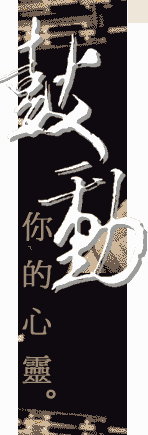

|
打擊樂的學習之路 台灣有一句俗諺說:「做人最衰--剃頭、打鼓、吹鼓吹 」,意指在傳統社會的價值觀中,「打鼓」這項工作,是不被尊重,也不會有什麼前途的。也因此,台灣的父母,尤其是早期社會中的父母們,大概都會反對自己兒女以此作為終身的職志吧。 我在鄉下經營小生意的父母,顯然對於這樣的說法不很「敏感」,不但是長了二歲的哥哥很早就開始學習爵士鼓,而且當我升上國立藝專四年級,並且決定將主修改為「打擊樂」的時候,他們雖然沒有特別加以鼓勵,但是也完全沒有絲毫反對的意思。這在當時那個風氣還不十分開放的社會中來說,已經是十分難得的了。 所以,就打擊樂的啟蒙來說,我是幸運的,不僅僅享有父母的完全尊重,讓我可以「為所欲為」地選擇報考藝術學校-國立藝專就讀,而且就在藝專遇上了當時的音樂科主任史惟亮老師,並且在他的推薦與鼓勵之下,朝著「打擊樂」的領域發展。也因為這樣的機緣與栽培,才有可能有今天的我,和我所創立的所有「打擊樂」相關團體與組織,以及今天全台灣數十萬的打擊樂學習與欣賞人口。 回想起來,學習打擊樂過程中最苦的時候,便是我在維也納進修的那段日子,包括體力與精神上的苦,只是,那些實在還是自找的,因此所有的苦都得自己吞嚥,不能回頭。 去維也納之前,我已經在台灣省立交響樂團擔任打擊樂首席有段時間了,要堅持拋下安穩的職位與生活,要到異地深造,「勸退」我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幸而自己相當頑固,父母和哥哥又願意全力支持,才終於成行。老實說,我在機場就已經有些後悔了,面對家人依依不捨的心情,以及對於那一個陌生城市的恐懼感,再加上飛機延誤了四個小時,我又因為不知名的原因整天都身體不適,其實心理是有點想著要放棄,甚至已經開始向航空公司探聽回國的班機,所幸是因為沒有飛機可以回家,所以我「不得不」飛往維也納。 可是當我終於抵達學校,理所當然的要進教室潛心學習之際,出現了第一個大問題-教授認為當時二十五歲的我「太老了」,因此根本不願意收我為學生。 這是個始料未及的困頓,被潑了一桶冷水的我只覺得難過得想要立刻收拾行囊返家,可是心理上又不願意這麼輕易的退卻,總覺得當初是反抗所有人的疑慮而出國的,長輩的紅包也收了,親友們送行的飯也吃了,如果才剛剛開學就回家,面子上實在掛不住。幾番思索後,我決定留下來「奮戰」。 如果教授不收我為學生,那麼我就旁聽吧! 勤快的我每天出現在教室裡,跟著眾人一起學習,我相信我不比任何一位學生差,只是上課的機會永遠輪不到我,我只有在一旁旁聽的份。有一天,有位同學缺席,教授空出了一堂課的時間,便要我頂替試試,我的表現讓教授極為「驚艷」,他對我高度讚賞,而我也自傲的回他一句:「我一直都很棒,祇是你不給我機會而已!」自此之後,我終於成為正式的學生,正式如願成為華特懷格教授的門下。 學習的挫折不少,但是因為相信勤能補拙,所以我總是以加倍於他人的努力,保持學業上的優異成績。不過有一次挫敗經驗,是讓我印象深刻的。那是一次與當地台灣留學生所組成的同學會一起到養老院去演出,還記得演出的是由巴哈A小調小提琴協奏曲改編的木琴協奏曲,才演出沒多久,我就發現自己因為太過緊張,竟然把樂譜忘光了。我幾乎可以說是倉皇的把曲子「混過去」,而我相信台下那些長年浸淫於古典音樂的老先生老太太們,也都知道台上的這位黃皮膚黑頭髮的年輕人,已經演出失常了,只是因為修養夠好,他們還是很用力的鼓掌。 雖然聽眾沒有苛責,我自己卻自責不已,甚至又出現了「放棄、回家」的念頭。拖著沮喪的步伐,我走進一家咖啡廳,坐下來點了一杯咖啡靜靜的啜飲,想著要如何善後,該如何面對自己和家人的期盼。半個小時的冷靜後我想通了,這不過就是一次演出失敗吧,等到我二十年後再看看這件事,它便顯得無足輕重,我又何必要在這個時候這樣的為難自己呢。 一但把關照的時間拉長,就發現一個現在看來不得了的挫折,原來也不過是長長的人生中的一點點,濃度根本就太低,沒有掛意的必要。這樣的想法影響著往後我所有對人對事的態度,每當我的學生、團員、工作夥伴們因為挫折,而跑來向我訴苦的時候,我便告訴他們這樁歷史事件,鼓勵他們把自己的感受放淡,把時間放長,那麼天下就沒有什麼大不了、不能解決的事情了。 想來,這竟是一杯咖啡的功效呢,讓我體悟到了一項重要的人生道理,以及繼續在那個冰天雪地的國家繼續唸書的動力。而老實說,咖啡也是讓我有了「辦樂團」想法的原因之一。 記得當留學生時,經費很拮据,也不知爸爸媽媽和哥哥是哪裡籌到的錢讓我繼續唸下去的,因此每一分一毫都不敢浪費。那時僅有的一點點娛樂,除了去看一場演出,就是存一點錢到咖啡館,點一杯咖啡,坐一個下午。我並不是對咖啡有著極度喜好的人,上咖啡館其實是為了那一種說不上來的舒坦氣氛,彷若是時間在那裡是停滯的,沒有人大聲喧嘩,沒有人急促的灌下一杯咖啡只是為了提神,人人總是神態自若,悠閒極了。 我總認為,這樣的悠閒與自在,才真的是人應該追求的生活-閒暇時,可以去聆聽一場好的音樂會、喝一杯咖啡,而不要太在意賺了多少錢、完成了多少事。所以在維也納的就學期間,我興起了辦一個「好樂團」的念頭,這樣的想法醞釀了一陣子,一直到我終於拿到文憑,要回國之前,我才認認真真的擬出十五年計劃,並且在回國的三年半後,創立了「朱宗慶打擊樂團」,讓打擊樂在台灣萌芽、茁壯,而終於有了今天的規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