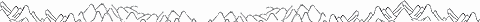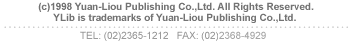與子偕行 文/楊南郡
1933年夏天,一個身材矮胖、戴著熱帶探險帽(Safari hat)、穿著卡其布探險裝、身背大背包的日本年輕人,在台東渡船場入口,滿身大汗焦急地打聽前往蘭嶼的船期。
這時候,街角陰涼處有個阿美族青年,正在悠閒的享受午後薰人的海風,順便與過往的年輕姑娘隨意調笑以消磨漫漫長夏。
這個阿美青年無論穿著、氣質,都與一般「生蕃」不同,照田中薰教授後來所描述的,他「身穿深藍色的水兵服,下著軋比丁緊身褲、頭上斜戴著寬邊草帽,皮膚黝黑,活像個美國南方的爵士樂手。」
在調笑的空檔,他偶然瞥見那個在烈日下奔走,穿著奇怪的「非洲獵人服」的日本青年,一時好奇心發作,就上前搭訕。
 原來,這個戴著眼鏡、相貌忠厚、言談誠懇的日本青年,是剛自東京帝國大學理學部畢業,專程回台灣作動物調查研究的鹿野忠雄。為什麼說「回台灣」?因為他原本就在台灣長大,當他就讀於台北高等學校時,已經在雪山山脈、中央山脈等高山上,留下無數足跡,並曾經到蘭嶼調查珍貴的昆蟲與動物。
原來,這個戴著眼鏡、相貌忠厚、言談誠懇的日本青年,是剛自東京帝國大學理學部畢業,專程回台灣作動物調查研究的鹿野忠雄。為什麼說「回台灣」?因為他原本就在台灣長大,當他就讀於台北高等學校時,已經在雪山山脈、中央山脈等高山上,留下無數足跡,並曾經到蘭嶼調查珍貴的昆蟲與動物。
這回到台灣,鹿野忠雄有更大的雄心壯志,希望作一套完整的台灣動物體系,並旁及於地質的、人文的研究,因為沒有一種學術是可以孤立的,身為一個真正的學者,他需要更多的相關資料來支持自己的學術研究。
因此,鹿野忠雄在台東渡船場附近奔忙,除了詢問船期,最重要的是要打聽是否能找到個通曉日語的「蕃人」,作為他的嚮導、翻譯兼研究助手。
太巧了,這個外表浪漫又散漫的阿美青年,竟然能說一口道地的京都日語,而且出語如珠、言談不俗。這偏僻的東台灣,竟然有這樣受過高等教育的「蕃人」?兩人言語相投一見如故,立刻相約第二天一起上都巒山採集標本,四夜五天的都巒山之行,更加深彼此的好感。之後,在鹿野忠雄博士長達九年的台灣高山田野調查行動中,這個名叫「托泰.布典」(Totai
Buten)的瘦高阿美青年,一直忠心耿耿地擔任不支酬的助理,如影隨形地陪伴鹿野忠雄跋涉千山萬水,甚至包括諸多處女峰的攀登,擔負起獵捕野獸的責任,並就地剝製成標本。
鹿野忠雄能縱橫於台灣高山地帶,廣泛地進行生物地理、冰蝕地形與人類學的實地調查,並留下至今無人能超越的學術經典,托泰也應該有一分功勞吧。
被鹿野忠雄暱稱為「阿美將」(Amijan,日語「阿美小子」,含有親密之意)的托泰.布典,其實是阿美族與平埔族的混血兒,他的祖父是荳蘭社的阿美族,入贅於花蓮加禮宛社平埔部落,生下他父親不久,就在一次日常的巡田水工作時,慘遭鄰近的泰雅族出草馘首。
托泰四歲時,牠的父親為了逃避徵召,半夜裏把他送到祖母處寄養,從此行蹤不明。祖母養了他幾年,深感年邁無力再撫養,就把他送到花蓮東大寺作小沙彌,這個小沙彌因為聰明機靈頗受住持賞識,特別送他到日本京都佛教花園中學唸書。在那兒,托泰除了每日研習佛教教義外,也讀了英文和日文課程,在課餘,更學習京都紈褲子弟追求時髦的惡習,漸漸地變成一個浮誇青年,兩年後就輟學返台了。
回到台灣不久,找到了失散多年的父親,這時他父親已再娶了一位富有的寡婦,因此能供給托泰寬裕的生活。二十出頭的托泰就整日遊手好閒,不是與堂兄流連在Cafe(日式小酒吧)的醉夢鄉,就是在台東街頭遊蕩,憑他的時髦打扮和風趣談笑招引年輕女子,任意揮霍黃金般的歲月……
對鹿野忠雄來說,一九三三年夏天那偶然的一遇,帶給他往後的調查研究極大的幫助;而對托泰來說,那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捩點--在他23歲這一年,隨著28歲如兄長般的鹿野忠雄上山,親自感受到鹿野忠雄對學術的執著與對生命認真的態度,大大地震撼了他空虛的心靈。他為自己的淺薄行為和浪擲生命感到羞愧,當即決心洗心革面,並且堅拒任何酬勞地追隨鹿野忠雄,協助他進行研究工作。
一個是樸實無華、木訥寡言的學者,一個是言語風趣擅唱浪漫情歌的原住民,一個矮胖、一個高瘦,這兩個外形和性情南轅北轍的年輕人,竟然互相吸引,建立了情同手足的主僕關係。
 鹿野忠雄在37歲那一年,被徵召前往北婆羅洲參加太平洋戰爭,由於他當時已有相當的學術地位,駐軍司令也對他禮讓三分,任他深入叢林進行熱帶昆蟲及原始部落的研究。兩年後,他在一場激烈的叢林戰中失蹤,一般相信這位正值盛年的學者,是因為長住部落潛心學術研究而對部隊調動命令無動於衷,因而被一名暴躁的日本憲兵以違抗命令槍殺了。鹿野忠雄博士留下無數未完成的研究,讓後生學者既仰慕又嗟歎。
鹿野忠雄在37歲那一年,被徵召前往北婆羅洲參加太平洋戰爭,由於他當時已有相當的學術地位,駐軍司令也對他禮讓三分,任他深入叢林進行熱帶昆蟲及原始部落的研究。兩年後,他在一場激烈的叢林戰中失蹤,一般相信這位正值盛年的學者,是因為長住部落潛心學術研究而對部隊調動命令無動於衷,因而被一名暴躁的日本憲兵以違抗命令槍殺了。鹿野忠雄博士留下無數未完成的研究,讓後生學者既仰慕又嗟歎。
今年春天,正在拍攝「台灣野鳥百年紀」的劉燕明,想要加入一段台灣原住民鳥占的畫面,我原本希望臉上帶有刺青的泰雅老人「哈隆.烏來」能擔任畫面的主角,出發前卻得知他因膝蓋舊傷復發無法走動。這時,劉克襄適時寄給我另一個阿美族老人陳抵帶的信件,囑咐我們順道過去看看牠是否適合擔任鳥占人?
初看陳抵帶寫給劉克襄的信時,我又驚又疑,又興奮又汗顏:身為鹿野忠雄的景仰者,三十年來我追隨他調查的腳步,在高山冰蝕地形旁印證他的發現,在文獻中蒐集有關他的言行與研究成果,卻從來沒有想過要尋找當年與他共同登山的原住民,是的,就是這個名字!他曾經出現在田中.薰教授的書中,談到這個阿美將很會唱山地情歌,在陪伴學者們從事田野調查時,把卑南族的情歌教給泰雅族,並且將歌詞譯成日文,讓日本的登山隊帶回去廣為流傳。
是的,托泰就是陳抵帶,這個當年瀟灑浪漫的阿美小子,如今應是83歲的老人了,他還在嗎?這封信是兩年前寄出的,無論如何,我必須到花蓮縣壽豐鄉去找他!
出乎意料的,托泰健壯得很,他換上阿美族的傳統禮服,頭戴羽飾讓劉燕明拍攝紀錄片(這一段紀錄片後來並未用上。)由於此行是以劉燕明的影片拍攝為主,並沒有太多時間訪問有關鹿野忠雄的事蹟,但是托泰從言談中看出我對鹿野忠雄博士的景仰與瞭解,高興之餘,很大方地借給我四本研究台灣山地部族的書,這些書都是一口子有盛名的當代日本學者,來台探訪托泰時送給他的。
我利用一個夏天,把托泰借給我的四本書仔細看完,然後就趁著還書之便,專程前去拜訪他。托泰所住的部落,阿美名是理那凡社(Rinafum),漢名光榮社區,是鯉魚潭山南邊的一個偏僻的小村,托泰住在這裏卻一點也不寂寞,因為每年都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學者,懷著孺慕的心情,遠離家鄉,寄宿到托泰的家裏,以一個月或兩個月的時間,進行各自的語言學、民族或民俗的田野調查工作。「就像屋簷下的燕子,每年都固定會來的。」托泰笑著說:「有一回來了一大群燕子,是日本正成大學的教授帶領的二十個學生,他們知道我家不夠住,就自帶了帳蓬,紮營在前院,一日三餐都在院子裏自行炊煮。」對於這些青年學人來說,這位記憶鮮明、活潑健談的阿美老人,他的離奇身世與豐富閱歷,就像一個挖掘不盡的學術寶藏。
剛與托泰寒暄完畢,他就直截了當的說:「我樓上有房間,是專門為來研究學問的年輕人準備的,現在正好有空,晚上你可以在這裏過夜,但是我不供應三餐,部落裏也沒有飲食店,牆邊那一輛腳踏車可以借你騎到壽豐街上去用餐。」
直覺的反應是這個老人未免太不近情理,我到任何村落去訪問時,不管認識與否,村人起碼都會招呼說:「吃飽沒?來跟我們一起吃飯吧!」只有這個托泰先生這樣小器,還要把話說在前頭?
除了不請吃飯這一點之外,托泰可算是一個熱情的好主人,他的記憶力尤其驚人,事件的來龍去脈講得清清楚楚條理分明,連分析能力與見解也都有獨到之處,原來他自從擔任鹿野忠雄的調查助手之後,經過鹿野的介紹,又認識了田中薰、國分直一等知名學者,因而視界大開,托泰的別名「木魚」就是當時擔任台南女子高校教師的國分直一所取的。
「托泰是一種樹的名字,布典是一種魚的名字。國分直一就開玩笑地稱呼我為木魚,我想,我當過小沙彌,被稱木魚也挺合適的。」目前已經信奉基督教的托泰。仍能夠以日語背誦當年留日時所學的金剛經、法華經,他的記憶力真令人歎服。
「鹿野先生是我見過最善良的人,」托泰在回憶時,習慣性地閉上眼睛,甚至把兩個手掌覆在臉上,語氣緩慢而感性,與他方才的輕快談話判若兩人。「他常常說,動物的生命也是很珍貴的,我們為了要研究,不得不殺生,但是射殺前要注意,每種動物最多不要超過二隻。」
自從有了托泰以後,鹿野忠雄就不再自行捕捉動物了,托泰以原住民天生的獵人血液和敏銳眼力,獵捕的效率高多了。「通常,我用陷阱捕捉小動物,用弓箭射鳥,只有大型的哺乳動物才用獵槍射殺。」托泰得意地說:「我的技術是很好的,差不多每射必中,因此,每次在瞄準時,鹿野忠雄先生就關心地說:『阿美將,你要看清楚,這種動物的標本是不是已經有了,有的話就不要再射了』」。
一九三三年夏天,都巒山之行後,托泰正式地成為鹿野忠雄的助手,有生以來第一次登上三千六百多公尺的南湖大山,當時同行的還有神戶商科大學副教授,同時也是著名的地理學家田中薰,以及十多個原住民挑夫,照片上的托泰布典,已經和鹿野忠雄同樣戴著「沙伐利帽」,穿著一式的「非洲獵人裝」,所不同的是托泰腰間掛著成排的子彈,並持著一把村田式步槍,與其他衣著襤褸甚至袒胸露背的挑夫們截然不同,看得出來,鹿野忠雄確實把托泰當兄弟一樣看待。
「我是讀過英文的,」這是托泰另一個足以自豪之處:「鹿野先生帶上山的書啊、藥品啊,上面都是英文字,我絕對不會搞錯,比如鹿野先生說:『阿美將,這個標本要泡在酒精裏。』我就不會拿來福馬林,他要查閱的書,跟我說書名,我就找出來給他。」
當時,不要說原住民,就是一般漢人有托泰這樣的學歷的也不多,難怪他在光復後,曾經坦任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辦事員,並親眼目睹二二八事件的爆發,同時,他也是台灣實施地方自治後壽豐鄉的首任鄉長。
「鹿野先生真是好人,他在得知前去南洋之後,就安排我到台北帝國大學理學部動物系工作,專門製作動物標本。」後來,托泰還擔任台北帝大文政學部言語學研究室的蕃語研究助手,難怪現任東京大學的言語學教授土田滋博士,要特地前來向這一位阿美老人請益。
「鹿野先生完全沒有架子,他跟我們番人一起吃飯一起睡覺,我們喝酒唱歌的時候,他就在旁邊靜靜的聽,他很尊重每一個部族的習俗。除了蘿蔔之外,他什麼東西都吃……他對每一個人都好,但是他非常討厭日本警察的官僚作風,他拒絕駐在所日警提供的乾淨宿舍,寧願住在番人的家……大家看他研究成果那麼豐富,以為他是天才,其實我感覺他是很遲鈍的,比如說,長老在對他說明某些習俗或地形時,他常常請人家暫停一下,把手按在額頭上,閉著眼睛想了好一陣子,再請人家繼續說下去。」啊,難怪托泰在回想過去時,也會有閉目扶額的動作,原來這個習慣是六十年前被鹿野忠雄傳染來的。
「鹿野先生比別人認真多了,他在高山上喜歡走別人沒走過的路線,他的膽子很大,常常走到斷崖邊緣去拍照和觀察地形,紮營後他叫大家儘早休息,自己卻在營地四周到處走動觀察,每天晚上都在帳蓬裏寫筆記,一定要把這一天內所有得到的資料和想法都記下來才睡覺……鹿野先生上山很少有計劃,他最不喜歡日本警察隨行保護,因為他想到那兒就走到那兒,最長的一次,我們曾在高山上待了三個月,糧食快吃光時,就叫蕃人下山去取,一點也不擔心是否會斷糧……他的穿著非常樸素,天氣冷的時候就穿上高等學校時穿的學生外套……」托泰還在侃侃而談時,一直很少說話的太太過來叫他吃飯。
「那麼,楊先生你也先去吃飯吧!」
「不必了,時間不太夠,我在院子等你吃完午飯時再來談。」不知不覺,已經談了一天一夜再加上一整個上午,托泰果然像一個挖掘不盡的寶藏,對於六十年前鹿野忠雄的事蹟巨細靡遺地珍藏在記憶裏。我感覺有很多故事還沒說出來,實在捨不得浪費一個多小時的寶貴時間專程去壽豐吃午餐。
我在院子裏遙望中央山脈,回想托泰所說約有關鹿野忠雄的事蹟時,一直不曾與我交談過的托泰太太,怯生生地走過來:「楊先生,不吃飯不行的,你來跟我們一起吃吧。」推辭再三還是勘不過她,只好跟隨她走進兼作餐廳的廚房。
眼光剛接觸到桌面,我立即明白了,難怪托泰一直不肯讓客人同他一道吃飯,原來他們夫婦倆吃得多麼地簡單!整個桌面上只擺著一小碟蒸瓜子肉和一碗絲瓜湯,七十幾歲瘦小的托泰太太靦腆地解釋說因為她血壓太高不能吃鹽,所以不方便招待客人。托泰似乎對太太的多事有點不以為然,輕輕地哼了一聲就自顧自地只吃那一碟瓜子肉。我儘量節制地和托泰太太分吃那一碗沒有鹹味的絲瓜湯,心中有一點撞破人家隱私的不安。
 吃過飯後,可能有一種同甘共苦的親切感,托泰忽然拍拍我的肩膀說:「楊先生,你跟我到樓上去,我讓你進入我特別的房間,有一個特別的故事要告訴你。」受寵若驚的我,立即跟著他上樓,看他掏出鑰匙,打開一間霉味撲鼻的房間。
吃過飯後,可能有一種同甘共苦的親切感,托泰忽然拍拍我的肩膀說:「楊先生,你跟我到樓上去,我讓你進入我特別的房間,有一個特別的故事要告訴你。」受寵若驚的我,立即跟著他上樓,看他掏出鑰匙,打開一間霉味撲鼻的房間。
看起來已經有幾十年沒動過的房間,牆壁連灰都不曾抹,壁上、牆角到處堆著老舊的器物、藤籃、陶甕、魚網、炊釜……以及一張破舊的沙發。托泰坐在沙發上,顯現非常安適恬和的神態。「我常常自己一個人坐在這個房間裏回想過去的種種一些懷念的人和事,伴隨我這個八十幾歲的老人。因為和鹿野忠雄博士的結識,使我的一生比別人更值得。現在我已經很老了,楊先生,有一個六十年前的故事,是關於我年輕時荒唐的羅曼史,這件事情我從來沒有告訴過別人,連我太太也不知道,現在我要說出來,讓你知道鹿野先生是怎樣的人。
「一九三三年九月,我和鹿野先生、田中先生到南湖大山去調查圈谷地形,我們在山上停留十天,發現了十二個圈谷以及圈谷下的冰磧石堆堤,收穫非常豐盛,下山後,田中薰教授回台北,我和鹿野先生就轉往雪山山區、司界蘭溪旁的志佳陽社,鹿野先生要在這裏觀察櫻花鉤吻鮭的生態,另外,我們還由志佳陽攀登雪山和劍山,當時劍山還是處女峰呢!
「我們在志佳陽足足停留了兩個月,除了登山、採集標本、觀察地形,還作高山水池和溪流的水溫及水質測定,每天都很忙碌,但是也非常快樂。
「泰雅族跟阿美族言語是不通的,起先我跟志佳陽社的族人也不熟,我們都用日語講一些簡單的話而已,但是,因為我特殊的穿著與風趣的性格,很快的就博得泰雅少女們的好感,每天晚上她們都成群的來到我們住的地方,央求我說故事給她們聽,或教她們唱山地情歌。
「其中有一首原本是卑南族的情歌,最受大家喜愛,我把它翻譯成日文歌詞教她們唱,大家都百唱不厭。歌詞是這樣的:
伊保樹下的女孩呀,
小米祭已經快要到臨了,
妳為什麼還在哭泣?
歐嗨呀汗,歐嗨呀汗,歐嗨呀汗,
歐灣耐耐喲,耐耐喲!
不參加月下跳舞,
就不讓你娶這女孩,
也不給你吃小米糕。
來吧,喝小米酒,跳舞吧!
歐嗨呀汗、歐嗨呀汗、歐嗨呀汗,
歐灣耐耐喲,耐耐喲!
「鹿野先生也很喜歡這首歌,因為這首歌讓他想起了住在大甲溪旁久良栖社,他的泰雅族女朋友。當志佳陽的泰雅族少女齊聲學唱的時候,鹿野先生有時會向我借『籮勃琴』(泰雅族的口琴)為大家伴奏。
「這些少女們之中,有一個跟我特別要好,當我們住了兩個月,即將離去時,我為她唱了這首別離之歌:
我所愛的人,我的愛,
我們曾經約好要一起去走那一條山路,
但是別離的日子已經到了,
不知何時能重回妳的身邊?
請妳耐心地等我,直到我回來,
啊,分手的時刻到了,
明天早晨,我們就要離開了。
「我們正在淚眼相對依依不捨的時候,突然外面人聲鼎沸,志佳陽社頭目和駐在所警察,帶著幾十個族人怒氣沖沖地走過來。原來當天傍晚,有個族裏的年輕獵人被山豬咬成重傷,經人抬回部落後,頭目立刻判斷這是部落的不祥預兆,一定要找出不祥的原因,作法消除,才不會造成更大的災禍。
「通常不祥都是來自外人的侵入,部落裏的外人就只有鹿野先生和我,可能為了要保全鹿野先生,駐在所的日警主管率先把矛頭對準我,厲聲地質問我:『是否與部落少女發生了不當的戀情?』鹿野先生立刻代替我回答說:『即使有,也是純潔的友情,絕對沒有男女之間的曖昧情事。』
「由於日警的質問,引起泰雅族人的共鳴,一時之間大家都認定了我是造成部落不祥的原因,即使平常口若懸河的我也百口莫辯。
「從前為了跋除這種不祥,部落必須出草去獵一個人頭來祭祀,但是由於日本總督府嚴厲禁止,加上駐在所主管在場,頭目不敢提出獵首的要求,於是要求以獵殺一頭水鹿或山豬來判定我是否有罪。頭目蠻橫地下令說:『以槍定奪,女方家族明日上山,在三日內如獵不到野獸,就是有不正當的男女關係,要罰托泰交出十圓!』
「鹿野先生也大聲地說:『好,就這麼辦:如果獵不到野獸,罰金由我來負責!』
「大家散去了之後,鹿野先生悄悄地對我說:『托泰,放心好了,山上的野獸非常多,要獵一頭大型動物是很容易的,萬一沒有獵到的話,罰金我來付沒關係。』我聽了感動得眼淚快要流出來,鹿野先生平常很少說話,今天卻為了我大聲和眾人爭辯,同時,鹿野先生的收入並不多,十圓對他來說是一筆很大的數目,我跟他才結識三個多月,他大可不必為我犧牲那麼大。
「當天深夜我聽到族裏的老年人議論紛紛,認為一定要出草獵首才算數,對於頭目判定可以用罰金代替相當不以為然。
「我想起幼年時,祖母常跟我說起當年祖父被泰雅族馘首的慘狀,她描述當年她到農地去收拾無頭屍體的情景,血淋淋的場面令我做了好幾次惡夢,祖母也曾厲聲地告誡我,將來絕對不可以娶泰雅女人為妻,因為泰雅人是我們家族的仇人。
「我原本早已忘記祖母的教訓和祖父的慘死,但是這一天晚上祖父無頭的身影卻不斷出現在我眼前,我怕憤怒的泰雅人會背著日警,趁夜來割取我的首級,整夜都驚恐不敢閤眼。
「真是可惡的傳統,部落有人受傷卻怪罪到不相干的人身上!我一方面有冤難伸,一方面又怕泰雅人故意不認真獵捕野獸,第二天早上就當著大家的面要求一起上山打獵,頭目和日警主管商議了一下就批准了。
「由於非當事人的親屬不得參與,上山打獵的只有受傷者的親屬七人,加上我的女朋友的親屬十一人,連同我共十九人,分成三路出發。鹿野先生為了讓我有必勝的把握,特別交給我一把德國製的新式散彈槍,並要我多帶一些子彈,此外,他也特別與日警主管交涉,請求借給打獵的隊伍每人一把村日式步槍和五發子彈,這是非常為難的要求,但是主管竟答應了。
「說也奇怪,前幾天登山途中經常看到的大型野獸,竟然一下子都不見蹤影了口與我同隊的泰雅獵人都很認真的搜尋動物的蹤跡,對他們來說,獵到一頭動物來祓除部落的不祥,其重要性並不下於我要證明自己的無罪,這一點使我非常安心。
「第一天,我們在司界蘭溪上游一帶搜巡終日而一無所獲,通常上游溪澗是動物最多的地方,這種不見獵物的反常現象更加深大家對我的懷疑,一個年輕的獵手就對我眨眨眼說:『托泰,披散亞克!』意思是說:托泰,有曖昧哦。我有口難言,只好笑笑說還有兩天,不用急。
「北部的泰雅族,和我們南部的蕃人不同,我們經常夜獵,因為夜晚大型的動物都會出來喝水,很容易獵捕。但是泰雅人根本沒有夜獵的習慣,也不肯聽我的話嘗試看看,我孤掌難鳴,整夜坐困愁城。
「第二天我們往雪山的方向直登,在賽蘭酒獵屋處再分為三組擴大搜索範圍,零星的捕到一些像黃鼠狼、松鼠之類的小動物,令我十分沮喪,因為只有山豬以上的大動物才算數!
「我不斷的摸著獵槍,只要一有獵物出現,我有把握在一秒間解決牠,然而像活見鬼似的,沒有獵物就是沒有!
「當天晚上非常寒冷,我們在賽蘭酒湧泉旁升起篝火驅寒,在明滅晃動的火光中,我那泰雅女友驚惶無助的表情、祖父無頭的屍身和祖母氣苦的面容,不斷交疊在我眼前……我雖然違背祖母的訓示,和泰雅女孩戀愛,但是也不該受到這樣的責罰,何況祖母一向痛恨獵首的習慣,她一定會保佑我的。
「我整夜胡思亂想不曾合睫,第三天已經憔悴不堪,卻不得不打起精神,繼續狩獵的工作。我取出自帶的白米和罐頭請隊友吃,希望大家吃飽後更加認真的打獵,無論如何,這是最後一天的機會。經過兩天的相處,大家都知道我的為人,也對我表示同情和關懷,然而打獵的事情完全要看上天的旨意,誰也愛莫能助。
「我神不守舍的跟著大家越過山稜,往七家灣溪上游的方向搜尋,一路思緒亂紛紛。沒有獵到野獸的話,不只是我個人的清白問題,也不只是讓鹿野先生無故損失十圓的問題,而是我擔心志佳陽部落的長老,不認為罰錢就可以祛除不祥,他們很可能在我們離開部落後,埋伏在半路截殺我!今天早上吃過我的白米飯後,有個獵手就偷偷地提醒我,要我特別留心『不利』的狀況,所謂不利,就是我最耽心的事。
「我在志佳陽住了兩個月,算起來也不是陌生的外鄉人了,何況一直與他們相處融洽。到了第三天,大家都格外賣力,遠離平日的獵徑,到原始森林內搜尋,我很感激他們,但是目標仍未達到,天色漸漸暗了,終於有人開口說:『認命吧,托泰,這是天意。』我有一種破釜沉舟的悲壯,就挺直背脊說:『還沒到最後關頭,我們在歸途還可以繼續尋找!』,一位年輕人也附和說:『今天夜晚也包括在第三天之內,無論如何我們要幫托泰到底!』
「走回雪山獵徑時,初冬的太陽已經落到稜線後方了,在淒涼薄暗的山路上,我的心情也像落日一樣不斷地下沈。忽然,遠處傳來雨聲槍響,還有模糊的喊聲,意思是打到一頭大山豬了,我們大家立刻用泰雅語大聲喊叫:『凱托巴奈,瓦拉克!』(好運氣!)
「狂喜之下,我們一面嘶喊一面奔跑,很快地衝到現場,原來是一頭長著一對大白牙,重約一百十斤的大山豬。這一頭一定算數!大家興舊地割下豬頭,放入網袋,如同出草獵人頭的作法一樣,要把豬頭帶回部落交給頭目和受傷者處置。
「我們把其餘的肉塊和內臟分割好,分別放入各人的網袋,也來不及砍油松照路,大夥就趁黑跌跌撞撞地趕回志佳陽社。頭目顯然對此次的結果感到滿意,有這麼大的一個豬頭,長老也都沒話說,當夜全部落的人就圍著營火,快樂的喝酒、吃肉、唱歌、跳舞,平日很少喝酒的鹿野先生也破例的喝了一些酒,整夜都聽到他興奮地對頭目不斷重複說:『我不是說過了嗎?托泰的戀愛是真誠的友誼,沒有曖昧!』」
說到這裏已是薄暮時分了,夕陽透過充作窗欄的牛車輪間隙,投射在牆上陳舊的阿美族飾袋和一張張霉跡斑斑的古老照片上,風流倜儻的托泰和敦厚誠摯的鹿野忠雄,陳年往事都封存在這一間特別的密室裏,六十年開罈一聞,竟然鮮活如昔,只是平添了更多的醇美。
黃昏的陽光也照射在托泰稀疏的白髮和白眉間,他揉揉久閉的眼皮,睜開眼睛對我恬然一笑,六十年的心事一旦說出來,心情真是無法形容的輕鬆暢快。
「托泰先生,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你,」我的心還記掛著志佳陽的泰雅少女:「你和當時的女朋友究竟有沒有曖昧關係?」
托泰站起身來對我曖昧一笑,借用鹿野忠雄的話說:「托泰的戀愛是真誠的友誼,不算曖昧。」
回到客廳,托泰坐在風琴前,為我彈奏引起戀愛友情的「伊保樹之歌」,他一面彈奏一面低聲哼唱,一遍又一遍。突然間,似乎歌聲觸動了他的思念,他纖長的手指停留在琴鍵上,閉上眼睛任思緒穿過茫茫時空。我也閉上眼睛,遙想三十年前我初登南湖大山,站在圈谷下,對照鹿野忠雄博士的手繪圈谷地形圖的情景。
良久,托泰輕聲的叫醒我,拿著一本今年二月新出版的「鹿野忠雄」一書給我看,這一本由東京都立大學助理教授山崎柄根博士所撰寫的鹿野忠雄傳記,甫一出版就獲得日本「非小說類文學大賞」,在日本文學界和學術界都造成轟動。
「山崎先生花很久的時間考證鹿野忠雄博士的事蹟,」托泰指著書中的圖片說:「他曾經與我通信許多回,跟我討論鹿野先生的往事,我看這本書寫得很好,如果你對鹿野先生還有什麼不瞭解的,這一本書可以借你帶回去看。」
我告訴托泰說,我已經自己買了一本,而且也全書都看過了,這本書雖然對鹿野忠雄的學術研究成果撰寫得十分詳盡,但是對於鹿野忠雄的人格風範和待人接物的體認,絕對不及托泰的描述。
「托泰先生,我真心的說,在你的訴說下,我感覺鹿野忠雄博士就像活生生地在我面前一樣。」這句話令托泰大為高興,他興奮地說:「楊先生,你真的覺得鹿野忠雄先生還活著嗎?告訴你,我也是這樣想!八年前,我到日本去探訪鹿野夫人靜子女士,她說她始終相信鹿野先生還在人世,他只是在叢林調查南島文化史,過度深入而忘記回來。」
回程的火車時刻已快到了,我回想這兩天豐碩的訪問成果,慶幸托泰的健在,慶幸牠的記憶力與表達力,也慶幸我的日語能力能夠與他完全溝通,更慶幸因為自己對鹿野忠雄的尊崇,感動了托泰願意滔滔說出六十年舊事。
在他送找出門之時,我問他為什麼要把這一段六十年前的故事告訴我?還有,我能不能把它寫出來?
托泰神秘地笑著說:「因為你是第一個為了多聽一點鹿野忠雄的事,寧願不吃飯的人!」「至於這個故事,我已經是83歲的老人了,寫出來應該沒有關係了,何況,這裏面有關於泰雅族出草習俗的變遷經過,應該要讓年輕的學者知道。」
走到院子,托泰忽然感慨地說:「如果鹿野先生還活著的話,我真希望他住在這裏,他也是88歲的老人了,應該也沒有辦法登山了。我們可以一起指導年輕人,賸下來的時間就一起坐在院子裏眺望中央山脈,追想我們年輕時的事……啊,楊先生,你要去搭火車了,記得,飯要吃,火車也要搭,不送你了,再見吧!」
我循著來路往壽豐火車站的方向走,不時回過頭張望夕陽餘輝下的瘦高身影。斜陽在中央山脈稜線上,還有在托泰頭頂的白髮上,都鑲上一道金邊。托泰並沒有看我,他的眼神遠遠地投射向中央山脈的高點。我知道在黑夜來臨前他將一直這樣凝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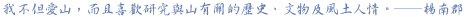
[回上一頁] [下一頁]
 作家檔案
作家檔案  探索山林間
探索山林間  生蕃行腳
生蕃行腳  高海拔人側記
高海拔人側記  作家首頁
作家首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