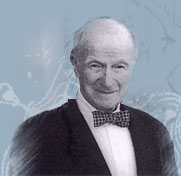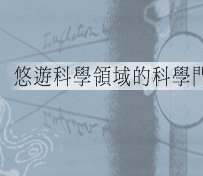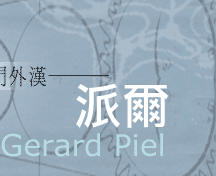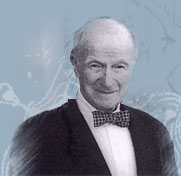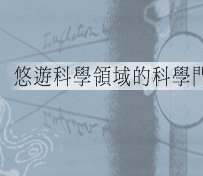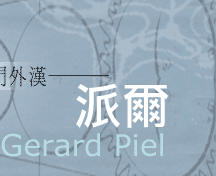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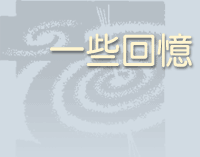 
科學人與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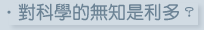
我在哈佛就讀時,接觸到與科學最「相近」的課程是社會學(sociology),這是跟一位名叫墨頓(Robert K. Merton)的研究生私下學習的。為實踐嚴師出高徒的古訓,他規定我讀遍大師們的著作:托尼(R.
H. Tawney,英國社會學家)、涂爾干(Emile Durkheim,法國社會學家)、馬克思(Karl Marx)、桑巴特(Werner
Sombart,德國經濟史學家)、韋伯(Max Weber,德國社會學家),甚至於作品剛被翻成英文的巴雷多(Vilfredo
Pareto,義大利社會學家)。從此我對社會學敬而遠之,決定專攻歷史。
1938年,歷史經驗告訴我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迫在眉睫,為實現當戰地記者的志願,我進入《生活雜誌》社工作。不料,我對科學的完全無知竟然超越我學歷史的背景,變成一項利多條件。當時擔任《時代》主編的畢陵思(John
Shaw Billings)被派去主持剛剛以重金併購的《生活雜誌》,新官一上任,馬上決定讓這份以照片為主的雜誌變成公司的招牌,並且極力想以各式各樣的報導內容,達到社會教育的功能。(老實說,這個理想一直都沒有達成,只要瞄一下超市櫃台旁所擺的版本即可知端倪。)他指派我負責報導科學方面的東西,理由是我對科學的無知總比半桶子水安全,只懂一點皮毛的人做起事來反而危險。
我接下這個任務之後馬上發現,當時根本沒有所謂的科學雜誌。我的同事們--報導國內外新聞的啦、體育新聞的啦、好來塢新聞的啦、藝文娛樂新聞的啦--都有許多資料來源,主要是《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知道下一期的《生活雜誌》要怎麼寫。我發現,科學資料只來自科學界自己的出版品,而
且其數量多得不得了,比人文方面多得多。這些極為專業的期刊只作為每一個狹窄的領域研究結果的內部交流,別說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不同領域的科學家也一樣看不懂。我發現沒有一個地方可以獲得科學資訊,包括《紐約時報》--雖然目前他們報導科學的工作做得不錯。
當時的科學家對出版任何東西都抱持極為慎重的態度,這不是沒有原因,他們常常因為一篇過度渲染或失實的報導,被弄得下不了台。記得第一次為了說服兩位一起做研究的科學家跟我及攝影師合作,報導他及她的研究工作時,曾花了好大一番功夫。不過,在我成功的將前幾篇報導登在《生活雜誌》上之後,要說服其他科學家跟我合作就容易多了。
因為攝影機會說話,照片可將事情本身所具有的趣味性顯示出來,取悅讀者的乏味工作因此變得趣味盎然。其他許多大眾刊物為吸引讀者的注意,往往做誇大煽情的報導,讓科學家們尷尬不已,無形中破壞彼此的關係。一張成功的照片勝過千言萬語,可以化腐朽為神奇。我為照片所撰寫的說明和故事,後來都被認為相當貼切;本來我的科學同事一直堅持要審查我的原稿,但後來發現他們所犯的錯誤並不比我和攝影師少,因此自動放棄這項權利。
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大眾雜誌上出現負責任的、權威性的科學報導。1944年夏,我發現自己大受科學家們的歡迎,只要我找上他們,他們都樂於協助。甚至高高在上的洛克斐勒機構(Rockefeller
Institute)都找我共同製作一篇報導。那是有關首度分離出某種病毒及分析出其化學結構的故事,為該機構成員史丹利(Wendell
Stanley)所完成的壯舉,後來於1946年獲得戰後首度頒發的諾貝爾化學獎。承蒙史丹利的協助,慨然借給我們一瓶菸草嵌紋病病毒(tobacco
mosaic virus);我和我的首席攝影師郭樂(Fritz Goro)因而得以將該病毒獨特的幾何形狀以伽皮魚(guppy,產於西印度群島的一種熱帶魚)游泳時閃現的四種顏色顯示出來。
此時我知道,我的科學部門已經在《生活雜誌》四百萬訂戶中分離出一群熱心的支持者;他們對我刊在雜誌上的文章熱烈的反應使我瞭解到,他們雖然對本行的東西非常清楚,但跟我一樣,迫切需要一本科學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