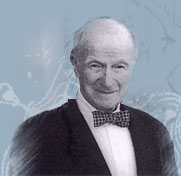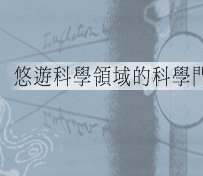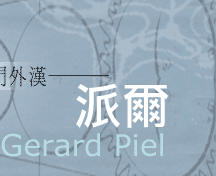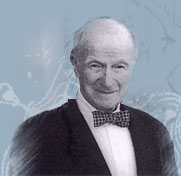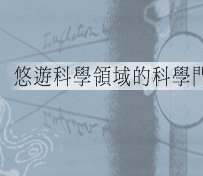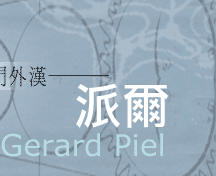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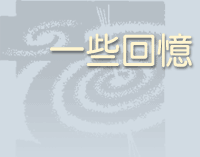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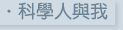
文/派爾(Gerard Piel)
在本書(《科學人的年代》)中,我想要告訴讀者們,就我所知科學家在20世紀當中知道了甚麼;總歸一句話:科學的功能主要是讓我們對周遭的世界有一完整的瞭解,並且在這個世界裡找到自己的定位。從人類以天意解釋萬事萬物以降,這幅圖畫從未如此完整過。在我們周遭的世界裡,甚至在超乎我們感覺的世界裡,科學為人類開啟了許多嶄新的知識領域。
與以往不同的是,科學知識係建構在可驗證的人類經驗上;我在此必須指出,這件事主要是在20世紀中方為人所知。在該世紀的最後數十年中,各種不同科學部門的研究結果都不約而同的指向相同的幾個終極問題。在客觀科學知識的重新包裝下,這幾個古老的問題都直接跟生命有關。這項工作目前還在進行當中,至於是否會因經過驗證而發揚光大或遭到修正,尚不得而知。
這個新知識的客觀性已經透過各種科技無比的精巧和廣度,向社會大眾展示過了。科技固然賦予個人和社會無所不能的權力,但伴隨而來的經濟上、社會上、環境上的改變,其速度、規模、不可恢復性,都使人不得不重新檢視目前既有的、人類行為所依循的一些前提。
面對這種重新檢討的要求,科學界一向表現出理性、容忍、與自制的良好示範。
我必須聲明在先,本書中拼出來的這幅畫完全不會在正式科學文獻中被拼出來。科學文獻的作者幾乎不談此事;因為同一領域裡的人早就知道拼出來是甚麼東西,否則就根本混不下去。
跟大多數人一樣,我不是科學家,因此就讓我來拼這個圖吧。我也希望讀者們從這裡找到材料和動機,拼出一張自己的圖。
身兼作家、編輯、及發行人的我,在20世紀後半科學客觀知識如火如荼展開之際,只能當一個旁觀者。我的職業是將科學各部門的研究成果報導給廣大的社會大眾,其中有許多人希望跟隨科學界的進展一起邁進。
我和我的同事們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滿足這批觀眾的興趣,就像絕大部份科學家對其他非本行的領域所具有的興趣一樣。他們生來就想瞭解周遭世界的一切--每一個小孩都是天生的科學家。但經過一陣子,他們馬上發現必須縮小興趣的範圍,而選定一個專長。在其他領域裡他們雖然是門外漢,但會想盡辦法參一腳,儘管一無所知,但有隨時接受突來驚喜的心理準備,可說是一群如假包換的熱心門外漢。假如我們無法滿足他們的好奇心,就沒有資格講甚麼話。
我之所以發現廣大的社會中有一群人具有這種需求,完全是偶然的;1940年代我在剛創刊不久的《生活雜誌》(Life)擔任科學編輯,這是一份以圖片為主的大眾化刊物。在這一段見習期間,我發現了這個讀者群,於是我開始籌劃創辦一份科學雜誌。當我正在找合夥人、工作人員以及籌募所需的經費時,我的老闆的遭遇給我一個靈感;當時《生活雜誌》已面臨停刊的窘境,而被《時代雜誌》(Time)併購。於是我也買下創刊102年但已面臨停刊的《科學人》(Scientific
American),於1948年5月以同一名稱推出新版的第一期。
這成了我終身的事業,但我的知識背景卻跟這件事相去甚遠。我在1937年由哈佛學院(Harvard College)以第二名畢業時,拿到的是歷史系的學士學位,對科學可說是一竅不通。跟目前美國大部份國中小學的學生一樣,對數學和科學課程完全敬而遠之。算術課有如軍事操練,全部靠死背,令人不敢恭維。在怎麼學也學不會的情況下所產生的挫折感,使學生們對後續的代數和其他數學更加排斥。
科學課程也都是紙上談兵(目前仍然如此)。當時高中和大學的課本都只是薄薄的八開本,不像目前學生書包裡所裝的四色印刷四開本--其中最好的多由富立曼公司(W.
H. Freeman & Co.)出版,這是《科學人》的一家子公司,專門出版科學課本。老師教給我的物理也少得可憐;物理課本像幾何課本一樣,是一本薄得不能再薄的綠皮書;更絕的是,其中一位作者(Charles
Elwood Dull)竟然姓「呆」(Dull)。測量水的沸點是典型的物理實驗,我早就知道那是華氏212度。實驗課本說是攝氏100度。我量來量去總是得不出這個數據,記得當時得到的平均值是攝氏98.6度,到現在我仍然搞不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