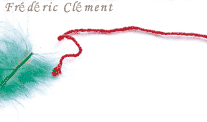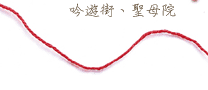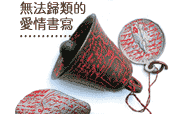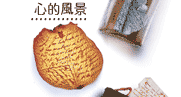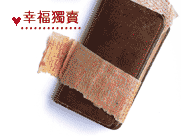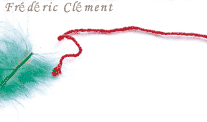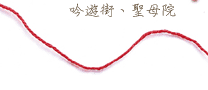|

這大掛鐘的時間將近正午時分,看守掛鐘的是一隻
長滿青苔的石獅子,我穿越柵欄,直抵面對費胡街的出口,
穿過沃吉哈街,為了實現我那神秘傳訊者的意願。在杜爾農街的
一戶門口,我放下一株從公園偷來的紫紅蝴蝶花,而在
孔代街22號,一片木牌寫著:
「這是露西兒•迪布雷西斯與卡密爾•德慕蘭(註1)結婚之前的住處。
1794年4月13日,露西兒被送上斷頭台。」
正對面是17號,在一個黑漆的心型下方,
釘著一張紅紙。短短幾個字:
「相約在奧德翁廣場2號。地中海餐廳的信箱。
2號,循著心型的尖端,你將找到送給露西兒和卡密爾的兩朵金黃蝴蝶花。
在餐廳信箱的上方,在地中海(Mediterranee)的 a 字字母上方:
金色絲線
懸吊著的透明管子
在風中晃蕩,那是一個信封。
彷彿作為交換,裡面是兩朵乾燥的蝴蝶花,
分別以棕色和白色的油墨寫著:
A
A是羽翼(Aile)的 A
A是愛情(Amour)的A
A是熾熱(Ardent)的A
A是銀白色(Argentin)的 A
我的名字就叫做
阿衷緹娜(Argentine)
是的,可愛的先生,我的名字就叫做阿衷緹娜。
阿衷緹娜有一顆金黃的心,人說:因為我愛。我所有的時間
都用來愛。我愛愛情。我愛愛侶,我看著他們,
觀察他們,跟隨他們,聆聽、書寫、紀錄,
我計算嘆息的次數,我衡量誓言的份量,我記下
每一次的親吻,錄下每一回的撫愛,每一個交遞的眼神……
有時候,我會陷在自己的遊戲當中,無可自拔……
謝謝您,我溫柔的先生,我為盧森堡公園的愛侶們謝謝您。
現在,我請您再穿過沃吉哈街,
停在50號,特亥摩爾大飯店的門前。
聽著,先生,仔細聆聽烏鶺醺醺然的顫音。
用指尖順著圍牆直到費胡街,
狹小的巷弄,左側,那兒您可以安靜聆聽。
攤平你的手掌緊貼10號的灰泥牆面。不要管
稍遠處那兩座人面獅身女像,集中精神聆聽那
喃喃細音。牆面已被這些細碎的聲音浸透。聽著……
霧的窸窣聲,紫藤枝蔓伸展的幾乎難以察覺的
聲音。牆後有蜜蜂振翅的嗡嗡細響,
紙張翻動的沙沙聲中夾雜著喃喃細語。您聽見了嗎?
瑪麗•馬德蓮的指尖輕撫著
《克萊芙王妃》(註2)初版的首頁,巴爾賓書店的夥計
剛把書送來。1678年3月16日。星期二。
約莫3時的時刻。
一隻蜜蜂被潔白的紙張,被新鮮膠糊的甜香
所吸引,棲停在翻開的書本上,閃亮的翅翼
像迎向陽光的槴子花。蜜蜂腳下的書頁還是熱的,
瑪麗•馬德蓮手掌下的書頁還是熱的。
蜜蜂前進,停下,梳理翅膀,尋覓,腳爪
緊抓紙張上的纖維,在空白處,在書頁邊緣,
在墨黑的字跡上,遺留牠採來的花粉。書頁夾縫間,
黃色的花粉堆成了一個F的字母。
拉法葉夫人微笑著,她從不在自己的著作上署名。
包括這本嶄新的、天藍色書皮的《克萊芙王妃》。
之前出版的《扎伊德》等書也是一樣。
她的小說會假借她的顧問、校對,同時也是教師的謝葛亥(Segrais)
的名字。當時風氣如此。對一個上層社會的貴婦人而言,
寫書出版是很不恰當的。
蜜蜂棲停於「愛」字,靜止不動。嘆息聲。
瑪麗•馬德蓮嚮往溫柔的情愛,自從十二歲,
琥珀般的少女之戀就繫在一位心如冰雕的高大男人
身上。瑪麗•馬德蓮溫暖了他,用伊棉絨一般的纖手。
伊很有耐心,總是將細嫩的手掌輕放在他額頭上。日復一日。
就這樣融化了他鬢角的冰霜。包裹他受傷的
靈魂。她冰心的男人如水晶般冷漠。
那是瑪西亞克先生,亦即後來的拉羅旭夫,投石黨(註3)
的敗將,被逐出皇宮,流放,變成伊那心如冰雹的
男人。伊照料他,為他包紮被時間利刃刺傷的
傷痕。1672年,跨越萊茵河之際,兩個兒子同時失去。
伊還是溫暖他,用伊如黃貂的手,
如紫貂的臂,如水貂的腹。將他環抱。
鄰近兩座修院的鐘聲交纏著
響起,其一是聖女修道院聖女之音的清脆悠揚,
怯怯含羞的,則適赤足修行的加爾默修會。
3時。三道陽光閃過
蜜蜂的眼睛,牠棲停在瑪麗•馬德蓮的記事本上,
彷彿一只訂婚的戒指。鑲了寶石的戒指。微笑。
瑪麗輕悄悄地移動手臂,闔上雙眼。做夢。
她一方面緊閉著眼瞼,等待金黃色的字句
浮現,一方面舌尖滾轉著溫熱的話語。
為他,拉羅旭夫,愛他。他是冰塊中雕塑出的情誼。
她略為顫抖。迫不及待地要向他展示這本藍色的書,這本
蝕刻著金心圖案的藍色新書。
回憶。
註1:卡密爾.德慕蘭(Camille Desmoulins,
1760~1794),法國大革命時代國民公會的議員。
註2:《克萊芙王妃》(Princesse de
Cleves),是1678匿名出版的一部愛情悲劇小說。作者是拉法葉夫人(Mme de la Fayette),瑪麗.馬德蓮(Marie-Madeleine)是她婚前的名字。
註3:投石黨,La Fronde,指1648到1652年間的反朝廷運動。當時皇帝路易十四尚年幼,由紅衣主教瑪札罕(Mazarin)督政,瑪札罕的嚴苛的稅收政策極不得人心,引致反對者集結暴動。
(節錄自《巴黎情人》,遠流出版)
沃吉哈街│吟遊街、聖母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