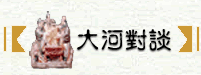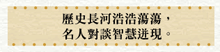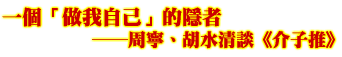|
 介子推是個很獨特的歷史人物。 介子推是個很獨特的歷史人物。
當晉文公重耳還在流亡各國時,曾經絕食斷炊,在那掙扎求生之際,傳說介子推忍痛割下一塊腿肉,煮給重耳吃;重耳即位後,介子推因不滿同僚爭功搶位而退隱於山中,傳說晉文公為了找他,放火燒山,他與母親相抱,被燒成一對焦黑的屍骨。
這兩則傳說,令介子推成為異人,但是在傳說之外,介子推有哪些具體的事蹟?他具備什麼能力特質?他為什麼追隨重耳?他做過哪些重要的事?扮演了什麼角色?這些都是歷史之謎。《介子推》一書,試圖撥開這重重迷霧,為我們探索那失落的一頁傳奇……
生在山野•隱入山野
 周寧(以下簡稱周):在小說中,介子推是個在山野中長大的孩子,他有一段奇特的經驗:在山上親眼目睹村人被老虎吃去了半截,便削木為棍,練習以木擊石,做為打虎除害之用,他勤練到功力精進,竟能以木棍擊裂堅硬的岩石,成為一個用棍高手。 周寧(以下簡稱周):在小說中,介子推是個在山野中長大的孩子,他有一段奇特的經驗:在山上親眼目睹村人被老虎吃去了半截,便削木為棍,練習以木擊石,做為打虎除害之用,他勤練到功力精進,竟能以木棍擊裂堅硬的岩石,成為一個用棍高手。
 胡水清(以下簡稱胡):介子推是山岳的子民,從山岳生活中鍛鍊出矯健的身手,是極自然的。加上古人自幼習文學武,不論是刀槍或棍、劍,習取任何一項專長,成為他後來追隨重耳流亡的一種本領。小說中賦予他精通棍棒,是極合情入理的。 胡水清(以下簡稱胡):介子推是山岳的子民,從山岳生活中鍛鍊出矯健的身手,是極自然的。加上古人自幼習文學武,不論是刀槍或棍、劍,習取任何一項專長,成為他後來追隨重耳流亡的一種本領。小說中賦予他精通棍棒,是極合情入理的。
周:作者花很多筆墨描寫介子推年少時的生活與思想,及母親對他的教養、幼時玩伴石承對他的刺激等等。直到介子推二十歲時,已經出去外面闖蕩很久的石承,回到老家,告訴他晉國的事,告訴他關於重耳、申生、夷吾、驪姬這些名字,他的世界才開啟了變化。
胡:作者宮城谷昌光對他筆下的歷史人物,其成長環境、成長過程,常刻劃得很細微。相對的,情節也就沒那麼緊湊。不過,這麼細微的刻劃,把介子推塑造成一個很崇敬山神的子民,長期接受山野薰陶,韌性較強,所以後來重耳流亡的艱困時刻,介子推很能忍飢耐渴,扮演著重耳的保護神的角色;等到看透權力爭逐的一面時,介子推毅然棄官退隱山林,還原到他原始的自然人本色,與世無爭。這樣,他的回歸,一點也不矯情做作了。
表裡如一•從不誇耀
周:這是很獨到的分析,很能解釋作者為什麼對介子推的年少生活做了如此多的舖陳。介子推是在二十歲以後,在家鄉的汾水之上,巧遇了渡河的重耳幹部先軫,才去投靠重耳。
這個時候,重耳才流亡不久,正是開始大量吸收人才,號召群眾之際。介子推很快就成了重耳的追隨者,但不是直接隸屬於重耳,而是當重耳的直屬臣子的臣子。這種身分較低,必須經過相當時間的工作、考驗,表現優異,才有機會晉升為直屬臣子。
胡:雖然小說中並無進一步提到重耳及其主要重臣,是根據什麼樣的考核制度來拔擢人才,但相信是有一套標準的。介子推在投效重耳之後,經過數年默默辛苦工作,沒人管、沒人問,有一天,重耳的大臣咎犯,來問介子推:願不願成為重耳的直屬臣子。這意謂著介子推被拔擢了──他們認定介子推是「真正表裡如一、認真、正直的人」;根據介子推自己的理解,他曾去做別人不喜歡做的工作、曾在暴風雨之夜,冒雨去察看麥子會不會受損,他從不曾誇耀自己的努力、艱苦或成果……。從「表裡如一」、「從不誇耀」這兩大優點看來,介子推是個很內斂、很會自我要求的人,而且具有很高的道德標準。
周:歷史小說之令人激賞,就在於它雖然所寫的是歷史上的人或事,卻好像在寫我們身邊、我們眼前的人事,有時甚至像在寫你或寫我,是那麼的似曾相識或息息相關!介子推就像我們在職場上所見到的一些優異者那樣,工作時積極投入,沒有人對他做什麼要求,他卻能始終如一、表裡如一。如果每個人都能像介子推這樣,一定不會被埋沒!
重耳的賢名日盛,投靠他的人越多。有的很單純,像介子推;有的很複雜,其中不乏晉王室派來臥底的奸細,因此引發不少「疑似間諜」事件。有一個則是擺明著要行刺重耳──他就是鼎鼎大名的閹楚,一個寺人(宦官)頭子、大內高手。
一個刺客•三種角色
胡:這個刺客可以說是歷史上最特立獨行、亦善亦惡的一個怪人,他如影隨形地跟蹤著重耳,三番兩次行刺,都造成大震撼,介子推屢次與閹楚對峙、挑戰,屢次扮演了重耳保護神的角色,卻也一直擊不倒閹楚。
閹楚是一個像鋼鐵般的刺客,是消滅不了的;也是個鏡子一般的刺客,是重耳的一面「內視鏡」,讓重耳反照自己。閹楚與其說是行刺,不如說是刺激──隨時提醒重耳:世上有我這個刺客存在,所以你的流亡之路不容稍懈!正如閹楚向介子推所說的那一段話:「重耳和你們一旦在某個國家受到禮遇而忘記苦難,開始驕慢的時候,我的劍就會刺到。與其說是我殺的,不如說是重耳自取滅亡。」這個刺客,已經昇華為一股鞭策重耳的力量了,他既是謀殺者,也是監視者,後來又變成保護者。
周:重耳返國即位,閹楚從刺客搖身一變,成為重耳的保護者,這又延伸了一個殺手的角色與意義──當你努力不懈地完成目標時,我的劍也完成了使命,不再是行刺之劍,而是保護之劍了。就現實意義上,閹楚從刺客轉變為保護者,是順理成章的。他一向忠於晉王室,從前是忠於晉獻公,奉命行刺重耳;現在晉王室已歸重耳所有,閹楚自然又效忠於重耳了。
在經歷了十幾年的磨難之後,重耳等一行人終於否極泰來,踏上了晉國故土──這也象徵著他們踏入了權力網路中。
求為隱者•做我自己
周:重耳的元老重臣咎犯,在親履國土之際,突然向重耳請罪,說他迫使重耳走上這條漫長的流亡之路。重耳當然明白咎犯的弦外之音,立刻表白說,他絕不會背棄咎犯,否則願受河神懲罰。就是這一幕,對介子推帶來沉重一擊,使他突然發覺:原來冒死追隨重耳,最後卻是為了權力。
胡:介子推原本把追隨重耳當做是一生的榮耀,他期望重耳可以比美帝堯,當一代聖主,但這個理想,被赤裸裸的權力分配所擊碎,介子推認為有損他純淨的動機而毅然引退。
周:咎犯等人在協助重耳成功地返國後,馬上面對一個權力大餅,絕大多數人都無法拒絕它的誘惑,這是正常的人性使然。
胡:對!其實這種現象常見於古今中外的所有組織文化中。當一個公司創業成功時、一個在野黨變成執政黨時、一個團體開始擁有可資分配的權力時,必然會發生爭功現象;當一個部門或一個主管竄起時,也常發生類似現象。爭功是第一步,搶權是第二步,接下來否定、打擊別人,展開赤裸裸的權力鬥爭。
周:這是介子推留給世人的一面鏡子,告訴人們:同舟共濟的革命同志、創業伙伴,在追求理想時都可以是很純真的,一旦碰上權力,就會產生了質變。權力的特質──具有壟斷、獨裁傾向,具有排他作用──使人際關係複雜、矛盾起來,最後往往導向了衝突。
我們不可能用道德勸服的方式,告訴局中人要如何珍惜那同甘苦共患難的情感,而不要為權力撕破臉。權力與道德往往是相悖的。在權力的網路中,是沒有道德禁區的。
介子推的斷然抉擇──退出權力網路,為這種爭功卡位現象提供了一解,他代表的是一種自省的力量,為了讓自我的理想不會變質,他拒絕做官,求為隱者。如果他也跟別人一樣,投入權力大餅中,他很快就會滅頂;但他勇於割捨,跳脫而出,不僅因此成全了自己,也為後世磨亮了一面明鏡。
(本次對談內容取自《介子推》,實學社出版,遠流發行))
最新更新日期:92.07.24
→歷史資料回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