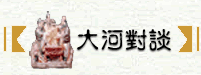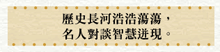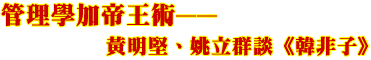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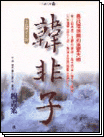 戰國時代韓國王室公子韓非,幼時便能以「秦王嫁女」、「楚人賣珠」等故事為喻,回答韓王的問題。及長,韓非師從荀卿學帝王之術,並由荀子「性惡論」得到啟發,力倡君王以法、術、勢治國的必要。 戰國時代韓國王室公子韓非,幼時便能以「秦王嫁女」、「楚人賣珠」等故事為喻,回答韓王的問題。及長,韓非師從荀卿學帝王之術,並由荀子「性惡論」得到啟發,力倡君王以法、術、勢治國的必要。
韓非力圖韓國長治久安,但歷經三代韓王皆如卞和獻玉於楚王一樣,不為君王所用。韓非將胸中大志盡書於簡策,後秦王政偶讀其書,讚嘆道:「使寡人與之遊,死不恨矣!」強行請其入秦。韓非一到秦國,尚未與秦王詳談其政治主張,便被老同學李斯構陷入獄,身死異國!
思想的源頭
 姚立群(前實學社主編,以下簡稱姚):韓非拜荀子為師,反對仁義、兼愛及王道,與孔孟之學背道而馳,他是對於古今社會、經濟背景的變化,做了透徹的觀察,並提出具體對策的法學大師,很值得我們重新認識。要談韓非,應先從他的老師荀子談起。 姚立群(前實學社主編,以下簡稱姚):韓非拜荀子為師,反對仁義、兼愛及王道,與孔孟之學背道而馳,他是對於古今社會、經濟背景的變化,做了透徹的觀察,並提出具體對策的法學大師,很值得我們重新認識。要談韓非,應先從他的老師荀子談起。
重義輕死的價值觀
 黃明堅(作家,以下簡稱黃):對!荀子主張性惡,他認為人性應該被導正,而要導正人性便要講究方法。性惡篇第一句話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這九個字便是荀子思想的精髓。古書的「偽」即是「為」,荀子本意是說:人性本為惡,其表露的善其實是刻意做出來的。這樣的思想不論在當時,或是兩千兩百年後的今天,仍是屬於非主流的思想,荀子認為古之聖王正因為了解人的行為偏險不正,所以立君上之威以統御百姓,倡明禮義以教化百姓,建立法制以治理百姓,加重刑罰以畏禁百姓,使天下達於治而合於善。 黃明堅(作家,以下簡稱黃):對!荀子主張性惡,他認為人性應該被導正,而要導正人性便要講究方法。性惡篇第一句話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這九個字便是荀子思想的精髓。古書的「偽」即是「為」,荀子本意是說:人性本為惡,其表露的善其實是刻意做出來的。這樣的思想不論在當時,或是兩千兩百年後的今天,仍是屬於非主流的思想,荀子認為古之聖王正因為了解人的行為偏險不正,所以立君上之威以統御百姓,倡明禮義以教化百姓,建立法制以治理百姓,加重刑罰以畏禁百姓,使天下達於治而合於善。
身為王室公子的韓非會去投靠荀子門下,即是很奇特的行為。我想,這大概是他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及歷史環境,使他在內心有非常反動及非主流的一面。
姚:韓非在當時的確是有點另類。讀這本書時,我學到了不少歷史掌故,也從韓非講述歷史人物與事件的過程中,發現他似乎是根據古今人口、食物供給、生產力等社會、經濟背景的不同而建立了自己獨特的政治觀。他在〈五蠹〉篇中曾提到:「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財貨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這樣的思想在當時算是很新穎。
黃:韓非算是個很聰明的人,他的這段話讓我想起經濟學家托瑪士.馬爾薩斯(西元1766∼1834年)。馬爾薩斯在他的「人口論」中指出,人口增加的力量比土地生產食物的力量大得多。韓非的時代比馬爾薩斯早了近兩千年,但他卻以如此前衛的、科學的眼光來看待政治,實在令人訝異。
韓非從社會經濟環境的轉變,看出了不同時代的不同需要,他觀察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於是構木為巢的有巢氏、鑽木取火的燧人氏相繼被推選為君王,如果現在還以這類人為君王,必為後人所笑!君王若欲以古治今,以先王的措施來治當世之民,就跟守株待兔的無知毫無二致。因此他反對王道,認為「治亂世,靠仁義、兼愛不行,必須依仗厚賞重罰,治以法術。」這樣從管理學衍生的政治主張實在具有開創性。
厚賞重罰、力倡法治
姚:韓非厚賞重罰的主張,與儒墨思想主流南轅北轍,他反對救貧與寬恕的仁道,認為那是治標,不能治本;他所主張的,顯然是要從基本面著手。韓非的法學思想似乎應有被重新定位的必要。
黃:荀子雖主張「性惡論」,卻無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及具體的施政藍圖;韓非把荀子的想法、主張具體地架構出完整的思想體系,相當具有經濟學與管理學的精神。
在韓非之前,每逢改朝換代時,大家都倡言聖王之治,但是韓非卻主張「變古」。他學的雖是帝王之術,卻不是從帝王的角度來看事情,他看到時代的變化與隨之而來的需求,於是主張「變古改制」,這是極為管理學的角度。他倡導富國強兵(明確的經營目標)及治吏不治民(分層負責)等等,隱然合乎管理的精神。
韓非的思想極具開創性,可算是管理理念的改革者,只可惜在諸子百家中,他的思想被定位在實用層次,而非人性或哲學的範疇,因此地位不及其他諸子。
姚:荀子講學之地──蘭陵,地方靠近厚葬成風的齊國。一日,荀子聽到鐃鈸之聲,便帶學生做戶外教學,這使得韓非深受啟發。他想起齊桓公曾憂心陪葬的衣衾把國家的布帛用盡,裝殮的棺槨把國家的木材耗完。於是,他聽從管仲之謀,下令規定陪葬的厚薄之度,才改變了厚葬的風俗。眼前的厚葬隊伍正說明人生時或死後都好名好利的,可算是一幅「性惡」的活圖畫。可否從管理學上的X理論、Y理論來談談孟子性善論與荀子性惡論的異同?從現代人性管理的角度來看,韓非師承的「性惡」理論有無可取之處?
黃:古代的政治,即是現代的管理學。現代管理學上有所謂的X理論、Y理論,前者主張人需要得到鼓勵與獎賞;後者則認為人必須經由懲罰與規範才足以防止流弊。孟子性善講的是選擇──即選擇善中最善者來管理百姓;而荀子認為人性本惡,便只好用方法加以管理。韓非師承荀子,亦主張人之性惡,「須以君上之勢、禮儀之化、法術之治、刑罰之禁」來矯正、向善。因此,韓非的政治主張,正融和了X理論與Y理論的特長。
韓非認為要導正人性必須有方法,因此才產生了對法的追求。荀子開發了道,而韓非子開發了術,建構了具體主張,是以他說「定法禁、明賞罰,布之於百姓。」他倡言的「法」便是指管理的方法,在只講聖人之治的古代,他談到魯哀公也曾在大野澤失火之時,用仲尼之議,嚴訂法刑,所以他認為聖人尚且用法,更可證明法具有很大的作用,這樣的法治思想實在是非常務實。
折轉靈活、巧用權術
姚:韓非的管理方法中談到君王要會用「術」。他說韓昭侯、衛嗣君都曾運用手段以御臣下──私下先將事情打聽清楚,然後將之公開,讓臣下以為君王明察秋毫,從此畏服,這便是君王用術以駕馭臣下的最佳例子。從現代政治或企業管理的角度來看,這樣的領導統御術,是否會流於權謀?
黃:君王的第一要務是──保住王位與尊榮;官吏所為,也是為了保住官位,他們口裡的仁義道德,事實上擺在他們心中第一位的,不是人民的利益,而是自己的榮華富貴。韓昭侯遣人暗中查看黃犢在田中毀苗,不准他人密報;而衛嗣君派人巧扮外來客商,以財貨向關吏行賄,都是為了讓臣下以為君王無所不知,而所謂「明察秋毫」的目的,說穿了還不都是為了防範下屬在背後耍花樣,以鞏固權位。
這正如某位曾任職大企業的管理學者所說:「在營利機構做事,最重要的是生產力第一、鬥爭第二;而在非營利機構做事,最重要的的是鬥爭第一、生產力第二。」這一理論,非常銳利地點出了組織與權力的本質,與韓非的觀點可謂不謀而合。韓非看出權力的本質是鬥爭,所以主張用術、用勢;他也看出組織的希望在於生產力,也就是富國強兵,所以他提出了厚賞重罰的主張。
其實,春秋戰國時代,國與國之間競爭激烈、君臣彼此互動尖銳,韓非的「術」一方面要顯示領導者的英明,不為臣子所蒙蔽;另一方面使國家不被消滅,君王不被臣子所取代。所以韓非子的術,基本上指的是一套實際的、領導統御部屬的方法。
權力在手、大行勢治
姚:韓非在「外儲說」篇也提到晉大臣師曠建議齊景公:「君必惠民而已矣。」勸其施德布惠於民,以免他的兩個弟弟成了政權最大威脅;齊大臣晏子則建議齊景公降低賦稅,緩其刑罰,以爭民心。世人皆以此二臣明智,齊景公為明君;韓非卻認為景公乃不知用勢之主;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在他以為,君王應以權力、威勢來禁止或誅殺那些擅行仁義,收買民心的權臣而非以仁德來與臣下爭民心,領導人如此用勢,是否得當?
黃:韓非對明君與賢臣的標準與孔孟之道不同,他的思想一向偏重於實用層次。政治的本質就是權勢,而非道德,這與現代管理有點異曲同工之處。所有君王都是以私人利益為第一考量,施仁政於民並非是君王的第一考慮,所以韓非認為齊景公必須先殺了隨時會與自己競爭的人,因為王位丟失,沒有了權勢,即使得民心又有何用?真正的領導者要有霸氣,要有高人一等的自覺,在韓非的政治理念中,也是認為空有道德無用,有權勢才有用。
法術勢的積極實踐者──李斯
姚:講韓非的一生時,不能不提他的老同學李斯。李斯曾經以廁鼠、倉鼠為喻,前者吃污穢尚且一日數驚,後者食粟米卻能泰然自若,二者處境迥異,高下立判;人之賢良與不肖,譬如鼠矣。李斯放棄小吏之職,向荀子學帝王之術,以便爭取高官厚祿。李斯總被評為太功利,太權謀,但我們卻清楚看到,他比韓非更能適應於當代的組織文化中。
黃: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不論在歷史上或是在現實生活裡,我們都可以看到,一個具有開創思想的人,其追隨者往往更加激進,李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以李斯為例,老師荀卿主張「隆禮」與「重法」並重,以掃除「性惡」造成的混亂,但是李斯卻更相信嚴刑重法的作用;此外,他一向嫉忌韓非,但韓非的主張,卻被他更積極地運用;當李斯成為秦王政的左右手之後,他也比秦王政更急於除去秦國的潛在威脅,李斯可說是性惡論的積極實踐者,他的作法比他所服膺及追隨的人都還要激進。韓非主張君對臣要「用勢」,李斯便也如法炮製,對這位老同學用勢──羅織韓非罪名,並以酖酒將韓非毒死。
李斯原是楚國小吏,為求高官厚祿,看準了情勢便能一無反顧,只求能見用於富強之國。韓非與李斯大不相同。韓非身在王室,錦衣美食,還有不可割捨的宗國情結,是以當魯國夫妻將徙於披髮紋身的越國,他笑他們以善織屨縞之長而遊於不用之國,必致困窮,卻未想到自己學富五車,竟也緊緊守住不用其學的韓國,不也是同樣的處境?
找不到老闆的人
姚:我們在孔子、孟子、莊子、荀子、韓非這些大思想家的故事裡,總看到他們在尋找理想國,卻都到處受挫。春秋戰國時代,君王們都在物色可以富國強兵的人才,而人才也都在尋找可以發揮的舞台,但終究還是有韓非這般「懷才不遇」的人。
黃:韓非雖是王室公子,很有機會勸諫韓王,事實上,歷代只求苟安的韓王,也害怕一旦起用韓非,韓非會比自己更得民心吧!韓非年少時便志於道,卻一直不能逢時遇主,但他依然留在韓國等待時機,及至踏上秦國領土時,仍舊是為了保衛韓國而去,他雖具有反主流的前瞻性思想,骨子裡卻仍與先聖先賢崇尚的道德觀一樣,極力效忠韓國,後來他被一向嫉妒他的老同學所害,大概也是無法逃脫的宿命。
秦王政授權李斯對於韓非全權處置時,曾對李斯笑言:「著書、立論、言權術,斯不如非;然縱衡、捭闔、行權術,非不如斯矣。」這是小說寫得最引人入勝的地方,從秦王政與李斯互動的這一幕來解讀韓非的不遇,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現代啟示:一個組織裡的領導者或是企業老闆,他的性格便決定了企業文化與企業的未來。
韓王懦弱苟安的性格,使他不敢放手一搏。韓王為了避免得罪秦國,一直不願起用韓非,韓國從韓非年少起,幾十年來,不僅無法國富兵強,最後甚至免不了覆亡的悲劇;而秦王政霸悍勇武的性格可與韓王大不相同了。秦王勇武有謀,知人善任,決定起用與自己同樣野心勃勃的李斯,更使他如虎添翼,一步步向外攻伐,擴張勢力範圍,統一天下。韓王與秦王完全互異的性格,最後也決定了韓國與秦國迥然不同的命運。
(本次對談內容取自《韓非子》,實學社出版,遠流發行))
最新更新日期:92.06.11
→歷史資料回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