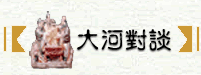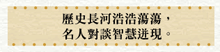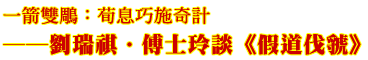|
 虞國與虢國結盟,一心稱霸中原的晉獻公深知,若攻打其中一國,另一國勢必馳兵來援,晉大夫荀息於是獻上「假道伐虢」一計,以借路之名,行攻佔之實。
荀息派人唆使犬戎侵擾虢國邊邑,趁虢公率兵出征之際,再獻計晉獻公以垂棘美璧及屈產良馬,贈予虞公,順利借道入虢,迅速攻取虢國下陽關;後來荀息更獻出美婢至虞,以為二度借路的籌碼,結果一舉攻克虢國,並於班師途中,消滅了虞國。 虞國與虢國結盟,一心稱霸中原的晉獻公深知,若攻打其中一國,另一國勢必馳兵來援,晉大夫荀息於是獻上「假道伐虢」一計,以借路之名,行攻佔之實。
荀息派人唆使犬戎侵擾虢國邊邑,趁虢公率兵出征之際,再獻計晉獻公以垂棘美璧及屈產良馬,贈予虞公,順利借道入虢,迅速攻取虢國下陽關;後來荀息更獻出美婢至虞,以為二度借路的籌碼,結果一舉攻克虢國,並於班師途中,消滅了虞國。
利益與道義的抉擇
 劉瑞祺(成功大學藝術系教授,以下簡稱劉):春秋時代,虞國內亂,虢國君主出兵幫助平亂,虞國因此與虢國歃血為盟,結成兄弟之邦。不久,晉國欲伐虢,向虞國借道,送玉璧良馬給虞公,虞公為了一塊美玉、幾匹駿馬,立刻答應借道,引晉兵入虢,這實在不講道義,而且毫無遠見。 劉瑞祺(成功大學藝術系教授,以下簡稱劉):春秋時代,虞國內亂,虢國君主出兵幫助平亂,虞國因此與虢國歃血為盟,結成兄弟之邦。不久,晉國欲伐虢,向虞國借道,送玉璧良馬給虞公,虞公為了一塊美玉、幾匹駿馬,立刻答應借道,引晉兵入虢,這實在不講道義,而且毫無遠見。
 傅士玲(TO'GO生活情報叢書部副總編輯,以下簡稱傅):當初虞公收下晉國進獻的璧馬,並答應借道給晉國時,並不知道晉國居心叵測,他是聽了晉國大臣荀息的一面之詞--晉軍只是借路去向虢國問個清楚:為什麼虢國要侵犯晉國邊境?
傅士玲(TO'GO生活情報叢書部副總編輯,以下簡稱傅):當初虞公收下晉國進獻的璧馬,並答應借道給晉國時,並不知道晉國居心叵測,他是聽了晉國大臣荀息的一面之詞--晉軍只是借路去向虢國問個清楚:為什麼虢國要侵犯晉國邊境?
劉:有些大臣告訴他提供給虢國過路方便,將會給虞國帶來危險,但他根本聽不進去,還給自己找理由。我發現虞公的處世邏輯很簡單,他凡事只求「合算」,晉國送來玉璧良馬,而他只不過借個路,不花分文,所以就爽快地借出去了。我看虞公改名叫「愚」公還差不多。
傅:這樣說太嚴重了吧!我倒覺得虞公是個愚得很可愛的人,他為人老實又容易相信別人,所以才會上當受騙。我們當中有很多人也跟虞公一樣,伸手不打笑臉人,面對別人的巧言善誘,不但不懂得如何拒絕,還會說服自己說「應該」沒什麼問題,全然相信對方,將自己的權益(如:財產、信用、名譽……)都借給別人使用,到發生問題時,才後悔莫及。
劉:要騙人的人總是巧舌如簧,虞公的是非觀念如此容易受到挑撥、改變立場,可見虞公既沒原則又有投機心理,他寧可背棄一同立下血誓的虢國,而換取一個超級強國脆弱的友誼,他沒有想到晉國為何要跟他作朋友,是不是他在現階段還具有某種利用價值?在那個大國吞併小國、強國欺壓弱國的時代,他竟然一點憂患意識都沒有。
傅:這樣太苛責虞公了。他單純地以為晉國欲與之交好,加上棄弱附強原本就是正常的政治生態,所謂的「邦交國」、「友國」、「同盟國」都要在某些特定條件下才能成立。虞公面對情勢逆轉,看著超級強國晉國笑盈盈地向他招手,他實在難以抗拒大國主動示好的誘惑,後來他想見風轉舵以保全虞國,也是可以被理解的作法。
劉:你所說的,大抵不離人性中最幽暗而深切的質問:在面對利益與道義,只能二選一時,我們應該怎麼做?
色字頭上一把刀
傅:在假道伐虢的謀略中,扮演著關鍵性角色的,是那位被指責為亂國的驪姬。
在中國古代的父權社會下,女人不但享受不到應有的尊重,而且還常常被當成談判的籌碼(如:驪姬、少姬)、使計時的一顆棋子(如:夏荷),甚至只是一種戰利品,任人掠奪。她們沒有自主權,只能任憑命運擺佈。
劉:可不是嗎?女人一旦參與政治,就會被罵成「婦人干政」,小說中的驪戎公主--驪姬便是一例。晉獻公殺死她的父母、屠戮她的族人,甚至蹂躪她與年少的妹妹,燒毀了驪戎人世世代代安居樂業的綠色原野。午夜夢迴,驪姬想起國破家亡及身心受創,恨不得立刻死掉,結束一切痛苦。但是,她不能--因為她要照顧妹妹,也因為仇恨未雪。
傅:驪姬為了報仇,表面上推崇太子申生,在晉獻公面前故作委曲求全的可憐狀;背地裡卻譖惡太子申生,害得申生走上絕路;公子重耳與夷吾狼狽出逃。驪姬的所作所為,搞得晉室雞犬不寧,在一般人眼中,是典型的「婦人亂國」。
劉:與其說她是典型的婦人亂國,不如說她是典型的母親,這點我與書中的荀息所見略同,哪個女人不想要自己的兒子當太子?尤其驪姬並不是一個只靠美色媚惑國君,與其他姬妾爭風吃醋的花瓶。晉獻公酒醉跌倒後,她衣不解帶,寢不安枕;晉獻公生了病,她也知道「夫有疾飲藥,妻先嚐之」的古訓。而她的復仇大計,連唯一的親人(妹妹少姬)都必須加以隱瞞。驪姬年紀輕輕,揹負了這麼多沉重的包袱,令我不得不對於處在亂世中的她,有著一份深深的同情。
傅:我倒覺得真正的始作俑者應該是晉獻公。驪姬害死太子申生,其行不可恕,但其情卻可憫。
如果說歷史上的君王因寵愛某個女人而亡國,那個女人總要揹上千古罵名,連史官都要記上驪姬一筆,說晉獻公愛之,「是以亂國」。事實上,當一個男人毀在女人手上,他應該好好反省,為什麼要貪圖美色,沉溺在溫柔鄉裡,竟至賠上了自己花了數十年心血、得來不易的一切?人們在不同的年紀或許需要不同的刺激與感情的慰藉,但在尋找情感慰藉的同時,似乎也該小心那會不會是個致命的陷阱……。
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女人,根本毫無政治地位,驪姬知道這個事實,但她想到既然男人可以用武力征服他國,佔有女人;女人為何不能同樣以肌膚之親降服男人,取得天下?驪姬化思想為行動,來個「反其道而行」,將晉獻公玩弄於股掌之間。她受到荀息「假道伐虢」的啟發,立刻仿照此計的精神,聯合次要敵人(公子夷吾),打擊主要敵人(太子申生);等到除去了主要敵人,立刻又使晉獻公追殺這位昨日的同盟,可見得驪姬頗具靈活的政治細胞。
身為女人的驪姬雖然不具任何政治權力,但是她運用美色與才智,在權力鬥爭的縫隙中,巧轉周旋,讓人見識到女人在政治領域中,具有這般不可忽視的殺傷力,也讓我們看到了父權社會下,慣於被支配的女人對世局的反擊。
誰是永遠的朋友?
劉:人們一提到政治,總認為在這個領域中,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傅:那個有著堅貞誓言的盟友,很可能是把我們逼上死路的人,歷史上多的是這樣的例子,如:孫臏與龐涓、韓非與李斯,乃至於《假道伐虢》裡的荀息與里克、屠岸夷與邳鄭……等等。功名利祿,往往可以使兩個生死至交變得形同陌路,甚至反目成仇。
好朋友會變成最強大的敵手,除了利益因素外,也可能因為政治理念不同--例如晉國的謀略家荀息與大將軍里克。他們二人曾經把酒言歡、共同完成「假道伐虢」大計;在他們心中,公子重耳是最適合的君位候選人。但後來荀息卻執意依晉獻公遺願,扶立奚齊登基,他認為「為臣者以忠為本」。最後,他不可避免地與老戰友里克、屠岸夷兵戎相見,終於慘死在屠岸夷手裡,令人為之扼腕。
劉:荀息絞盡腦汁為主公劃謀獻計。先是利用「美人計」香餌釣虢,接著又二次獻上「假道伐虢」之計,順利地滅掉了虢國和虞國。
荀息曾以「賢臣擇主而輔」勸虢國大夫舟之僑易主而事,既然荀息認為重耳是理想的繼位人選,就可以將晉獻公的遺言,視為病中昏憒所說。如果荀息不要這麼「死忠」,或許晉國國運將更強大,重耳也不用在流亡了十九年之後,年近花甲才稱霸中原。
然而,荀息經過一番掙扎,還是「不敢有負先君」,他對晉獻公忠心到死的原動力是晉獻公對他的知遇之恩,沒有任何一件事可以超越「報恩」的價值,也因此荀息才會違背自由意志,而去順從底蘊的忠君思想。
劉:百里奚對於虞公的忠心,也給我同樣的感受。當虞公走投無路時,虞國大夫宮之奇勸百里奚一同離開,百里奚卻說當初來投效了虞公,已是不智,「既不智矣,敢不忠乎?」既然不智又繼續忠心到底,這樣的不智之忠不明擺著就是「愚忠」?
傅:虢國大夫舟之僑對虢公死諫,差點慘遭車裂。後來他被貶至下陽,荀息計取下陽關時,舟之僑被俘,但求速死,然荀息的一句「你只是投錯了主」,令他感慨萬千,轉而降晉。這跟荀息、百里奚的忠君思想似乎完全不同。
劉:舟之僑被貶至下陽,不再被虢公賞識,這點和晉國的荀息及虞國的百里奚大不相同。當舟之僑見晉軍攻陷下陽,自己成為俎上肉,但荀息卻以禮相待,並嚴命晉軍不得侵害下陽城的虢國百姓,這讓舟之僑相信,荀息的直屬長官晉獻公應該是個值得他效忠的人,所以他才決定換老闆。舟之僑的「變節」其實比較符合現代人的工作倫理--為公司竭盡心力,宵旰勤勞,卻得不到同樣質量的對待,既然沒有發展的前途,則不如歸去。
就像百里奚對於虞國的存亡所悟出的道理:再高明的水手(臣下)遇上了愚不可及的舵手(虞公),也難以挽回其沉沒的結局。所以,一個優秀的人才一旦加入一個沒有希望的組織,或是遇上了一個不夠睿智的領導者,最後將難逃與組織一同滅頂的命運。唯有組織裡的成員受到信任與重用,那麼當別人前來挖角時,成員才不會輕易離去。
理性的思考,成功的指標
傅:照你這麼說,晉獻公雄才大略,他領導的組織應該是人才可以投奔的好去處吧?
劉:晉獻公在位二十六年,攻滅驪戎、兼併了耿、霍、魏等十五個國家,還攻滅了赤狄、白狄等部落,統一了汾河流域……這就好像公司的領導者,不斷攻城掠地,業務蒸蒸日上,進而吞併許多小公司,而成為頗具規模與份量的大企業一樣。
傅:但是晉獻公嗜殺好鬥,將同宗室的桓叔、莊伯諸公子大肆誣害,甚至全體誘殺,實在是心狠手辣。後來幾位公子潛逃至虢國,晉獻公為了趕盡殺絕,甚至出兵將整個虢國給消滅,最後更在班師途中,順手滅了讓他借道的虞國。
劉:你可以說這是晉獻公的道德缺陷,但並不影響他的成功;相反的,這種為了維護個人利益而表現出來的冷血性格,反而是他在競爭激烈的大環境下,獲致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所以他可以穩坐江山,全力向外擴展。
傅:不過,晉獻公在寵愛驪姬後,事業逐漸走下坡,他在「逆取」之後,卻不懂得「順守」,以至於做了許多錯誤的決定。當太子申生被驪姬設計而丟了性命時,晉獻公仍不知醒悟,他表現出來的是無明又無情,竟連續兩年派人追殺其他的兒子,導致晉室大亂。
劉:如此一來,原本培養好的接班人被毀了,改由幼主嗣沖,使得政局急轉直下,這是中國歷史上許多動亂的根源。晉太子申生德行出眾、聲名遠播,不論領兵作戰或是治理地方,皆功績卓著,不失為理想的守成之君。晉獻公卻感情用事,一心想改立奚齊為儲君,結果造成了國家動盪、社稷不安。由此可見,一個國家乃至於一個公司,領導者若以個人好惡來決定接班人選,都將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
(本次對談內容取自《假道伐虢》,實學社出版,遠流發行)
最新更新日期:92.03.19
→歷史資料回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