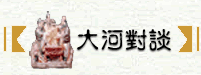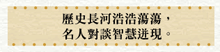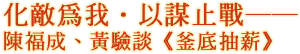|
 《釜底抽薪》描寫的是唐憲宗時代,一位非常與眾不同的軍事謀略家李愬,奉命征討節度使的叛變,在與強敵對峙下,他卻不以戰勝為手段,而以減輕敵我傷亡為最高原則,進行一場一場「避免流血的戰爭」,為了把戰場傷亡降至最低,他放過許多致勝的契機;為了「化敵為我」,他不僅不殺降將降兵,還大量任用敵將。李愬獨樹一格的軍事策略家風格,照亮了他所處的那個大黑暗時代,為唐朝的後半段開啟了中興的契機。 《釜底抽薪》描寫的是唐憲宗時代,一位非常與眾不同的軍事謀略家李愬,奉命征討節度使的叛變,在與強敵對峙下,他卻不以戰勝為手段,而以減輕敵我傷亡為最高原則,進行一場一場「避免流血的戰爭」,為了把戰場傷亡降至最低,他放過許多致勝的契機;為了「化敵為我」,他不僅不殺降將降兵,還大量任用敵將。李愬獨樹一格的軍事策略家風格,照亮了他所處的那個大黑暗時代,為唐朝的後半段開啟了中興的契機。
化敵為我
 陳福成(壽險顧問以下簡稱陳):打從李愬征伐淮西,他就設定敵人只有一個:首逆吳元濟。吳元濟手下的百員戰將、十萬淮西精兵都非敵人。「不是敵人就是朋友」是李愬的最高戰略指導,他頻用招降的手段,「化敵為我」,把吳元濟的一個個大將、一座座城池,收為己用,因此,他每打一場勝仗,便能增加將領和部隊,這與一般戰爭為了打垮敵人戰力、殲滅敵軍,其策略思想截然不同! 陳福成(壽險顧問以下簡稱陳):打從李愬征伐淮西,他就設定敵人只有一個:首逆吳元濟。吳元濟手下的百員戰將、十萬淮西精兵都非敵人。「不是敵人就是朋友」是李愬的最高戰略指導,他頻用招降的手段,「化敵為我」,把吳元濟的一個個大將、一座座城池,收為己用,因此,他每打一場勝仗,便能增加將領和部隊,這與一般戰爭為了打垮敵人戰力、殲滅敵軍,其策略思想截然不同!
 黃驗(實學社總編,以下簡稱黃):李愬的領導風格,也與歷史上所有軍事家截然不同。他剛上任時便對將領說:「天子知我柔懦,能忍受戰敗之恥,所以派我來安撫你們;至於攻戰進取,那不是我的事。」這話帶有謀略的成分,故意要讓敵人窺知他這位討伐軍主帥的作戰意志,但他善於隱忍,而且溫文謙抑,毫無威嚴,倒是完全不似戰場主帥。 黃驗(實學社總編,以下簡稱黃):李愬的領導風格,也與歷史上所有軍事家截然不同。他剛上任時便對將領說:「天子知我柔懦,能忍受戰敗之恥,所以派我來安撫你們;至於攻戰進取,那不是我的事。」這話帶有謀略的成分,故意要讓敵人窺知他這位討伐軍主帥的作戰意志,但他善於隱忍,而且溫文謙抑,毫無威嚴,倒是完全不似戰場主帥。
陳:中國歷代兵法家治軍,不外一個「嚴」字,孫子、吳子、尉繚子都曾以「殺」來樹立軍令如山的紀律,即使最溫和的諸葛亮也要揮淚斬馬謖來維護軍威。李愬完全推翻了「嚴」以治軍的鐵律,相反的,他以寬鬆出名,不僅不殺降兵降將,還完全信任降將,像李忠義、張伯良等來降,李愬推心置腹相待,對其部隊原封不動,立即派去攻擊、守城。套句現代的話說,李愬把前線敵人的師長、軍長、軍團司令招降後,就地將其部隊改個番號,便讓他們率領衝鋒陷陣去了,弄不好,便是縱虎歸山。
黃:是很大膽。降將與李愬要立即建立互信基礎,是一大挑戰。李愬非常大膽地,開了一個很好的範例,然後建立起重用降將的模式,從而使他的寬容與信賴成為一種人格保証,在敵軍陣容中形成了口碑。
陳:用人不疑、推心置腹,也是一種謀略。
黃:他從小慈孝過人,見識過他父親李晟南征北討,為拯救天下蒼生而戰,父親死後,他們十五個兄弟中,唯他與哥哥李憲堅持為父親廬墓三年,被唐德宗勸回,隔天又跑回去守墓。他年少時期的悲天憫人胸懷,成為他日後用人不疑的後盾。
陳:在許多戰役中,李愬與將領們分析戰略時,都充分地運用了《孫子兵法》,歷代兵法家把孫子的「上兵伐謀」奉行得最徹底的,當推李愬。最上乘的策略,是以計謀代替殺戮,李愬比孫子發揮得更好。西方戰略家克勞塞維茨、李德哈達等人均不主張過度使用軍事手段來獲取作戰目標,而主張多用政治、心理等手段。在精神上,與李愬運用「釜底抽薪」之計頗多契合之處。
黃:「釜底抽薪」的策略概念,就是把叛軍吳元濟視為一口巨釜(鍋),釜裡熱騰滾滾,非常強勢;想除去吳元濟這一股炙手可熱的勢力,根本之計,須將那些發光發熱、發揮作用的將領兵士,像薪柴一樣,從鍋底一根一根地抽掉。去薪之釜,其滾滾強勢便失去後勁,便會降溫、冷卻。
陳:李愬「釜底抽薪」的步驟包括:剪枝弱幹與抽薪止沸。「剪」,包括人與地,就是將吳元濟的手下大將李忠義、董昌齡、李祐、吳秀琳、丁士良……一個一個「剪」掉,化敵為我;地就是城池,將吳元濟占領的襄城、葉縣、舞陽、文城…一座座「剪」過來。第二步的抽薪止沸,就是在逐步截斷吳元濟的資源後,戰略目標蔡州城就「止沸」,孤立無援,最後予以擊敗!
黃:「釜底抽薪」有兩種層次的妙用。第一種就是抽別人釜底的薪,使其失勢;第二種是抽自己釜底的薪,形成捉襟見肘。攻下城池,要派兵派將防守(抽自己的薪),當攻占的城池一多,即可能形成自己的負擔。李愬攻占吳房時便是如此,於是在占領吳房後,只收了降將降兵,然後把吳房空城還給吳元濟,讓吳元濟再抽派一位將領及數千兵力去防守,李愬等於是再將敵人抽一次薪,真是妙招!
陳:戰場上以殺人兵器對決,是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李愬卻想與敵人雙贏。「一將功成萬骨枯」的仗容易打;要處處顧忌敵我的傷亡,那高難度了。
黃: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李愬每一場戰役的戰術戰略都不一樣,都創新、出奇,都是在與吳元濟鬥智!
謀高人膽大
陳:李愬用兵的特色是出奇。這個奇,建立在他對地理形勢瞭如指掌,他大膽用兵、用間、用政戰、心理戰,交互使用出奇。他尤善於變化移位,大凡主帥、主力的位置,主攻的路線、如何攻法、埋伏奇襲等,都虛虛實實,讓吳元濟猜不透,造成敵情研判錯誤。
黃:吳元濟與其部將,各有一套亂世中的作賊哲學,讀來令人捧腹,也令人深思。吳元濟造反時說:「權力就住在強盜的隔壁」,「不出去搶,就沒出息」;說他父親吳少陽節度使的侵掠行為是「劫富濟貧,替天行道」;他的部將王仁清被俘時,罵李愬說:「軍人造反,自古皆然,你們忝為軍人,手握重兵,畏首畏尾,比太監更無種。」
吳元濟強悍的領導風格,手上沒有籌碼可以賞功,加上興兵作亂名不正言不順,他所凝聚的這批猛將,不旋踵即被李愬一一抽走。他若多一點智謀,多一分胸襟,那大勢應該是站在他那一邊的!
陳:每個將領要投降前,都天人交戰很久了,當李愬找到很好的切入點時,他們二話不說就降了,譬如有的將領投降,需要下台階或面子,李愬就做場面、親去受降;有的顧慮家屬安危,李愬都為之設想周全。當吳元濟的最後一張王牌董重質困獸猶鬥之際,李愬找董的兒子去送招降信,這一招讓董重質心理防線崩潰,「原本這是一場賭局,在莊家吳元濟的號召下,大家結伴來賭,要賭運氣、賭未來、也賭生死,是一場不折不扣的豪賭,沒想到賭了半天,全部賭友都溜光了,只剩我與莊家兩個人在對賭……」顯見他不折不扣的草莽性格。因為這場賭局不踏實,所以他告訴自己:「只要有一個很好的理由,我就要投降了,現在機會就在眼前。」李愬對人性、心理,可說掌握得恰到好處。
以謀止殺
黃:李愬的頻頻招降重用,收到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用!
李愬處於唐朝國運的下坡路段、「安史之亂」之後的五十年,藩鎮目無朝廷,據地為王,殺人遍野,是個大黑暗時代,由於他征服了淮西,使得大黑暗時代露出一線曙光,也使唐朝出現了短暫的中興的局面!
陳:這位亂世的中流砥柱,以仁治軍,以謀用兵,在他身上,把謀略、計策提升到一個很高的層次,那是真正叫作「仁者無敵」,他的謀,已經不是一般所謂「工於心計、陰謀詭計」之流可相比擬的了。
黃:可以說是以謀止戰,以謀止殺。
陳:也就是「上兵伐謀」。正如小說最後的那句話:「他簡直是在救人,不是在用計!」
最新更新日期:91.05.06
→歷史資料回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