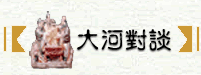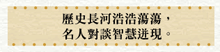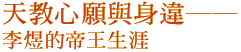| 上天彷彿和李煜開了個大玩笑。
祂給了他詩詞書畫無一不精的文藝天份與感情細膩的浪漫情懷,卻不讓他安度文藝家的悠遊人生;祂吝於賜予他經國治軍的政治才幹,卻又將他推上皇位,去承擔「後主」的稱號。
身當「用武之世」的五代十國,面對如旭日東昇的趙宋,李後主無可奈何地背上家國的重軛,他知道國勢的艱難,但只是擔憂,卻無能為力。在人治的專制時代,君主決定了國家的前途,一個不想也無能作為君主的人,註定將國家帶向滅亡。李後主就是如此走完了十五年的亡國之旅。
真是命運嗎?
 履彊(名作家及政論家,以下簡稱履):看這部書的第一個感想,就是「造化弄人」。一個對皇位無野心,也缺乏政治能力的人,竟然會去當皇帝。這樣不適才不適所,若是太平歲月還好,在那個弱肉強食的五代十國,怎麼能不亡,真有點「天亡我,非『不』用兵之罪」的味道。 履彊(名作家及政論家,以下簡稱履):看這部書的第一個感想,就是「造化弄人」。一個對皇位無野心,也缺乏政治能力的人,竟然會去當皇帝。這樣不適才不適所,若是太平歲月還好,在那個弱肉強食的五代十國,怎麼能不亡,真有點「天亡我,非『不』用兵之罪」的味道。
 陳一銘(實學社編輯,以下簡稱陳):這又回到歷史上最常見的老問題──接班問題。李後主的父親中主李璟本身就是一個闇於政治,也不想當皇帝的人,勉強為之,結果國勢江河日下,只不過當時北方多事,南唐才沒亡在他手上。可惜,他雖然知道這點,卻又重蹈覆轍,立了一個和自己一樣的繼承人,撇開當時艱難的外在環境不談,這樣的選擇本身就很有問題,我覺得南唐亡國,李璟的責任也很大。 陳一銘(實學社編輯,以下簡稱陳):這又回到歷史上最常見的老問題──接班問題。李後主的父親中主李璟本身就是一個闇於政治,也不想當皇帝的人,勉強為之,結果國勢江河日下,只不過當時北方多事,南唐才沒亡在他手上。可惜,他雖然知道這點,卻又重蹈覆轍,立了一個和自己一樣的繼承人,撇開當時艱難的外在環境不談,這樣的選擇本身就很有問題,我覺得南唐亡國,李璟的責任也很大。
履:這麼說也是有理啦,只是也太巧了,李後主身為第六子,卻偏偏上面五個兄長都早逝,李璟會立他,也是遵循「立嫡長」的原則,雖然他也曾想過「立才」──立七子李從善,但最後還是選擇了「立嫡長」,這真是崇尚宗法制度的中國皇室,在繼承問題上的宿命。
陳:其實立儲以嫡長或以才幹各有利弊,只是找一個毫無意願的人繼位,就很少見了,再有才幹,沒有意願也是枉然,這真是令人不解?
履:說不定只是因為後主的「重瞳子」,所以我說是「造化弄人」嘛!
不委屈以累己
陳:不過,既然答應繼位,成為一國之主,那亡國的責任就不能用「命運」一筆帶過。我覺得李後主雖然當了君主,卻沒有因換了位置,就換一個腦袋。在書中,中書舍人潘佑說他帶點水性,在方形容器就是方的,在圓形容器就是圓的。也就是說,其實他是沒什麼主張的,端看臣屬的意見如何,這其實就是把治國的責任交到臣屬的手上,所以我們會看到在他弟弟李從善輔政的時候,他就積極些,一旦李從善不在了,他又變了個樣,缺乏主動性。
履:這就是藝術家的個性吧,他們比較自我,不大會去屈從於環境,我想他答應繼位已經是極限了。照理說,當了君主,應該多去想、多去學如何治國,可是他依然是詩詞歌舞,只做他喜歡的事,還加上沉迷於佛事,自然疏於政事。而且,這點他是始終一致的,亡國後在開封的囚徒生活,他依然是有靈感就直寫、直言,不大會去想忌不忌諱,才會有「小樓昨夜又東風」、「當時悔殺潘佑、李平」,引來殺身之禍。不過也就是這種「不委屈以累己」的性情,才能創作出那麼多的好詞作。
陳:說到他沉迷佛事,我倒覺得是一種逃避,以他的聰明,應該是早看清國家的情勢了,也知道該去改善,但就因為他的個性,他做不到,無能為力,「知善而不能行、知惡而不能去」,這是最痛苦的,要是不知,渾渾噩噩也就罷了,他曾有詩云:「賴問空門知氣味,不然煩惱萬途侵」,這或許便是他遁入佛門的主要原因。
以小事大,難!
履:其實當後周剛建立時,南唐正好達到顛峰,以國力言,是可以分庭抗禮的,可惜因為君主的不同,兩國走向不一樣的命運。不過無論如何,李後主繼位時,南唐的情勢已十分嚴峻,江北之地盡失,宋已取得壓倒性的優勢。而宋的目的非常明顯,就是要消滅唐末以來的割據勢力,重建一個大一統的皇朝,因此它最終是不會讓南唐存在的。面對這種態勢,南唐是很難為的。對抗,則強弱之勢甚明,可以說沒有勝算;妥協,也只是拖時間而已,最終還是會被迫投降。李後主選擇了妥協,這就是他的個性吧!
陳:雖然是如此,但南唐好像是「自暴自棄」,常常是「要五毛給一塊」,退讓太過,讓宋以為可欺,益加侵逼。像李璟,淮南一兵敗,就一口氣將江北十四州全割讓,自動退守長江;李後主則是得知宋屯兵漢陽,就趕緊遣使輸誠,接著貶損制度,這些也都沒有換來善意的回應,只是徒然養大對方的胃口,我想宋後來竟敢直接向南唐要地圖,和李後主這種懦弱的態度不無關係,而宋也順著南唐的退讓,一步步淘空南唐的根基。其實作一些策略性的對抗,讓宋知道南唐是有實力,也會抵抗的,或許可以爭取到更有利的地位。
履:我想這是從統治者的角度來看,其實打仗會造成人員傷亡、經濟破壞,最直接受害的是老百姓,我想固然是李後主沒有野心,但以他的寬厚仁惠,應該也不想生靈塗炭,所以謹守保境安民的政策。儘管國家處境日蹙,至少百姓是免於戰亂的,這也是當他亡國後,仍能受到江南百姓的懷念的主要原因。若是因窮兵黷武而亡國,像隋煬帝,那所得到的只會是咒罵吧。從這點來說,李後主也算是不壞的統治者。
陳:可是他畢竟沒把國家保住。我覺得除了妥協,小國要自保,應該還有方法,就是找到奧援。當時的情形,長江以南還有吳越、南漢,而且宋的背後還有北漢和契丹,若能好好經營,結為盟友,對宋產生壓力,讓它有所顧忌,也是一條生存之道。可惜平時都疏於聯絡,臨危時早來不及,終於被宋各個擊破。
履:這些小國間也有不少矛盾,像南唐與吳越便是世仇,要合作,難!而宋又從中操作破壞,像逼李後主寫信去叫南漢投降便是一例;而契丹是外族,又有石晉的前車之鑑,民族主義使得這樣合作缺乏正當性,所以雖然南唐和契丹有聯絡,卻始終猶豫而不積極。
林仁肇該死?
陳:是啊,最後的結果令人覺得當時出使契丹的潘佑是白跑了一趟。
履:也不會啦,至少救回了一個正儀公主。
陳:潘佑和正儀公主這一段,作者倒是別出心裁,兩人的不婚之戀及花樣年華的逝去,甜而不膩,充滿了浪漫的情懷,是很成功的感情戲,這應該是作者的強項吧。
履:是啊,比起南都留守林仁肇的下場,潘佑是好多了,至少死得明明白白。
陳:說起來林仁肇的死,還真是冤枉,死在這麼粗糙的「反間計」,而且還被摯友親手毒死,以李後主待臣下的寬厚,罪重如皇甫繼勳,都想保全,竟然會對林仁肇毫不留情,我想這固然是張洎等人蓄意誣陷,而最重要的是,「背叛謀反」對任何統治者來說,都是最敏感,最無法忍受的,再如何的寬厚,在這點上也常會失去理智,沒得商量,且絕不會心軟的。這和明思宗殺袁崇煥,差堪比擬,只是明思宗本性多疑褊急,會那麼做比較不令人意外。
履:我倒覺得林仁肇的死和岳飛的死頗有相似之處。他們都妨礙了國家,或者說是統治者的利益與政策。岳飛就很明顯,宋高宗想和金人休兵議和,他卻堅決主戰,這樣的人是一種隱憂,且金人也說,「必殺飛,始可和」,所以岳飛就成了和議的祭品了。而林仁肇的情形也相似,他也是主戰的,曾請求率兵北伐,由淮南直取汴京,這對宋來說是一大威脅,宋當然欲除之而後快,所以會設計除他。而從南唐的角度來看,既決定要與宋妥協,那像這樣的武將,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會不會影響到與宋的關係,都必須加以考量,那現在宋已經點名林仁肇,且設下了反間計,給了劇本,南唐要不要套招呢?所以我想,在當時嚴峻的形勢下,林仁肇是註定要死的,因為他該死。只是,趙匡胤這麼做的時候,沒想到百多年後,同樣的情形,該死的竟是他大宋的猛將岳飛。
法不勝姦,威不克愛
陳:除了林仁肇一事,李後主其實御下不嚴,應該說是失之寬厚,書中提到,有好幾次主戰派大老陳喬和主和的老臣殷崇義兩人就在他面前拍桌對罵,甚至還有肢體衝突,簡直沒有朝儀可言,這也可見後主在他們心中,實在沒有「君威」可言,而後主也不以為忤,再看到他處置皇甫繼勳時的軟弱,完全沒有君主當有的決斷,這就難怪南唐的臣屬驕橫輕慢的多了。再對照宋,趙普和趙光義雖然常有爭執,但卻不敢在趙匡胤面前造次,而趙匡胤處置荊南節度使一事更是明快果決,這就是望之「似不似」人君的差別了。
履:李後主本來就不是這塊料,我想他的作為也不出南唐那些大臣的意料吧。他是個感情豐富的人,看他和大、小周后的相處,尤其是大周后去世後他情真意切的哀傷,這可是史上的君主中罕見的。他也以一貫的感情來對待臣子,像徐遊、張洎等,如同朋友,不明白「主懦則臣驕」。幫他寫墓誌銘的徐鉉說他「賞人之善,常若不及;掩人之過,唯恐其聞」,所謂「雷霆雨露,莫非皇恩」,這「二柄」是缺一不可的。所以徐鉉用「法不勝姦,威不克愛,以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來總結李後主失國的主因。他是一個好相處的國君,卻不是個稱職的國君,不過這也正是他可愛可親的地方。
亡國,卸下重軛?
陳:這樣的性情,也導致他在亡國時,不能死社稷,雖然他大張旗鼓的弄了個自焚台,最後還是沒能與國家共存亡,成為俘虜,還被宋將曹彬說「獨木板尚不能進,畏死甚也」,真是情何以堪!
履:我想,在亡國時,他的心情應該是很複雜的,一方面,把父祖傳下來的江山給丟了,會慚愧難過;另方面,國家亡了,壓在他肩頭的重軛也就沒了,他自由了,或許也有一絲苦盡甘來的輕鬆與喜悅吧!我想就是這樣再無後顧之憂,反而讓他能有勇氣說出心裡的話,而不費心去避忌,固然因此而致死,不過也因此道出他的真性情,留下許多好詞。
陳:該這麼說吧,比起其他的君主,李後主更像是個「人」,他缺乏政治才幹,同時也不受政治的污染,他雖屈從於命運,卻能堅持活出自己,也因此,雖是亡國之君,卻也被譽為詞國帝王,比宋朝開國之君趙匡胤──這個勝利者,更加受到後人的懷念與寬容。
延伸閱讀──
˙《李後主(一)玉樓春》
˙《李後主(二)浪淘沙》
˙《李後主(三)望江南》
→歷史資料回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