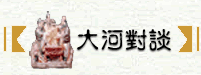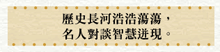|  在中國歷史上,當滿六十年的皇帝之後,自願讓位,改當八年的太上皇,最後以八十九歲高齡壽終的清朝乾隆皇帝,一生酷愛舞文弄墨、附庸風雅,而有「十全老人」的封號。在乾隆的殿前,環繞著三顆超級巨星:紀曉嵐、劉墉、和珅,正邪比鄰,逗趣鬥智,機鋒百出。如果乾隆帝少了這幾顆星,勢必黯然失色。 在中國歷史上,當滿六十年的皇帝之後,自願讓位,改當八年的太上皇,最後以八十九歲高齡壽終的清朝乾隆皇帝,一生酷愛舞文弄墨、附庸風雅,而有「十全老人」的封號。在乾隆的殿前,環繞著三顆超級巨星:紀曉嵐、劉墉、和珅,正邪比鄰,逗趣鬥智,機鋒百出。如果乾隆帝少了這幾顆星,勢必黯然失色。
介於弄臣與諫臣之間的紀曉嵐,在乾隆朝發光發熱,流下許多膾炙人口的機鋒妙趣,《紀曉嵐》一書,以傳記體的筆法,忠實地刻劃了這位愛逗趣搞怪的大學士的一生。
 黃驗(實學社主編,以下簡稱黃):俗話說:「三歲定終生」,紀曉嵐「機智、搞怪」的形象,從小到老都是一以貫之。他從小就顯露出叛逆、打抱不平等性格,譬如捉弄塾師、調戲和尚、替人寫離婚休書等等,都遠超過他的年齡所為,十分異常。他八歲時就頗有進步思想,擅自改寫《正學歌》,以符合時代潮流。這些獨特的性格,看似與生俱來。 黃驗(實學社主編,以下簡稱黃):俗話說:「三歲定終生」,紀曉嵐「機智、搞怪」的形象,從小到老都是一以貫之。他從小就顯露出叛逆、打抱不平等性格,譬如捉弄塾師、調戲和尚、替人寫離婚休書等等,都遠超過他的年齡所為,十分異常。他八歲時就頗有進步思想,擅自改寫《正學歌》,以符合時代潮流。這些獨特的性格,看似與生俱來。
捷才,古今第一
 沈謙(玄奘大學中文研究所所長兼中文系主任,以下簡稱沈):在文人之中,紀曉嵐是一種典型,集機鋒妙趣、叛逆、創意於一身。清朝人物中,金聖嘆、紀曉嵐、鄭板橋為同一類型。 沈謙(玄奘大學中文研究所所長兼中文系主任,以下簡稱沈):在文人之中,紀曉嵐是一種典型,集機鋒妙趣、叛逆、創意於一身。清朝人物中,金聖嘆、紀曉嵐、鄭板橋為同一類型。
這種性格,固然是天生的,但在成長階段,也會受外在環境的影響,李白、杜甫一樣狂放不知檢點,但薰染不同,其性也異,李白喜歡遊仙、道家,最後成為詩仙;杜甫受到儒家的影響,成為詩聖。紀曉嵐也是狂放不知檢點,但他是浪漫之中有節制,所以能遊走於權力中心;金聖嘆是浪漫知中不知節制,因此不容於當道;鄭板橋浪漫之餘,自絕於當道,辭官鬻畫為生。
黃:紀曉嵐記性過人,充分將此一能力運用在文字及言談的機鋒上,產生源源不絕的靈感、急智,成為他的標記,他的優勢。
沈:紀曉嵐的作品,文學價值不高,但他的「捷才」,堪稱古今第一,無人能及。他記性好、過目不忘,能立即反應,尤其對文詞的奇趣非常敏銳,因此常有出其不意的效果。舉例來說:有一次,乾隆帝與大臣們同遊蘇州四大園林之一的「獅子林」,當地人士恭請乾隆為其中一座亭子題名,乾隆題了「真有趣」三個字,很俗氣,但誰敢說不好?紀曉嵐在一旁說:「您的墨寶身價非凡,能否送我一個字,這樣我就什麼都有了。」乾隆問他什麼字?他說「有」字。乾隆准了,亭子便成了「真趣」亭。此二字源自陶淵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之句,紀曉嵐的急智,可謂化腐朽為神奇。
乾隆帝常愛捉弄紀曉嵐,有一次問他「忠臣」的定義,紀曉嵐說了幾種答案,乾隆都不滿意,最後他說: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是為忠臣。乾隆便問道:你願不願當忠臣?他頭皮發麻,不敢違抗,只好去投水自盡。過不久,跑了回來,向乾隆說他自殺不成,被趕回來。原來他在護城河邊正要投水時,河中冒出了屈原,跟他說:你想投河,得先回去問問你的國君,看他是不是昏君?
若是昏君,你再來投河;若非昏君,你卻來投河,不但白死,還會陷你的國君於不義。乾隆帝一聽,也就不好為難紀曉嵐了。這種機鋒妙趣的故事,在《紀曉嵐》這部小說中屢見不鮮,最能代表這位「捷才」的風格與特色。
說鬼大師,以鬼喻人
黃:紀曉嵐的捷才,從小就已露鋒芒,他尚有一大特質:少年多夢幻,幾乎夜夜夢見鬼狐,他從小即愛聽鬼狐、愛講鬼狐,也撰寫大量的鬼狐,堪稱「說鬼大師」,一方面,少年紀曉嵐對不解的事想要探究到底,一方面是鬼故事太充斥了,幾乎與他的生活合而為一了。
沈:紀曉嵐的著作《閱微草堂筆記》,便是鬼話連篇。閱微,寓意「見微知著」,即是從小故事談人生的大道理,他說:人與鬼狐相遇,時時有之,不同的是,你要是心正,鬼狐也要懼怕你幾分;要是心存邪念,鬼狐自然要欺負你。此即是他寫鬼狐精怪的旨趣。
黃:紀曉嵐憑其博學與捷才,走科考之路,雖非一帆風順,卻也能步步高陞。但從兩件事可見紀曉嵐之油滑,一是鄉試前,他對主考官說:紀家子弟不才,寫「也」字不會挑勾。這是打暗號作弊,主考官會意,結果紀家子弟有多人因此高中;一是他的親家盧見曾涉及弊案,紀曉嵐在一個空白信封裡裝入一撮茶、一撮鹽,用醬糊封好,置於空木盒裡,盒外放幾枚棗。以此向盧示警。後來弊案爆發,乾隆帝追查到紀曉嵐洩密,把他發配至烏魯木齊。
從這兩件徇私事件觀之,紀是善良而不正直。
沈:這是遊走灰色地帶。紀曉嵐比較靈光、頑皮、不守規矩,叛逆的本色,使他沒有傳統士大夫的道德包袱,所以他做官也不守規矩,偶而出軌──也可以說是通權達變,用一種機智的手法徇私一下,基本上不算是為惡。
乾隆帝對舞文弄墨甚感興趣,對於機鋒妙趣也頗為欣賞,對紀曉嵐便形成了既愛護,又嫉妒,既競爭,又捉弄,不認輸,又佩服等等非常複雜的情結。
是諫臣,也是弄臣
黃:紀曉嵐能周旋於權力中心,固然是靠機鋒妙趣,更重要的是同時扮演諫臣與弄臣的角色,既討皇上歡喜,又委婉勸諫皇上,這是不容易的事!
沈:既要維護主子的尊嚴、討好主子的歡心,又想規諫其過錯,這是兩難,往往只能取其一,要嘛是弄臣佞臣,要嘛是忠臣諫臣。紀曉嵐是二者合而為一,在扮演諫臣之前,先在某些場合扮演弄臣,他扮弄臣也不是一味討好,往往是奉承之中違逆一下,抬個槓。奉承,是作為勸諫的潤滑劑。
諫君,是高難度的藝術。漢代劉向所著《說苑》一書有「正諫」篇,以前學者解為「正直的勸諫」,其實應是「勸諫之正道」,因為其中的故事都是委婉的。勸諫之道不能太正直,正直往往拂其逆鱗,適得其反,必須另闢蹊徑,掌握技巧,才能奏效。《資治通鑑》記載,有一次,魏徵在朝廷上說唐太宗是昏君,唐太宗大怒,退朝,回到寢宮還在生氣,說:「會須殺此田舍翁」(等會兒殺掉這個鄉巴佬)長孫皇后聽了原委後,回到內室換了禮服出來,向唐太宗說:恭喜皇上,大唐國運昌隆,皇上鴻福齊天。唐太宗不解其意,長孫皇后說:自古以來,敢在朝廷公開罵皇上是昏君,罵完而沒事的,只有現在,可見上有明主,下有能臣。
這段故事,是「勸諫之正道」的最佳註解。即使是正直之士,也好聽美言,何況是一國之君?所謂忠言逆耳,不講究技巧的諫臣,除了激起人主之怒,平白犧牲外,於事無補。紀曉嵐對「正諫」頗有一套,他一定非常熟知《說苑》才對。
黃:紀曉嵐的機鋒妙趣,有時是謀定而後動,像他把乾隆帝的寶物瓷桶砸碎;他掃了嘉慶帝的興,指稱燭中有詐,都屬大冒險,這是運用了幽默技巧中的「逆轉」手法,把負的說成正的,把破壞變成建設,讓人主沒話可說,這是急智之外,屬於搞怪了。
紀曉嵐的三窟
沈:紀曉嵐的夫人馬氏曾說:紀有三窟,一是利用和珅之奸,以奸訓奸,二是利用劉墉之忠,以忠揚忠,三是利用乾隆,以樹歇蔭。知夫莫若妻,這一觀察十分公允。小說裡有一段寫到紀曉嵐與和珅打賭一千兩銀子,說他敢反穿朝服去見乾隆帝,紀曉嵐趁機搞怪,讓和珅貪污舞弊之事曝光,即是以奸訓奸,這故事很精彩,最能襯托出劉墉、紀曉嵐一唱一和的活寶本色。
黃:乾隆帝還算明君,卻縱容和珅貪贓億萬,嘉慶繼位抄了和珅的家,而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之謠。是什麼道理,讓乾隆帝被矇騙到如此地步?
沈:人皆有所蔽──性格上的缺陷,以及視野的死角、思想的死角、愛與憎的死角等等,造成了不可理喻的盲點。組織中最常存在的一種現象,就是老闆(或主管、經理等)對某個部屬產生超乎尋常的偏執,看得順眼的話,便百般縱容;看不順眼,極百般挑剔。成見,如銅牆鐵壁,很難打破,別人冷眼旁觀對他提醒,絲毫不起作用。和珅的貪贓,乾隆絕非一無所知,但和珅帶給他的好感,以及他對和珅的移情作用,遠大於他被和珅A去的那些錢,當然就不會在意了。
黃:這種「交換」好處而共生的現象,普遍存在於現代組織中,一個領導者的身邊,為什麼會伴隨著一個狗腿似的小人?這個小人可能會把老闆照顧得服服貼貼,或讓老闆很有偉大感、安全感,或替老闆扮白手套、做背德的事。老闆從小人那裡充分感受自己存在的價值,以及小人的價值:小人的地位與功能,是無可取代的。他既然如此重要,平常狐假虎威,揩點油水,偷雞摸狗,算是一點回饋,老闆就不管多數人對這個小人是如何反感了。
智之時者,機鋒妙趣
對於紀曉嵐這位傳奇人物,您對他有什麼評價?
沈:如果說孔子是「聖之時者」,紀曉嵐可謂「智之時者」,他的聰明機智,用得恰到好處。中國傳統講究溫柔敦厚,機鋒妙趣不易被發揚,因此紀曉嵐成為中國少有的幽默代表性人物。通常,天才型的人物較有個性,較易逞才使氣,紀曉嵐在逞才之際懂得適時地收斂,這是其成功之處。
黃:現代人比較能欣賞這種類型的幽默,他代表急中生智、化解危機的能力,那正是現代人需要的。
沈:心理學上有個名詞叫「預期逆應」,即與預期之反應相反,出人意外。機鋒妙趣既能化解危機,又回過頭來修理別人,此種危機處理手法,豈不令人激賞!
讀《紀曉嵐》,有助我們瞭解古人的生活、文人的成長與勵志、社會真相或傳聞、被生活壓迫的百姓或女性,都可從紀曉嵐的經歷或他的著作中窺見一斑。他的詩詞聯對,也有助我們腦力激盪,很值得一讀!
(本對談取自《紀曉嵐》一書(實學社出版,遠流發行)
───────────────────
◎延伸閱讀:
•紀曉嵐(上卷)
•紀曉嵐(下卷)
→歷史資料回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