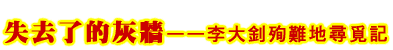| 文/李潔
一夜強冷空氣,把壅蔽於京城上空多日的陰霾蕩滌得無影無蹤。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四日這一天,就成了一個晴得讓人發暈的日子。午後,我和朋友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下約齊,去天安門廣場西邊找一段灰色的高牆。《北京黨史》編輯部的陸兵先生告訴過我:幾年前,他曾騎自行車來找過北洋時代的京師看守所的遺址,但只有一截灰色的高牆尚存於世了。
我們想尋李大釗先生的殉難地。
關於李大釗,我從小就聽得很熟了:他是二十世紀初的北京大學的著名教授,是第一個把馬克思主義引進並傳播到中國各地的思想先驅,是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建人之一,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北方地區的領袖;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被把持北京政府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下令絞死,年僅三十八歲。
想起大釗先生殉難時的年紀,我曾幾次生發出這樣的感慨:如果這位導師沒在盛年時遇害,而是活到一片「赤旗的世界」(李大釗在天安門演講語),那麼,登上天安門城樓向全世界宣告一個共產黨國家在東方誕生的人會不會不再是他的學生毛澤東?一九四九年的李大釗,剛好六十歲,正是治國安邦的黃金年齡啊!
李大釗殉難後的第二十二個春天,他手下的北大圖書館助理員毛澤東與天津南開大學的周恩來等學生們意氣風發地入主北京城。途中,毛澤東曾對身邊的人說:三十年前我就來過北京,遇到了一個大好人李大釗,我就是在他的影響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坐定古都後,新政權的有關部門便將舊時代看守所裡的那台絞殺了李大釗生命的絞刑架,搬進故宮午門下的一間平房裡,供新中國各單位前往參觀。我認識的一位「老北京」就曾隨所在部隊參觀過,他回憶說:那個絞刑架是袁世凱當大總統時從德國進口的,個頭很大,機械很複雜,像一部小汽車似的,上面還有一塊塊的暗紅色的血痕呢!我聽得心驚肉跳,想去中國革命博物館一睹那座殺人機器的欲望一點兒也沒有了——據說那是「革博」收藏的第一件文物,館藏文物編號為○○一。
大會堂西街迤西,是一排排相似的灰瓦灰磚的平房,北部是一道一直延伸到長安街的長長的大牆——平房是皇城根兒百姓們的擁擠住宅群,而大牆則是北京諸多不便標明其單位名稱的禁地。深秋的寒風一把一把地捋著街樹上的葉子,蕭瑟中我記起了這條街的舊名,叫刑部街。
清時,這條街上有大理寺、都察院和刑部。朝代更迭後,新主人一般都是一邊大罵前朝統治者混蛋,一邊卻恬然享用人家的物質遺產甚至精神遺產。所以,中華民國的京師警察廳、法院和看守所繼續借用封建王朝的外殼也就沒什麼奇怪的了。
只是,那一堵僅存的灰色大牆在哪裡呢?
我想,這堵殘存的大牆,應該是專制、禁錮、殘暴、昏庸和沒落的具體呈現。我只想找到它,踹它兩腳。
冷風中,目光也冷。我們走進最南端的西交民巷,開始了冷冷的審視。
西交民巷與東交民巷遙遙相對,那邊是使館街,這邊是金融街——早年的大清銀行、金城銀行、中國實業銀行等都在這條巷子裡,如同現在的西二環路。
寂寂小街上,有個小小的郵政所是老房子,雖說不大的門臉兒是用鋁合金與深藍玻璃新裝修的,但門楣上方的三個模糊了的鑿痕,還是讓我辨出了繁體的「郵電所」幾個字。北洋時代的舊址,似乎僅此一處了。
回到大會堂西街,我不死心,又朝北邊的高碑胡同深處走去。
高碑胡同已是一片狼藉——不斷有搬家公司的民工在搬遷戶的監護下,從陋巷窄院裡抬出冰箱、彩電和家具塞進泊在街口的小卡車裡;而眾多的拾荒者則在興奮地東奔西走,每一處搬空的房子都成了他們的天堂。
牆上的一紙布告告訴了我謎底:
北京市房屋拆遷公告
西房拆告字〔九九〕第一一七號
根據《房屋拆遷許可證》西拆遷字(九九)第一一七號規定,國家大劇院工程業主委員會在西城區(縣)東起人民大會堂西側路,西至兵部窪胡同,北起東絨線胡同,南至高碑胡同(在圖內的)地區的範圍內,進行國家大劇院工程建設,需對上述範圍內的房屋及其附屬物進行拆遷。本地區拆遷價格為每平方米六五○○元。
被拆遷的單位和個人必須服從城市建設的需要,在九九年十一月六日至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內完成搬遷。
特此通告。
西城區房屋土地管理局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五日
原來,這裡要建國家大劇院了,這裡要傳出最為動聽的人聲與樂聲了。或急切或舒緩的旋律,會講述好多年前的一個讓人悚然的故事嗎?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是中國共產黨人永遠也不會忘記的一年。這一年,屍山血海。四月十二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先生麾下的軍隊藉口調處工人內訌,突然朝「友黨」大開殺戒,上海灘的鬧市口很快陳列起身首異處的共產黨人的屍骸。就在「四•一二」 慘案發生後僅十六天,就在我待著的這個地方,甚至也是這樣一個日頭偏西的時候,北方也發生了一起小規模的集體處決——「過激黨領袖」李大釗等二十人,被張作霖任大元帥的安國軍政府特別法庭執行了絞刑。在中國共產主義事業的天平上,北方折斷的這顆頭顱,抵得上南方多少犧牲者的重量?
「要奮鬥」,為什麼一定「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在中國為什麼是「經常發生的」?毛澤東所總結的這些中國現代歷史現象何以出現的?每一次社會進步的代價為什麼注定是層層疊疊的先驅者的屍骸?進入二十世紀的中國難道非要在酷烈的階級仇殺中起步?……
沐著二十世紀末的夕暉,在中國的政治中心之地,我默默地想著這些好沉好重又好難找到頭緒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