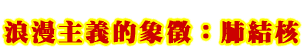| 文/張劍光、陳蓉霞、王錦
工業化對效率、機器和財富的熱心追求已經使人忘卻了內心的感情世界。整齊劃一的生活如此死氣沉沉、僵硬刻板;於是,一批豔羨父輩英雄戰績、推崇個人情感的年輕人在歐洲掀起了一股反叛的文化風尚。這就是強調個性、非理性、想像和激情的浪漫主義運動。
二十世紀英國的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曾精闢地指出,性情古怪的浪漫主義者喜歡奇異的東西:幽靈鬼怪、凋零的古堡、哀愁的末代貴族、催眠術士、異術法師、沒落的暴君和東地中海的海盜。的確,在強調大量生產的工業社會裡,古怪是自我的體現;在煙囪林立、機器轟鳴的城市裡,中世紀的田園生活是最好的夢境;在行程日復一日的商業社會裡,也彷彿只有冒險的刺激才能讓人深切意識到生命的脈動。
崇尚肺結核的病態美
浪漫主義還喜歡病態的甚至死亡的美。德國浪漫主義的代表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說,與「健康的」古典主義相反,「浪漫主義是病態的」。法國詩人波特萊爾以「社會上最有意思的東西——一個女人的面容」為具體對象來談美時也說,「美」就是「能夠同時滿足感官並引起愁思的迷濛夢境;它暗示著憂鬱,疲倦,甚至厭膩之感;或者暗示著相反的感覺——一種熱忱,一種生活的願望,與失意或絕望所產生的沉悶心情中的怨恨相混合」。個體的疾病和死亡,在一個崇尚理性的工業社會中,從不被人重視。人不過是高級的機器零件,壞了、丟了,再換一個就可以了。然而,死亡和疾病在強調個人的浪漫主義那裡卻是無法迴避的命運之劫難。生命一旦喪失,個性與自我還會存在嗎?死亡突顯了生命,也表現出另類的美感。
於是,疾病史上最奇特的事情發生了。浪漫主義者怪異的審美情趣以及對強烈熾情的無比崇尚,在被結核病折磨的軀體和靈魂中找到了最佳的表達。脆弱的軀體彰顯了人類的激情和超越性。秋風涼意中羸弱的身軀、蒼白臉頰上病態的紅暈都被看作是美的化身;潔白手絹上咳出的鮮血更是熾熱的內在生命力的彰顯。結核病成了浪漫主義的最佳伴侶,正如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一書中所指出的:「早在十八世紀中葉,肺結核就和浪漫主義緊密聯結在一起。」美麗女人和英武男人的情慾,成為引發肺結核的精神誘因。
「像肺病患者那樣美麗」
美國作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生於一個患肺癆病的家庭,祖父於1801年死於肺癆,父親也在大量咳血後死去,兄弟約翰大概也患有肺病,妹妹海倫從童年時代起就患了肺結核,於1849年病死,年僅二十二歲。梭羅本人亦長期患病,在治病的旅行中,看到一片斑跡點點、中間仍是翠綠,邊緣卻已緋紅的楓葉,他深切地感到,「衰敗和疾病往往像消耗性肺病的患者那樣美麗」。
詩人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更加奇特,他甚至渴望自己能患上肺結核病,「因為夫人們都會說:瞧那個可憐的拜倫,垂死之時也是那麼的好看啊!」有一次,他的雇工在後院耕地時,掘出一個僧侶的頭蓋骨,拜倫高興地把它送到珠寶店,磨成琥珀色,當作酒杯。他還作了一首〈骷髏酒杯吟〉,以骷髏的口吻寫道,「和你一樣,我活過,愛過,痛飲過/到頭來是死了,把骸骨交給了土壤/把我斟滿吧,這對我毫無損傷/地下蠕蟲的嘴唇比你的更骯髒/盛裝這閃閃發光的葡萄酒釀/可比餵養一窩黏乎乎的蚯蚓要強/以酒杯的形狀,盛裝這神仙的美釀/也比盛裝地下爬蟲的食物更為舒暢」。會客時,拜倫還披上中世紀僧侶的黑袍,舉行宗教儀式。可謂是浪漫主義者的最佳寫照。
大師筆下的「玫瑰色臉頰」
肺結核更是浪漫悲劇的主要素材。在默戈(Henry Murger)的《波西米亞人的生平》中,女主人公弗朗辛是位肺結核病人,她多愁善感、體質纖弱,「臉色像天使一樣蒼白」。然而肺結核使她「玫瑰粉色的皮膚透明得像山茶花一樣潔白」,日益消耗的脆弱軀體中卻「奔湧著青春的熱血」,充滿對美麗人生的無限憧憬。死亡的場面被描寫得更是唯美,與情人依偎在一起,秋日的最後一片樹葉被風吹落在她的身旁,臉上散發著「聖潔的光輝,彷彿死於美麗」。
在小仲馬(Alexandre Fils Dumas)的《茶花女》中,女主人公瑪格麗特「難以描繪的風韻」也是來自肺結核病。她因疾病的消耗身體顯得「頎長苗條」;因為時常有低熱臉頰呈深紅的「玫瑰色」;發燒還使她「細巧而挺秀」的鼻子「鼻翼微鼓,像是對性慾生活的強烈渴望」。然而在冠冕堂皇的上流社會中,紅顏薄命的風塵女子,注定要為純潔的愛情香消玉隕。小仲馬近乎完美地闡釋出肺結核所隱含的淒美的浪漫主義意象。
然而,當一味強調內在情感衝動的浪漫主義,徹底地忽視了現實的道德後果時,整個浪漫主義運動不可避免地為現實主義所替代;在1945年科學家發明了特效藥物鏈黴素等抗生素後,結核病也可以治療。由於以上兩個原因,肺結核便逐漸失去了它的浪漫主義意蘊。
|
| 本次內容摘錄自《流行病史話》
最新更新日期:94.08.11
→歷史資料回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