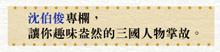|
|
||||||||||||||||||||||||
|
|||
| 一隻鳥不肯叫,司馬懿會等牠叫 | |||
|
文/秦濤 十三歲少女殺人事件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這天天氣晴朗,司馬懿吩咐下人們把自己的藏書拿出去曬一曬,以防發霉生蟲。他自個兒照常躺在床上。 突然,暴雨滂沱。司馬懿是愛書之人,他對書的喜愛,是本能性的,不受大腦控制,直接由神經作用於肢體。 司馬懿一躍而起,跑到院子裡搶救藏書。 院子的一角,一個剛剛進來的婢女近距離目擊了這一切:風痹已久、癱在床上的司馬懿突然身手矯健地在雨中收書。婢女嚇得捂住了嘴,跑出門去。司馬懿忙著收書,沒有察覺。另一個剛剛進院子的人卻看到了。 司馬懿的妻子張春華。 張春華尾隨婢女出去。過程有點血腥,此處刪節數百字。總之,張春華親手把婢女做掉了。具體怎樣處理屍體,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只知道,根據史書記載的推算,張春華今年大約十三四歲。 張春華做掉了婢女以後,冷靜地親自做飯。從此以後家裡不再請婢女和下人,一切家務都由張春華一手承擔。 我始終覺得中國歷史上有些夫婦是絕配,比如劉邦和呂雉,再比如司馬懿和張春華。有其夫必有其婦。 司馬懿得知此事以後,對妻子大為器重。從此也更為謹慎,認真裝病。 這一裝就是好幾年。 這裡有幾個問題,我們來澄清一下,不感興趣的朋友請直接跳過看下一節: 第一是司馬懿裝病裝了多久的問題。 關於這件事情,書上沒有明確的說明。涉及此事的,首先是《晉書•宣帝紀》:「漢建安六年(二○一),郡舉上計掾。魏武帝為司空,聞而辟之。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堅臥不動。及魏武為丞相,又辟為文學掾,敕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曹操做丞相,是建安十三年(二○八)的事情。從建安六年首次征辟司馬懿,到建安十三年第二次征辟,間隔七年。中間司馬懿沒有任何行事可記載,說明他這段時間可能一直臥病;而七年之後,曹操說「若復盤桓」,說明司馬懿這段時間一直「盤桓」著。 其次張春華的傳記裡提到的曬書事件:「嘗暴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這次暴雨不可能是曹操征辟當天發生的事,而應該是長期裝病中的某一天的突發事件。由此也可見司馬懿是長期「臥病」。 另外《太平御覽》引的臧容緒《晉書》殘本,記載有所不同。該書說曬書事件被使者發覺,使者回稟曹操,曹操下令強迫司馬懿出仕。這顯然是把時間間隔長久的兩件事情合併在一起了,與本傳不符,不可信。不過這也說明,曬書事件之後,強迫出仕之前,無事可敘。 所以結論是,司馬懿雖然未必臥病七年之久,但長年裝病是沒有疑問的。 第二是究竟司馬懿有沒有裝病騙曹操這樣一件事。 有學者提出,《晉書》關於司馬懿裝病之事是虛構的。原因是為了美化司馬懿,說他忠於漢室,不願出仕奸賊。理由有二:一,司馬懿的父親司馬防、兄長司馬朗、堂兄司馬芝都已經在曹操帳下了,司馬懿也沒有理由產生對抗情緒;二,司馬懿當時寂寂無名,曹操沒理由派刺客強迫他出仕。(見張大可等著《三國人物新傳》) 這裡這位學者混淆了兩個問題。 第一,《晉書》所記載的司馬懿裝病躲避出仕是事實判斷,司馬懿不出仕的原因是價值賦予。原因可能是後人虛構的,但事實卻是板上釘釘的。因為同樣的事實不僅見於〈宣帝紀〉,還見於張春華的傳記。如果說〈宣帝紀〉中還只是順帶一筆美化司馬懿,那張春華的傳記中,四分之一的篇幅都在描述此事,難道也是虛構?把這段虛構去了,那張春華幾乎就無事可敘了。前引臧容緒的《晉書》殘本,也記載了這件事。多書有徵,難道都是美化?不能因為看到〈宣帝紀〉裡有「不欲屈節曹氏」這樣的鬼話,就連「辭以風痹,不能起居」這樣的真話也不信了。所以,此事的斷案是:事實描述基本正確,動機描述有美化之嫌。 司馬懿裝病不出仕的動機,可能有兩個:首先,自抬身價;其次,袁紹雖敗但實力仍在,北方局勢並不明朗,天下未知鹿死誰手。女怕嫁錯郎,男怕入錯行。此時貿然出仕,投錯主公,影響的是一輩子的命運。 第二,所謂的「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不是派刺客去刺殺,而是派探子去刺探。這件事,臧容緒《晉書》描述得比較詳細:「魏武遣親信令史,微服於高祖門下樹蔭下息……令史竊之,具還以告。」可見是刺探而不是刺殺,更不是有些民間傳說的「針刺」。 曹操強迫司馬懿出仕,未必是因為他能力多強名頭多響。這要結合漢末的社會風氣和曹操的行政風格來看待。漢末的真名士淡泊名利或者假名士沽名釣譽、拒絕朝廷的征辟已經成為了一種時尚。翻開《後漢書》,類似記載比比皆是。而曹操厲行名法之治,對於拒絕征辟的行為深惡痛絕。再加上曹操本人雄猜多疑的性格,自然有可能強迫司馬懿出仕。 書歸正傳,司馬懿的「病情」時好時壞,在床上斷斷續續躺了七年,不知何時方是個盡頭。 這七年,曹操已經蕩平北方,殺光袁紹的子弟,還兵鄴城、榮升丞相了;這七年,兄長司馬朗已經在基層鍛煉、歷任三地縣長,最後當上丞相主簿(秘書長)了。 這七年,自己卻在床上躺了七年,肌肉功能都要退化了。司馬懿有沒有後悔自己的選擇,我不清楚。但我想,他應該明白了一點:不要輕易和曹操鬥。 北伐歸來、春風得意的曹丞相,究竟有沒有忘記七年前那個裝病在床的司馬家老二呢? 答案是──當然沒有。 曹操二請司馬懿 之前七年,曹操以一個詩人的激情和浪漫,指揮了一場波瀾壯闊的北伐。袁紹的青、幽、并、冀四州地盤,被一一打平。曹操大軍回來的路上,特地取道碣石。在這觀海勝地,東漢末年唯一有資格看海的英雄曹操望著吞吐日月、波瀾壯闊的大海,一種望見宇宙本原的感受油然而生,胸中豪氣憋鬱已久,不吐不快: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
回到鄴城,曹操就收到了來自漢朝廷的任命通知,榮升丞相。他提拔了近兩年官聲甚佳的司馬朗為主簿,又任命名士崔琰擔任丞相西曹掾,主管選拔人才。崔琰自然念念不忘十四年前見過的司馬家老二,連忙向曹操推薦。而曹操帳下的首席謀主荀彧,竟然也力薦司馬懿。 其實不需要你們推薦,我也早想再會會他了。 曹操找來當年那位使者:還記得司馬懿吧? 使者心想:廢話,這七年來我就沒幹別的。 你去把他請來吧,我要任命他為相府的屬官。曹操頓了頓又說:「如果他還不肯來,就逮捕。」(若復盤桓,便收之) 使者心想:老大,我就喜歡你玩乾脆的。 使者來到司馬懿府第,驚奇地發現三十歲的司馬懿正喜氣洋洋坐在堂上恭候。 七年了,太久了。再不出山,天下都要統一了。天下統一了,就沒我司馬懿什麼事兒了。 使者一怔,揉了揉眼睛:這就是我監視了七年的司馬懿?前兩天還氣息奄奄,怎麼這病說好就好了? 丞相命我來征辟閣下,丞相還說,如果你…… 我去! 使者後面的話被噎了回去。他永遠不會明白,聰明人之間是不必把話說透的。 七年之前,曹操沒有征到司馬懿,七年之後斷然不會仍征不到。曹操用不了的人,斷然不會讓他活在世上。 日本的一個段子,放到三國仍然適用:一隻鳥不肯叫,怎麼辦?曹操會逼牠叫,劉備會求牠叫,司馬懿會等牠叫。 但是,聽起來「等」似乎是最被動的辦法。如果曹操遲遲不來第二次征辟司馬懿,那這七年、甚至司馬懿的一輩子,豈不是白費了嗎? 不會的。司馬懿的「等」,不是消極的等待。因為他心中有數:曹操有必用我司馬懿之理。 曹操與袁紹的抗衡,一定程度上是寒族勢力與世族勢力的抗衡。曹操用人不拘一格,多有案牘小吏、行伍軍人被提拔到高位的。而曹操本人,更是所謂「閹宦之後」,為世族所鄙視。所以,曹操必須拉攏一批世族在他帳下,以表現出他的政府向所有人開放,爭取更多的人站到自己這一邊,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而河內司馬氏,無疑是當地世族的一大代表,屬於必須爭取的對象。這是其一。 司馬朗在曹操的府中任職,在人事任用上能說得上話。而從名義上講,曹操還是司馬防的門生故吏,自然應該用司馬懿。這是其二。 其他與司馬氏交好的世族,自然也不會錯過這個保舉司馬懿、進而與司馬氏進一步修好的機會,以延續世世代代的交情(所謂世交),比如崔琰和荀彧就出手了。這是其三。 以曹操的用人風格,目前為止還真沒有過他用不上的人才。他一定不會輕易放過這個七年前曾經拒絕過他的年輕人。這是其四。 那,回到老問題:犧牲七年時間,代價是不是太高了? 司馬懿如果當年直接出仕,官位難以凌駕兄長之上。司馬懿拒絕平庸,他永遠追求直逼目標的捷徑;儘管有時候這捷徑看上去反而像繞遠路,但最後的事實總能印證司馬懿的判斷。因為有兩句老話,一句叫「以退為進」,另一句叫「欲速不達」。 更關鍵的是,司馬懿第一次如果直接應徵,則根本無法在廣大應徵者中引起曹操的注意。注意力資源,有時候是比官位更重要的資源,是一種官場晉級的潛在資源。得到上級的器重,職未必高,權一定大;如果被上級忽視,職再高,卻可能是個虛位。在中國當官,如果以為職位的高低就等於權力的大小或者油水的肥瘠,那就太天真了。 況且,《易傳》上說:「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作為未出茅廬的司馬懿,直接出山和荀彧、荀攸、賈詡、郭嘉、程昱這些超一流的謀士們PK,顯然不是明智的選擇;這七年,司馬懿並沒有白躺。他大量地讀書,有了更深的體悟;他修養身心,把韜光養晦的功夫修煉到了極致。 十年磨一劍,今朝試鋒芒。 潛龍出山,司馬懿終於有機會直接挑戰相府的智囊們,開始自己的官場生涯了。
|
|||
| ──摘自《權謀至尊司馬懿》 | |||
|
最新更新日期:2012.08.06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