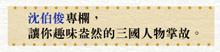|
|
||||||||||||||||||||||||
|
|||
| 在信仰中掙扎的「名士」們 | |||
|
文/周非
信仰危機是政教合一造成的,是智謀文化和大一統文化發展的結果。 中國傳統文化核心價值觀是要在人世間建立「理想國」,因此就注定了中國人的信仰與西方完全不同,同時也因此有人認為中國就沒有完全意義上的宗教。於是乎,無論是漢代的儒教,還是東漢末年創立的道教、以及從東方傳進來的佛教,都在「大一統」文化中,天人合一、政教合一了。皇帝(天子)既是人間統治者,又是大教主。六朝(後漢魏晉南北朝)的帝王將相們在充滿虛偽、殘暴、動蕩、貪婪、荒淫的生活中,演繹了一場「亂世」的歷史劇。從此,信仰危機成為中國文化中的一個大問題。所謂信仰時代,卻正是人們空前的信仰危機時代。 ──作者手記
朝政腐敗、帝王荒淫,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們不再只是一心去當謀士了。他們為了心中的信仰,漸漸演變為「名士」。其實質,是「政」與「教」之間的衝突。 成為名士的條件是什麼呢?是他們無須再依附於皇帝,也就是說,他們不再只有當帝王謀士這一條路了。因為東漢以後,世家大族漸漸形成,他們有了自我生存和發展的土壤了。 世家大族是怎麼形成的呢?原來,東漢以後,皇帝暗弱,貴族們把持朝政,他們在朝中提拔、重用自己的親族為官,形成政治力量;在鄉野則扶持親族不斷占地,形成經濟力量;更有甚者,他們還控制了一些軍事力量。這種政治、經濟、軍事三結合的力量膨脹起來後,一些豪門世族便有了左右一方甚至影響朝政的能力。這就是後來歷史上說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豪族」、「望族」。 在東漢末年,望族裡的一些有「知識」者,面對腐朽的朝廷,一方面受控制皇帝的外戚、宦官們的排擠,另一方面也不恥與那些蠅營狗苟之輩為伍,於是,他們便高標儒家的仁義道德,自闢公府,清議朝政、評點人物,頗有孟子「以天下為己任」、「威武不能屈」的風範。這些人,因為名氣很大,所以,一般稱之為「名士」;又因為他們以儒家道傳人物自居,所以,這一時期的儒教,人們也稱之為「名教」。 東漢時期的名士,以陳蕃(字仲舉)、李膺(字元禮)為代表。陳仲舉常常「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他的一言一行,都被當作天下知識分子的行為規範。他在被任命為豫章太守時,一下車便問徐孺子(當地的名士)所在,要先去看看他。主簿說:「大家的意思是先請長官去辦公室。」陳說:「周武王穿行在大街小巷訪問賢人,席不暇暖。我這樣禮賢,有什麼不可以!」李元禮也是「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當時的後進之士,只要能進他家門,經他品題,「皆以為登龍門」。 由於世族是有錢有勢有名望的階層,所以他們雖然「在野」,一言一行都會掀起波瀾:「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宦官、外戚對名士清議朝政的畏懼可見一斑。結果就有了兩次「黨錮之禍」,即以宦官為主的朝政把持者,大肆逮捕、屠殺以名士為主的知識分子。李膺、陳蕃面對這種恐怖政治,一身正氣、寧死不屈。 但隨著時勢的變化,名士們的抗爭方式也只能「順應形勢」,否則,他們的生命會隨時被亂世裡那些殺人不眨眼的帝王權貴們所剝奪。這一點,我們在三國時期名士代表人物孔融、彌衡身世遭遇裡,會看得很清楚。其中孔融最有代表性。後人說,孔融(字文舉)是名士的一位「承上啟下」的人物。從他的身上既可以看見黨錮名士的餘韻,又可以探微出後世阮籍之流的濫觴。較之「依仁蹈義」的黨人,孔文舉多了「包忍」的一面。曾經有一次荊州劉表違禮越制,私自行郊祀禮,擬於王者。漢獻帝欲責之,孔文舉卻勸住了。他說的話意思大概就是:「您漢獻帝自身尚且如籠中鳥,他劉表遠在湖北,他幹什麼您管得著嗎?萬一同劉表鬧翻了,您也拿他沒辦法,到頭來還不是天子的面子丟盡?!」而換了陳蕃他們,必然早就拍案而起了──這還得了!違禮越制就必須嚴辦嘛!──黨人名士是「依理不顧勢」。孔文舉這一事蹟,體現了一個純粹的儒家人士「投鼠忌器」的一面,這可是迥異於黨人名士的。 但孔融也有抗爭一面,他為官時,常常指責那些當權的宦官及其親信。他遺世特立最出名的是他宣揚「無孝論」,即反對孝道。反孝道就是反朝廷,因為朝廷提倡孝,認為孝是忠的前提,當時選拔官員的方式便是「舉孝廉」。所以,反孝道就有反忠君的意味。為什麼他要反對忠、孝呢?因為他看透了當時的當權者利用儒教(名教)的偽君子嘴臉。名教在他們的手中已經成為功利的工具、陰謀的藉口,所以,他要反對它!他「反孝道」的立論依據是:「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缶中,出則離矣!」這話聽上去,也可謂是振振有辭了。其實孔融也是個大孝子,他父親死的時候,他傷心得差點暈過去,要人扶著才能走路。孔融最後還是被曹操找藉口殺了,其中罪過之一便是「譭謗名教」。 孔融的「高論」、「怪話」開了魏晉名士之先河,同時,晉代以後生活在更為恐怖、高壓、專制、黑暗中的名士們,多採取表面回避現實、繞彎子發表一些更為「怪」、「奇」的高論。……名士們內心的痛苦主要來源於對現實的失望,他們一方面用怪誕的言行表明抗爭,另一方面也在探討人生的新出路,做法是在老、莊哲學裡尋求關於「人生意義」的微言大意。他們這種做法,雖然在哲學觀點和思想體系上與儒家大相徑庭,但在方法論上還是如出一轍的。最後,宇宙人生的理論被他們說得玄而又玄,加之他們標榜的《老子》一書開頭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故而有人稱魏晉名士們的學術思想為「玄學」。 玄學並不是他們超脫現實去討論人類的「終極關懷」,而是為了逃避現實以故弄玄虛。所以,玄學的出現,沒有在中國哲學史上掀開嶄新的篇章,倒是為後來宋明「清議」樹了一個壞典型。
|
|||
| (本文摘錄自《非議歷史:中國歷史的正動與逆動》) | |||
|
最新更新日期:2010.08.16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