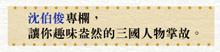|
|
||||||||||||||||||||||||
|
||
|
文/于學彬 周瑜是一個性格內向的人,所以,他對喜怒憂驚都動於情;他又是一個浮躁好勝的人,所以,他又喜怒憂驚都形於色。由於五志過急,便常為情志所傷。無論是喜、怒、憂、驚,周瑜都來得急驟,而且程度也極強。 以「喜」字為例,僅赤壁之戰前後,周瑜表現出大喜過望的樣子就有十幾次之多。如:當周瑜要諸葛亮星夜往聚鐵山斷操糧道,諸葛亮欣然領諾時,「瑜大喜」。在歡迎蔣幹的群英會上,他「大笑暢飲」。當諸葛亮答應三日內交出十萬箭,並寫了軍令狀時,「瑜大喜」。當蔡和、蔡中詐降時,周瑜又「大喜」。當蔣幹第二次過江的時候又是「瑜大喜」。當他看見曹營中被風吹折了中央黃旗時,「瑜大笑」。當孔明答應借三天三夜東風時,「瑜聞言大喜」。當凌統答應暫代他守城時,又是「瑜大喜」。當他以為諸葛亮中了自己的「假途伐虢」之計時,周瑜一路上「時復歡笑」在這些「喜」字之前都有一個「大」字,足以窺見他高興的程度。特別是他臨死前的「時復歡笑」,更可看出他內心難以抑制的興奮。 再說「驚」字,在短短的一段時間內,也有十來次。如:當周瑜請劉備飲宴,初次見到關羽時,「瑜大驚,汗流滿背」。當周瑜夜間登高觀望,看見曹操一邊火光接天時,「瑜亦心驚」,第二天發現曹操深得「水軍之妙」時,又「大驚」。當周瑜得知諸葛亮看破了自己借手殺蔡瑁、張允時,「瑜大驚」。當魯肅報告諸葛亮草船借箭之事時,「瑜大驚」,當諸葛亮借得東風時,「瑜駭然」。當趙雲接走孔明時,又是「周瑜大驚」。當他得知劉備移屯油江口時,「瑜驚曰……」。當他得知甘寧困於彝陵城時,「瑜大驚」。在這裡所「驚」的程度,也全是「大」字。 至於「憂」字,周瑜「憂」的次數雖不多,但這次卻實在「憂」得死去活來。如周瑜在經過一番苦心準備之後,自認曹操可以手到擒來了。一日他站在江岸向對面遙望,一陣風「刮起旗角於周瑜臉上拂過,周瑜忽然想起一事在心,大叫一聲,往後便倒」,「口吐鮮血,不省人事」。無論服什麼藥都「全然無效」。正當大家認為這是「曹操之福,江東之禍」時,還是諸葛亮看透了他的病源,投了「欲破曹公,宜用火攻;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的藥方,才解了他的「憂」。試想,如果不是諸葛亮「解憂」有方,他還要賴在床上不起,那時,說不定東吳真的要被他斷送。周瑜的這種「憂」法,於國於己都十分可怕。 最後是「怒」字。「怒」是周瑜被「氣死」的直接原因,按照周瑜的脾氣,即使不是這次,早晚也會得此下場。他「大怒」的例子很多。如:當周瑜以為曹操真的要「攬二喬於東南」時,「勃然大怒」。當他聽到諸葛亮說他只會水戰時,「瑜怒」。當他接到曹操送來的書信時,「瑜大怒」。當蔣欽兵敗而回時,「瑜怒欲斬之」。當他打敗曹仁,準備收取南郡,發現該城已被趙雲所佔時,「周瑜大怒」。當他得知魯肅又沒有討回荊州,只討得一紙文書時,「瑜頓足」而怒。當他「賠了夫人又折兵」時,「怒氣沖激,瘡口迸裂,昏絕於地」。當他使用「假途伐虢」之計不成,反被四面包圍時「瑜怒氣填胸」,「瑜馬上大叫一聲,箭瘡復裂,墜於馬下。」當他得知劉備、諸葛亮在山頂上飲酒時,「瑜大怒,咬牙切齒」。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周瑜「怒」的程度不僅僅是「大」,簡直到了「極」和「絕」的地步。他甚至可以把金瘡氣得迸裂,把自己氣得昏厥,有如此「功力」之人,實在少見。 《孫子兵法•九地》中說:「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意思是將軍帶領軍隊行軍作戰,處理事情,要沉著冷靜,幽深莫測,嚴肅認真而有條不紊。要做到「無故加之而不怒,猝然臨之而不驚」。如果像周瑜這樣,心理素質極不穩定,情緒意志總是被外界的成敗利鈍所左右,那就不可能取勝。 另外,從醫學的角度講,這種動怒又叫「肝火上升」,其病多因肝氣鬱結,鬱而化火,而致肝火上衝;或因暴怒傷肝,怒則氣上,引發肝火衝逆直上;或因情志所傷,五志過急化火,心火亢盛,引動肝火所致。這就是周瑜為什麼會怒而昏厥,終致於死的原因了。 諸葛亮在《便宜十六策•喜怒》中說:「故君子威而不猛,忿而不怒,憂而不懼,悅而不喜。」意思是君子要有威嚴但不粗野,感到氣憤但不暴怒,心裡擔憂但不畏懼,心裡喜悅但不得意忘形。 所以,無論處於何種環境,是什麼樣的身分地位,都該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緒,培養良好的心理素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知良好的素養,在某些關鍵時刻,比工作能力更為重要。 (本文摘錄自《三國啟示錄》一書) 最新更新日期:2005.08.11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