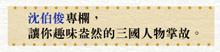|
|
||||||||||||||||||||||||
|
||
|
在《三國演義》的眾多謀士形象中,袁紹的重要謀士沮授、田豐是兩個雖未得到濃墨描繪但卻給人留下較深印象的人物。 歷史上的沮授﹙﹖–200﹚,東漢末廣平﹙屬冀州巨鹿郡,治所在今河北雞澤東南﹚人。他少有大志,長於謀略,曾任冀州牧韓馥別駕,拜騎都尉。初平二年﹙191年﹚,袁紹迫使韓馥讓出冀州,自領冀州牧,沮授向他提出了一個戰略規劃﹕首先擊敗黃巾軍、公孫瓚等對手,奪取青州、幽州、并州;然後「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眾,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復」。這一規劃,與後來荀彧勸曹操奉迎獻帝,然後「奉天子以令不臣」如出一轍。袁紹聽了很高興,當即表沮授為監軍、奮威將軍,使其成為袁紹手下實權很大的重要人物。可惜袁紹雖有雄心,卻胸無偉略,並未徹底實行沮授的戰略規劃,當漢獻帝離開長安,在河東等地顛沛流離時,袁紹竟拒絕了迎獻帝到鄴城的重要建議,結果錯過良機,讓曹操將獻帝迎到許縣(此後稱為許都),從此在政治上佔據了主動。此後,由於沮授幾次建議均不合袁紹之意,加之郭圖等小人從中挑撥離間,袁紹削弱了沮授的權力,並逐步疏遠了他。 歷史上的田豐﹙﹖–200﹚,字元皓,東漢末巨鹿﹙治今河北巨鹿﹚人。他博學多識 ,長於奇謀權略,曾在朝中任侍御史,因不滿宦官專權,棄官歸家。袁紹起兵討伐董卓後,卑辭厚禮請田豐出來輔佐自己,以其為別駕。田豐也曾勸袁紹奉迎漢獻帝,袁紹也未採納。不過,袁紹採用田豐的計謀,消滅了強勁的對手公孫瓚,成為佔據四州之地的最大割據者。可以說,田豐為袁紹集團的發展壯大立下了赫赫功績。建安五年﹙200年﹚正月,曹操東征佔據徐州的劉備,田豐勸袁紹趁機奇襲許都,袁紹卻以兒子生病為由,拒不採納,錯過了又一個千載難逢的良機。在此前後,由於袁紹的另一個謀士逢紀害怕田豐的耿直,多次在袁紹面前進讒言,使袁紹對田豐產生了疑忌。 在關係到袁紹集團命運的官渡之戰中,沮授、田豐都屢次提出正確的建議,卻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拒絕。結果,沮授隨軍出征而不得信用,袁軍潰敗時被俘,因欲逃走而被殺;田豐被投入牢中,袁紹大敗後不僅不承認錯誤,反而為了自己的「面子」而將田豐殺害。兩位奇才,竟都落得如此悲慘的結局! 《三國演義》對沮授、田豐的描寫並不充分,如對沮授為袁紹制定的戰略規劃,便未提及。不過,對他們在一些關鍵時刻的關鍵言行的描寫,仍然相當生動。例如﹕第22回寫袁紹與眾謀士商議起兵攻伐曹操之事,田豐因袁軍剛攻滅公孫瓚,百姓疲弊,倉廩無積,認為不宜馬上興兵,主張「先遣人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稱曹操隔我王路」,爭取政治上的主動,然後穩扎穩打,逐步取勝;沮授也認為此乃良策;而審配、郭圖則力主立即出兵,認為要消滅曹操,易如反掌,顯然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加之許攸、荀諶也主張立即起兵,迎合了袁紹的自大心理,於是立即起兵論佔了上風。事實證明,田豐、沮授的頭腦要清醒得多。第24回寫曹操親統大軍攻徐州,劉備派孫乾向袁紹求助,田豐主張乘虛而入,襲擊許都;袁紹卻因幼子患疥瘡而精神恍惚,拒絕出兵。見此情景,「田豐以杖擊地曰:『遭此難遇之時,乃以嬰兒之病,失此機會!大事去矣,可痛惜哉!』跌足長嘆而出。」作品對田豐憤懣而無奈之狀的描寫,頗為傳神。第25回寫曹操擊敗劉備,奪回徐州,袁紹已經失去進攻的最佳機會,卻偏要在此時攻曹;田豐堅決勸阻,竟被囚於獄中。沮授見田豐下獄,乃會集宗族,盡散家財,與親屬訣別道:「吾隨軍而去,勝則威無不加,敗則一身不保矣!」這已經透出前途未卜的蒼涼心境。隨後,沮授諫阻袁紹以顏良為先鋒,諫阻派文醜輕率渡河,均被袁紹拒絕;結果,事實又證明沮授是對的,袁紹枉自丟了兩員大將的性命。第30回寫袁紹大舉南下,田豐不顧個人安危,從獄中上書諫阻,幾乎被斬首;沮授主張緩守以待時機,也被鎖禁軍中。至此,袁紹的兩位最有才華的謀士都失去了自由,袁紹只能在錯誤的道路上越滑越遠,終於遭到慘敗,而沮授、田豐則白白成了犧牲品。寫到這裏,作者禁不住以詩嘆曰: 昨朝沮授軍中失,今日田豐獄內亡。 沮授、田豐的悲劇,固然有小人進讒的因素,但根本原因還在於袁紹忠奸不分,是非混淆,心胸狹隘,文過飾非,不僅使英雄無用武之地,甚至還害賢掩過,令人憤恨。不過,沮授、田豐自己也有一定責任。作為英傑之士,他們善於綜觀全局,擅長奇謀妙計,卻偏偏不能看透袁紹的本質,非要把自己的命運牢牢地拴在袁紹身上。如果他們稍微開通一點,按照「賢臣擇主而事」的原則,在袁紹已不可救藥時抽身而去,又何至於遭到那樣悲慘的結局呢? (本文選自《三國漫談》一書) 最新更新日期:2003.10.24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