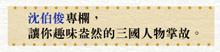|
|
||||||||||||||||||||||||
|
||
|
讀過《三國演義》的人,一般都會覺得虎踞東吳的孫權是一個善於識才用才的明君。 其實,歷史上的孫權和封建時代的許多創業之君一樣,也是一個性格複雜的人物,其一生作為,充滿了矛盾。在人才問題上,他就表現出明顯的二重性。 首先應該肯定,孫權確有識人之鑑、用人之明;特別是在關係孫吳集團安危存亡的關鍵時刻,這一優點表現得更為突出。他先後重用的東吳四任統帥──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都可以說是選拔得當,並稱其職。周瑜在赤壁之戰中以弱擊強,大敗曹兵,不僅維護了孫吳集團的生存,而且為三分鼎立奠定了基礎;魯肅不僅早就向孫權闡明了「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的天下大勢,提出了「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的戰略方針,而且在其執掌兵權期間,堅持聯劉拒曹,鞏固了東吳的基業;呂蒙偷襲荊州,實現了孫吳集團多年來一直追求的佔據長江的目標,大大擴張了它的勢力範圍;陸遜在夷陵之戰中大敗蜀軍,以後又屢次擊敗魏軍,成為支撐東吳江山的棟樑。對於這幾位傑出的人才,孫權放手使用,尊崇有加,甚至脫略行跡,恩禮備至。對周瑜,他視之如兄,親厚異常;當周瑜去世時,他「素服舉哀,感動左右」;直到多年以後稱帝時,他還頗為動情地說:「孤非周公瑾,不帝矣。」(《三國志.吳書.周瑜傳》及注引<江表傳>)就連周瑜的子女,他也特別關照。對魯肅,他始終待以殊禮,比之為東漢開國功臣鄧禹;當他稱帝時,也沒有忘記魯肅,對眾公卿說:「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三國志.吳書.魯肅傳 》)。對呂蒙,他十分賞識,認為其「籌略奇至」,僅次於周瑜;當呂蒙病重時,他極為關切,以重金召募醫者,千方百計為之治療,並隨時觀察其病情,見其能吃東西便喜笑顏開,否則便坐臥不安,夜不能寐;呂蒙病死,他痛哭流涕,悲不自勝(《三國志˙吳書˙呂蒙傳 》)。對陸遜,他倚為干城,極為信賴,特地把自己的印留一枚在陸遜身邊,每當與蜀漢交往書信,總是先請陸遜過目,若有不妥,徑直改定蓋印發出;黃武七年(228年),魏國大司馬曹休率大軍南侵,他以陸遜為大都督,統兵迎擊,並親自為之執鞭:以後,他又讓陸遜輔佐太子孫登鎮守武昌,總督軍國重事。……如此厚待輔弼之臣,實在難得,所以後人往往傳為美談。 然而,孫權也有不敬才、不愛才的時候,有時甚至發展到忌才害才的程度。試看以下幾個例子: 張昭,東吳的開國元勳。早在孫策創業之初,就任命他為長史、撫軍中郎將,「文武之事,一以委昭」(《三國志.吳書.張昭傳》)。建安五年(200年),孫策受傷身危,把年僅十八歲的孫權託付給張昭,慨然叮囑道:「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張昭傳》注引《吳歷》)孫策死後,張昭當機立斷,叫沉浸在悲痛之中的孫權上馬巡軍,並命令各地將校各奉職守,迅速穩定了局勢。以後,他又忠心耿耿地輔佐孫權數十年之久,在東吳享有很高的威望。然而,由於張昭性格剛直,常常犯顏切諫,使孫權下不了台。孫權對他既不太滿意,又無可奈何,便採取讓他坐冷板凳的辦法。孫權初置丞相,張昭乃眾望所歸,孫權卻任命了孫邵;孫邵卒,百官再次推薦張昭,孫權卻又用顧雍為相;不讓張昭當丞相也就罷了,可連「太傅」、「太保」之類榮銜也沒授予,只給了他一個「輔吳將軍」的官號。如此措置 ,未免有些薄情。《三國志》的作者陳壽由此認為孫權的胸襟氣度不及其兄孫策(關於張昭,本書另有<剛直不阿的張昭>一文專門予以評說)。 虞翻,東吳的大學者,勤於治學,著述甚豐,並樂於獎掖後進。孫策奪取會稽郡後,自領會稽太守,以他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然而,由於虞翻「性疏直」,不會察顏觀色, 因而在孫權手下一再倒霉。孫權掌權不久,以他為騎都尉,他屢次犯顏諫爭,使孫權很不高興,加之又遭同僚毀謗,他竟被貶到丹陽郡涇縣,多年不得任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 呂蒙襲奪荊州,因虞翻兼通醫術,請他隨行,才使他擺脫禁錮。孫權封吳王後,大宴群臣,半醉之餘,親自行酒,虞翻偏偏不賞臉,假裝酒醉伏地,不接受孫權斟酒,等孫權離開,他才坐起來。這一來,孫權勃然大怒,拔出寶劍,要親自將他斬首。大農劉基抱住孫權,請他勿殺善士,孫權竟振振有詞地說:「曹操尚且殺了孔融,我殺虞翻又算得了什麼?」經劉基苦苦諫阻,他才寬恕了虞翻。但積怒在心,終難消釋,最後還是把虞翻放逐到偏遠的交州,死後才許歸葬故里(《三國志˙吳書˙虞翻傳》)。 張溫,孫吳集團的後起之秀,才華出眾,張昭、顧雍等大臣都十分推重。孫權開始徵拜他 為議郎,不久又提拔為選曹尚書(主管官吏的選拔任用),徙太子太傅,一度甚為信任。可是,由於張溫出使蜀漢後,對諸葛亮的為政有所稱美(《演義》第86回寫到此事),孫權竟因此而暗生疑忌;又擔心張溫聲名太盛,「恐終不為己用」。於是,他就籍張溫舉薦的選曹尚書暨豔得罪之機,誣指張溫「專挾異心」,「無所不為」,將其罷黜還鄉,使這位英傑之士在抑鬱寡歡之中罹病而死(《三國志.吳書.張溫傳》)。 對於陸遜,上面已經說過,孫權曾經尊崇得無以復加;但當孫權第三子、太子孫和與第四子、魯王孫霸爭寵時(詳見下篇<孫權的立嗣之爭>),陸遜為了維護孫和的正統地位,一再上書 ,建議對二人「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孫權不僅不聽,而且屢次派遣使者上門詰責陸遜。陸遜忠而獲譴,憤懣而死。後來,孫權終於認識到自己對不住陸遜,曾流著眼淚對其子陸抗說:「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總算認了錯。 對比孫權在人才問題上的兩種不同表現,可以看到一種規律性的現象:他的識才用才,主要見於他黃龍元年(229年)稱帝之前,也就是他四十八歲之前。在這將近三十年的漫長歲月裏,他身處內憂外患之中,銳意進取,開土拓疆,深知人才之難得、之可貴,因而能夠不拘一格選拔人才,並能做到用而不疑,對某些人才的缺陷也不吹毛求疵,遂使江東人才濟濟,雄視魏、蜀。而在這以後的二十多年中,由於三國鼎立的局面相對穩定,他承受的壓力有所減弱,而又久握權柄,唯我獨尊,於是驕矜日甚,怠惰漸生,禮賢下士的風度消磨殆盡,忌才害才的行為卻多了起來。所以陳壽在《三國志.吳書.吳主傳》中這樣評論他:「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是的,在人才問題上,他同那位「可共患難而不可共安樂」的越王勾踐相似,也帶有很強的實用主義傾向。 羅貫中在《三國演義》的創作中,將孫吳集團置於陪襯的地位,加之篇幅的限制,不可能充分展示孫權的性格的各個方面,而只能選擇和強化其性格的某一兩個側面。經過這種選擇和強化,孫權的「明主」形象逐步凸現,給讀者留下了鮮明的印象;同時,人物性格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卻遭到削弱。這真是一種不得已的遺憾!
(本文選自《三國漫談》一書) 最新更新日期:2003.04.30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