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然而,上述情節帶有很大的虛構成分。歷史上雖然有「捉放曹」一事,但並非陳宮所為,事情的起因和過程也與《三國演義》所寫的不同。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云﹕ (董)卓表太祖為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 這裏說得很清楚:曹操因為不願與董卓同流合汙,所以避開了董卓的舉薦,悄悄返回家鄉以圖另舉,並沒有謀刺董卓。《演義》虛構曹操自告奮勇謀刺董卓,事情不成又詐獻寶刀等等,是為了表現這個奸雄的大膽和機敏,突出他「雄」的一面。 曹操在東歸途中,確實曾經被捕而又很快獲釋,《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是這樣記載的 ﹕ 出關,過中牟,為亭長所疑,執詣縣。邑中或竊識之,為請得解。 裴松之注引郭頒《世語》說得更為具體: 中牟疑是亡人,見拘於縣。時掾亦已被卓書;唯功曹心知是太祖,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俊,因白令釋之。 在這裏,對曹操獲釋起了關鍵作用的,不是中牟縣令,而是那位慧眼識英雄的不知名的功曹,是他勸說縣令放了曹操。而無論縣令還是功曹,都與陳宮毫無關係,因為陳宮從未擔任過這兩種職務。 另外,曹操殺呂伯奢全家是在中牟被捕之前(呂伯奢本人因不在場,並未被殺),而不是像《演義》寫的,在獲釋之後。對於曹操殺人的原因,裴注引了三種說法,而這三種說法都不涉及陳宮。 總而言之,「捉放曹」這件事,自始至終都與陳宮完全不相干。 歷史上的陳宮與曹操的相識本來沒有什麼戲劇性。《三國志˙魏書˙呂布傳》注引《典略》云:「陳宮字公台,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 這就告訴我們:當中平六年(189年)發生「捉放曹」這回事的時候,陳宮根本沒同曹操接觸;直到初平二年(191年)曹操擔任東郡太守時,陳宮才成為他的部下。這也證明陳宮與「捉放曹」無關。 那麼《三國演義》為什麼要把「捉放曹」這件事加在陳宮的頭上呢?這是因為歷史上的陳宮與曹操的關係經歷了親密合作──一刀兩斷──生死鬥爭的過程,很有典型意義。 歷史上的陳宮雖然不是曹操的救命恩人,但確有大功於曹操。初平三年(192年),兗州刺史劉岱被青州黃巾軍殺死,陳宮馬上建議曹操把兗州抓到手中,以便建立「霸王之業」﹔緊接著,他又跑到州府去遊說別駕、治中等官員,稱曹操為「命世之才」,擔保他能夠保境安民。濟北相鮑信等贊同陳宮的見解,隨即迎曹操領兗州牧,使曹操佔有了一大塊地盤,實力大為增強,這是曹操一生事業的一個重要起點。這時的陳宮﹐對曹操真可以說是忠心耿耿。 但是,陳宮與曹操的親密關係沒過多久就破裂了,這倒不是因為他看穿了曹操的奸雄面目。當時,曹操以討董卓而聞名天下,又尚未挾天子以令諸侯,根本談不上「篡逆」﹔何況天下大亂,群雄並起,智勇之士各為其主,一般不會這樣考慮問題。實際情況是:興平元年(194年),曹操殺了前九江太守邊讓全家,「讓素有才名,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內亦自疑」,這位「剛直烈壯」的角色因此對曹操產生了不滿情緒。正好這時曹操第二次出兵征伐徐州刺史陶謙,派陳宮駐守東郡,陳宮便趁機聯合陳留太守張邈,共迎呂布為兗州牧。一時間,「郡縣皆應」,曹操的地盤只剩下三個縣,處境頓時惡化。從此以後,陳宮便一直站在曹操的對立面,直到建安三年(198年)戰敗被俘,慷慨就戮。 正因為歷史上的陳宮是這樣一個個性鮮明的人物,而歷史上的曹操又確有殺死呂伯奢全家,宣稱「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等惡德劣行和被執於中牟的經歷,羅貫中在精心結撰《三國演義》時,便採用張冠李戴、移花接木等藝術手法,巧妙地將陳宮拉進「捉放曹」故事中,繪聲繪色地描寫了二人的結識,分歧和決裂。這樣,不僅在人物關係上起了刪繁就簡的作用,而且使陳宮的所作所為帶上正義的色彩,使他成為表現曹操奸雄性格的一個有力的陪襯人物。 (本文選自《三國漫談》一書,將由遠流集結出版) 最新更新日期:2001.12.18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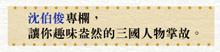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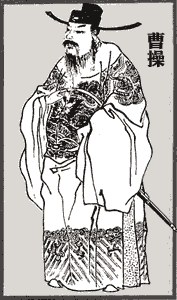 《三國演義》中的「捉放曹」情節,素來膾炙人口;經過京劇和各種地方戲的傳唱,更是家喻戶曉。它寫的是曹操謀刺董卓不成,匆匆逃出洛陽,在中牟縣被捕,縣令陳宮聽他說謀刺董卓是要「為國除害」,回家鄉則要「召天下諸侯興兵共誅董卓」,不禁大為感動,毅然放棄了向董卓邀功請賞的機會,當即棄官與曹操一起出走。而當他發現曹操由誤殺呂伯奢全家到故意殺死呂伯奢本人,並悍然宣稱「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時,馬上判定曹操是個「狼心之徒」,堅決與之一刀兩斷。這個故事,不僅使曹操的奸雄面目第一次得到大暴露﹐而且表現了陳宮關心國事、善惡分明的正直品格。
《三國演義》中的「捉放曹」情節,素來膾炙人口;經過京劇和各種地方戲的傳唱,更是家喻戶曉。它寫的是曹操謀刺董卓不成,匆匆逃出洛陽,在中牟縣被捕,縣令陳宮聽他說謀刺董卓是要「為國除害」,回家鄉則要「召天下諸侯興兵共誅董卓」,不禁大為感動,毅然放棄了向董卓邀功請賞的機會,當即棄官與曹操一起出走。而當他發現曹操由誤殺呂伯奢全家到故意殺死呂伯奢本人,並悍然宣稱「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時,馬上判定曹操是個「狼心之徒」,堅決與之一刀兩斷。這個故事,不僅使曹操的奸雄面目第一次得到大暴露﹐而且表現了陳宮關心國事、善惡分明的正直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