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飯之恩 ◎天籟之音
一飯之恩
「小時候的赤陶飯鍋大多已經消失,瓦斯逐漸取代柴薪和椰殼等天然燃料,電鍋也出現在近代的家庭。然而,我們巴里島人依然公認,以傳統方式煮出來的米飯最為可口。」
開旅行社的N意猶未盡的指指旁邊的司機說:「在他們的老家還吃得到喔。」千方百計連拐帶哄,司機終於答應帶我去看媽媽煮古早飯。
 位在最盡頭的廚房,依文明人的標準只能用簡陋來形容。燻得黑漆漆的那面牆邊,倚著一座磚塊水泥砌成的雙口灶。灶前供有天天獻給火神布拉瑪(Brahma)的椰葉小籃子,內裝香花、米粒和鹽巴。牆上零零落落地掛了刮椰肉器、木製飯匙、椰殼杓子等等。和灶連結的檯子上除了砧板、菜刀,還有較為陌生的小石臼、竹子吹管、陶盆、銅壺和竹編的方型有蓋食籠。另一角,老舊斑駁的食櫥已經歪斜變形,仍在硬撐到底。 位在最盡頭的廚房,依文明人的標準只能用簡陋來形容。燻得黑漆漆的那面牆邊,倚著一座磚塊水泥砌成的雙口灶。灶前供有天天獻給火神布拉瑪(Brahma)的椰葉小籃子,內裝香花、米粒和鹽巴。牆上零零落落地掛了刮椰肉器、木製飯匙、椰殼杓子等等。和灶連結的檯子上除了砧板、菜刀,還有較為陌生的小石臼、竹子吹管、陶盆、銅壺和竹編的方型有蓋食籠。另一角,老舊斑駁的食櫥已經歪斜變形,仍在硬撐到底。
由於語言不通,我在窺探的歉疚和昏暗的光線中,潦草地記下了有如田野調查般的整個過程-老媽把前晚已泡過水的米撈起,連同圓錐形的竹簍(kukusan)沉入赤陶的深鍋先煮約二十分鐘。將未完全熟透的飯取出放在盆裡,澆上開水放置十分鐘後,重新倒入竹簍內,這次是加上蓋子回到深鍋燜蒸。滾燙的白色泡沫不斷泉湧而出,陣陣的熱汽和香味也瀰漫在只有嘶嘶聲響的廚房裡。這樣,又過了二十分,老媽掀開蓋子看一眼飯上的洞穴,滿意地抿著嘴用木杓把熱騰騰的飯挪到方型的竹籠中。
我迫不及待地走上前去,顧不得作客應守的禮儀,伸手就抓起仍然白煙蒸騰的飯粒,塞入流著唾液的口中,一股淡淡的幽香隨即擴散開來。老媽慈祥地笑了,默默遞給我一個小碗。
我轉身向靦腆的司機說:「味道很像泰國的香米耶。」
「媽媽聽說你要來,特別準備了我們平日都捨不得吃的巴里原生種米(beras Bali)。」
緊緊端著晶瑩白飯的手,竟突然僵在漫過全身的暖流中。
註:和我們一樣,巴里島的語言中也清楚分辨稻(padi
)、米(beras)、飯(nas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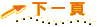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