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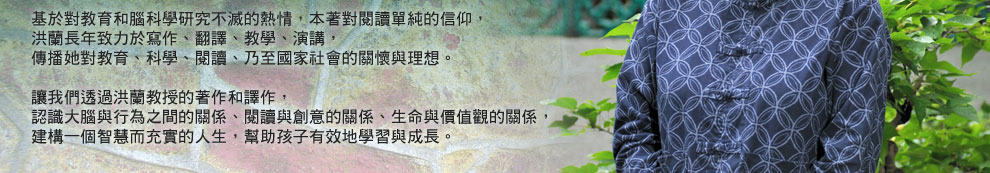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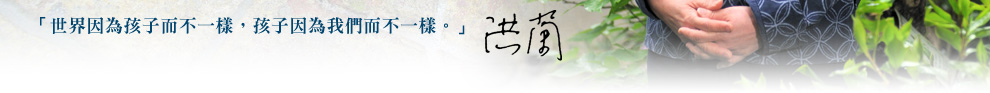 |
|||||||
判斷力的腦科學實驗 中國人說「合」字難寫,跟別人合作時,總是覺得自己做得多,人家做得少。一旦有了這種感覺,在分紅時,就覺得我做得比他多,怎麼分到的錢跟他一樣?這個不滿會像暗室中的草菇,生長得奇快,一旦充滿胸腔,不久就會拆夥了。最近科學家發現這是因為我們仰賴記憶來做判斷的緣故,而我們的記憶是偏頗的,它是以自我為中心做出發點,來組織周邊發生的事情,所以它只記得對自己有利的訊息,把對自己不利的就以「不相干」「不是這樣解釋」拋到九霄雲外,於是人就越來越自以為是,別人都是錯的了。 最近的研究更發現我們對事情的判斷不但受到記憶的影響,還受到當時情境中不相干因素的影響。諾貝爾經濟獎的得主康納曼(Daniel Kahnman)曾經做過一個實驗:他請受試者隨機抽出一個從1到100之間的數字,然後問他一個跟這數字完全無關的問題,如「聯合國有多少非洲國家的席位?」大部分的受試者都不知道正確答案,因此用猜的。想不到他們的猜測居然受到這個隨機數字的影響,假如這個數字是10,他們就猜大約佔聯合國國家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五;如果這個數字是65,他們就猜百分之四十五,非常令人不解。 康納曼說:人在猜測時會不由自主的從那個數字開始尋找,直到他們覺得差不多的時候就停止,然後報告出來。所以看見10這個數字,他們覺得有點太少,就往上加,加到百分之二十五,覺得差不多了就停下來;如果看到的是65,覺得這個數字太大了,就往下減,減到45,覺得差不多了就報告出來。因此起始點低的人會停在可能範圍的最低點,而起始點高的人會停在可能範圍的最高點。照說,如果我們認為這個可能範圍是在25到45之間,我們應該選35,因為這是上下兩點的平均數,最有可能正確,但是顯然人並不是這樣做的。 研究更發現,我們的判斷甚至受到不相干情緒的左右。有一個實驗叫慣用右手的人用左手盡快的聽寫下一些名人的名字,同時要他的右手掌心朝下用力壓在桌面上,另一組則是右手掌心朝上托著桌子的底部,做同樣的聽寫。聽寫完後,實驗者問他們喜不喜歡剛剛所寫下的名人,結果發現右手向下壓的人「不喜歡」的次數多,而右手向上托的人「喜歡」的次數多,因為前者是個負向的手勢,而後者是個正向的手勢。我們的喜好居然會受到完全不相干情緒的干擾,令人訝異。 古人在做重大決策時都要先沐浴淨身、齋戒三日,原來「正心誠意」會使自己比較不受周邊環境無形因素的干擾,進而影響自己的決策。古人有很多經驗上的智慧,我們現在才慢慢了解它背後的原因。有人認為腦科學終究可以將人性剝繭抽絲分離出來,透過這些有趣的實驗,或許有一天我們能了解人之異於禽獸的那個「幾希」了。 ── 本文摘自《理直氣平—講理就好8》 左右不分的大腦 前幾天去參加一位長輩的告別式,因為鄉下地方沒有門牌號碼,只好一路問。我問到一位在門口剝豆子的老人家,她正好認識這位長輩,指示我走到丁字路口右轉,結果右轉後,越走越荒涼,心中想,該不會是左右弄反了吧? 結果真的是弄反了。 這個左右混淆在人類和動物行為上常看到,最近才剛展過名畫《蒙娜麗莎》,請問蒙娜麗莎是朝左邊微笑,還是右邊?她兩隻手交叉放在胸前,是左手在上面,還是右手?人不太區分左右,因為在演化上沒有這個必要,大自然的景色沒有左右之分,而且左邊來的老虎跟右邊來的老虎都一樣會吃人,看到老虎,管它是哪一邊,都要馬上逃命。 所以演化讓對稱深藏在我們的大腦中,連還不會爬的嬰兒都喜歡對稱的東西,他們看對稱的圖形比不對稱的久。大腦一旦學會某個形狀,便馬上登錄它的鏡像。在演化的過程中,對稱節省能量,是個有利生存的好策略。 當然祖先完全沒有料到後人會發明文字,使對稱變成閱讀障礙。 全世界的孩子在初學讀和寫時,都遭遇到鏡像分辨的困難,比如分不清b和d,p和q。我的孩子剛回台灣時,就一直把「都」寫成「陼」。因為文字的發明才幾千年,來不及登錄到基因上,所以大腦只好借調本來處理臉和物體的神經元來處理文字,而它們本來是左右不分的。因此學讀和寫時需要先把這個鏡像本能「反學習」(un-learned)。大腦的適應性很強,很快就不再弄錯,不過偶爾在閱讀障礙的孩子身上還有看到。 我們怎麼知道左右不分是大腦的對稱在作祟呢? 有個實驗是把鴿子的一隻眼睛矇起來,訓練牠單眼辨識垂直對稱,如V和Λ,以及水平對稱,如◢和◣。鴿子的眼睛跟哺乳類不同,牠們是左眼到右腦,右眼到左腦(而我們是左視野──兩個眼睛的右半邊──到右腦,右視野──兩個眼睛的左半邊──到左腦。坊間流行的矇眼來啟發右腦是完全錯誤的),鴿子學會後,實驗者矇住原來的眼睛,讓牠用另一隻從來沒有看過這些圖形的眼睛做選擇,結果垂直對稱沒有問題,但是左右對稱就一直犯鏡像的錯。如果把連接兩個腦半球的胼胝體剪斷,對稱訊息過不去,錯誤就消失了。所以閱讀時鏡像錯誤是大腦的對稱本能還沒有「反學習」的關係。 早期埃及的象形文字可以從左或右開始寫,如果是從左,那麼人和動物的頭都朝左;早期希臘的文字書寫方式則是牛耕式,從左到右,再從右到左,一直到後來才有固定的書寫方向:中文、阿拉伯文、希伯來文從右到左,其餘文字從左到右。 原始的對稱知覺本來是讓我們左右逢源,但是文字這個文化上的發明卻逼著我們選左還是選右,而且一旦形成不對稱,大腦演化的痕跡就會顯現在適應這個或左或右問題上。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歷史果然是反映在腦的演化中。 ──本文摘自《理所當為—講理就好9》 結合大腦科學與基因學,解析行為奧秘 演化心理學家說現代人不快樂,因為人的腦在千百萬年前演化出來時,那時候的人是住在草原上,以打獵─採集為生,人的本性是幾百萬年非洲草原塑造出來的,我們是石器時代的人住在現代的社會裡,所以格格不入,難怪現代人憂鬱症這麼嚴重了。但是演化生物學家的看法不是如此,他們認為大腦是環境和基因共同作用的產物,你是過去歷史的你和生物機制的你不停交互作用所得出的產物。最近從腦造影圖片上,我們的確有看到大腦不停的因為外在的行為而改變內在的結構。 九二一地震後,有受災戶到榮總作創傷後治療,當時榮總已有核磁共振造影儀器,所以精神科蘇東平主任就請他們先照一張基準線(baseline)看當時大腦的情形如何,經過一年治療,再照一張時,發現大腦結構有改變。也就是說,外在的行為改變了裡面的組織結構。我們也看到母親有產後憂鬱症,她的孩子必須即刻抱給別人帶,因為嬰兒才十二個月,大腦照起來就不一樣了。大腦科學的進步改變了我們對教育的看法,既然大腦是不停的因外在環境而改變,那麼就沒有不可教的孩子,或許你教你的孩子是一遍二遍,但是我若教我的孩子一萬遍、二萬遍,我也可以把他教會。我們曾看過一個母親鍥而不捨的將她重度自閉、不會說話的孩子教到可以說話,那真是無限愛心與耐心教導的結果,古人說「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是對的。 過去,哲學家都認為人是自私的,中國人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動物學家也觀察到斑點土狼(spotted hyena)一出生就有很強的頸背、下巴、很長的犬牙及強有力的門牙,如果母狼生下二隻小狼,先出生的那隻便毫不留情的攻擊弟弟,在牠還沒有脫下胞衣之前就把牠咬死;不過第二隻也不是省油的燈,沒有脫下胞衣也已會還擊,最後出洞者是勝利者,所以從動物觀察好像支持了佛洛伊德、霍布斯等人的人性本惡論。但是從演化的觀點來看,人都會死,生命其實太短,短到無法真正參戰,如作者所說「今天才走得好好的,明天就消失了」,因此演化學家認為真正自私的是基因不是人,只有基因才有機會長長久久生存在這世界上。我們身上的基因都是身經百戰、長生不死的基因,它來自我們的遠祖,這個遠祖比他同代的人更聰明、更狡猾、更詭計多端,所以他才能把基因傳到我們身上。 最近二十年大腦知識的累積是過去二千年的總和,過去奉為圭臬的一些基本教條都被推翻了。我們現在知道大腦是一直不停在改變,大腦神經細胞死了可以再生(它在管記憶的海馬迴的齒迴〔dante gyrus〕處);最重要是大腦不是被動的接受訊息,它是主動的搜尋外界的訊息,大腦蒐集、評估、儲存訊息,再根據外界傳進的資料與內部感官的訊息做出行動。它不是電腦,這個比喻是錯的,大腦會因學習而改變,但是電腦不會──不論你怎麼打字,電腦不會因為練習的次數多就改變了內在的電路,或長出新的電路來。電腦壞了就壞了,它不能修復自己;大腦可以,它一直不停因外界需求而改變內在結構或生存上的因應措施。 草原田鼠(prairie vole)的母鼠並沒有固定的時間成熟,牠必須在接觸到無親戚關係的雄鼠尿液中的荷爾蒙化學信號後才會性成熟,只要一點點嗅覺的訊息就可以啟動雌鼠基因的連鎖反應,在二十四小時內,轉變成可以交配的性伴侶。這個原因是草原田鼠為一夫一妻制,母鼠等到沒有親戚關係的公鼠出現後生殖系統才成熟,可以避免近親繁殖,減少生育不健康下一代的機會。大自然的神機妙算,就是最好的科學家也不可能設計出這麼好的方法來防止近親繁殖。所以基因是用經驗來改變大腦對新環境的新挑戰。 人類的行為很有彈性,那是基因對我們的貢獻。不過大腦的發展並非完全由基因掌控,大腦不是盲眼的鐘錶匠,它是基因與外界的互動,而且互動的方式是建構式的學習,只要外在環境一直不變,這功能就不需要登錄在基因上。比如動物身上有一種酶可以從食物中製造維他命C,人類本來也有,但是在人類發展歷史上,因為可以吃到水果,水果中有豐富的維他命C,我們可以完全仰賴外界,沒有必要在身體中製造維他命C,因此我們就把這個酶丟棄了。當然那時並沒有料到人會發明船去航海,在海上長期沒有新鮮水果蔬菜可以吃時,人就會得壞血病了。哈佛大學的平克(Steven Pinker)教授就說演化是個非常節儉的家庭主婦,凡是不必要的東西都不會留。從演化上來看,的確也沒有必要保留不再用到的東西,所以海鞘(sea squirt)剛出生時會在海底游走,尋找最適合居住的地方,當牠找到一小塊珊瑚礁或岩石可以附著了生活之後,牠便將自己的大腦吃掉,因為牠已經不再需要大腦了。 ……未完,全文請見《騙子?情人?英雄?-看大腦科學如何揭露:你是怎樣變成這個你》譯序 改變大腦才是治本 近年來,因為腦造影技術的進步,我們可以在活人大腦中看到這個人在思考、說話、做決策時,大腦各區域線上的工作情形,這個資訊改變了很多我們過去對人的行為的看法。古人說「清心寡慾」其實是很對,因為沒有慾念,就不會有行為,如果要去除一個不要的行為,必須從觀念改正起,而且還得有配套措施,同步加強要的行為的神經迴路才會有效。過去我們只是禁止孩子某些行為,但是沒有給他指出可以做哪些替代行為,結果發現只是一味禁止,孩子會陽奉陰違,心中很想時,還是會偷偷做。現在知道必須用一個我們可以接受的行為去取代不可接受的行為,矯正才有效。 青少年飆車是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常常傷及無辜。美國聖地牙哥二○○二年一年就有十四名青少年死於飆車,三十一人重傷。他們通常是你抓我躲,警力一撤走,他們就出現,防不勝防,禁不勝禁。最後聖地牙哥政府聽從學者的勸告,成立「合法飆車」的專案,將該市美式足球場在沒有比賽時,開放給年輕人飆車,參加者只要繳一點錢,有合法的駕駛執照,有文件證明他是合法的使用這部車子(不是偷來的),便可以去球場飆車。 一開始時沒有人去,因為馬路是免費的,何必付錢做本來免費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呢?這時,配套措施就要上場了,市政府嚴格取締飆車,警察開始用V-8錄影機拍攝違法者,然後叫拖車到飆車者的家裡把車子吊走,用手銬把飆車者帶走,送進監獄。他們用嚴刑峻法逼迫年輕人進入合法飆車場:吊銷執照一年,罰款一千五百美元,執照記點二點,車子入監三十天,罰一千美元。假如你還敢在街上飆車,第二次被逮到時,你的車就永遠被沒收,即使車主是你父母或租來的都不管,你得在牢裡蹲更久。 二○○一年,聖地牙哥郡起訴了二九○件案子,二○○二年一五五件,到二○○三年只剩六十件。這件事會成功是因為執法者和立法者兩者密切合作的關係:一方面強大警力取締飆車,嚴格執行法律,一方面政府提供青少年一個合法飆車的安全場所。到二○○五年,一整年裡聖地牙哥都沒有人因飆車而死亡,只有三個重傷。「合法飆車計畫」提供青少年一個合法的發洩管道,它使不合法的街頭飆車事件急劇下降,減少無辜市民的死亡。聖地牙哥的成功使別的城市紛紛前來取經,在奧克拉荷馬州的諾伯市(Noble),青少年只要花十五美元就可以在星期五的晚上去賽車場賽車。每個月的第二個星期五的晚上,年輕人可以用他自己的車子與諾伯的警察賽車,警察開的是巡邏車,這很像把電玩遊戲中的賽車情景搬到真實世界來,使青少年非常興奮。 現在亞特蘭大、拉斯維加斯和印地安那州的孟斯,都有同樣讓青少年合法發洩的地方。雖然很多父母覺得讓沒有受過特別訓練的孩子去參加時速一百哩的賽車很危險,但是在合法場地中,用的是直線的車道,沒有轉彎,而且只有八分之一哩長,比較不會出事。最主要的是,研究者發現,告訴男孩不要去馬路上飆車不是一個有效的方法,你必須提供他一個合法的選擇。 人的行為是大腦意念的產物,如果能從大腦的觀念中直接改變,觀念正確了,行為也跟著改善了。不過很多時候,壞習慣已形成堅強的神經迴路,這時,責罵和體罰只會暫時性的抑制這個行為的出現,並不能使它真正消失。從早期行為主義的動物實驗中,我們知道一個已被消除的行為仍然會「自然回復」(Spontaneous Re-covery),只是強度沒有原來這麼強,要過許久這個神經迴路的連接才會慢慢鬆掉。如果這個等待消除的時候再給動物一個「增強」(即當時做為獎勵的報酬物如食物或水),這個行為就馬上回復到它原來的強度。就像戒酒的人一定不可以再讓他沾到酒,一沾到酒,哪怕只喝一小口,他過去對酒的慾望與渴求就馬上回復,因此只是禁止效果不好,從神經學上得知,最好的方法是打散原來的連結重新形成我們要的迴路。 大腦的新知識對制定和執行法律的人來說很重要,因為凡事正本清源,只有從源頭改正,行為的改善才會有效。 ……未完,全文請見《順理成章—講理就好7》 大腦不會說謊 教育部在推展有品運動,教學生做人要講誠信,要忠誠、正直、公平、正義。有學生問:誠信有什麼好處?為什麼所有的人類社會都發展出這種的社會規範? 從大腦上來看,「誠信」是個最節省腦力的過日子方式,腦造影的實驗顯示說謊時大腦工作得比說真話時辛苦得多,說謊要說到天衣無縫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只要是假的,就有被拆穿的可能,說一個謊要用十個謊來圓它,大腦就工作過量,人就覺得日子過得很辛苦。 有一個實驗發現說真話時,大腦動用到七個區塊,但是說謊時,十四個地方都得活化起來才能圓謊。謊話說多了一定會露馬腳,因為大腦沒有那麼多資源來記住曾經對誰說過什麼樣的謊,時間一久,記憶痕跡淡退,馬腳就露出來了。 「演化」就如哈佛大學的平克(Steven Pinker)所說,是個節儉的家庭主婦,算盤一打,何必說謊,誠實的過日子比較輕鬆。 警察在偵訊犯人時,常要反覆訊問,因為問的次數多了,大腦就記不得前一次講過什麼(這叫同質性的干擾),前後一矛盾,只好俯首認罪。當然,也有僥倖、搜不到證據的犯人,這時就只好等時間來解決,所謂「真相是時間的女兒」,時間久了,秘密就守不住,真相就出來了。 古代「秋決」是有道理的,人命關天,頭砍了接不回去,所以死刑都是等秋收之後再執行,一方面看看有沒有新證據出來,再一方面,行刑另有殺一儆百的作用,農閒時老百姓才有時間看熱鬧。 古今中外的法官都不敢百分之百確定伏法的人是真凶,因為人的記憶是很不可靠,而且眼見常不為真,會受到先前經驗的影響。但是現在有了直接觀察大腦活動的儀器後,好了很多,因為人會說謊,大腦不會,同一件事,說真話與說謊話大腦的血流量及活化的地方不同。 英國的實驗更利用大腦不同區域的活化情形,來推測受試者的意圖:實驗者先給受試者看支短片,同時掃瞄他的大腦,再請他回憶這支短片的情節,又掃瞄他的大腦,把前後兩次大腦活化的情形作比較,找出處理某個核心訊息的大腦部位,然後藉由活化區域反推這個人在動什麼念頭。也就是說,實驗者想不經由受試者的嘴巴直接從大腦中去推測他的想法。 這個技術一旦純熟,會像DNA用在犯罪偵查上一樣,使被受害人指證歷歷、「化成灰也認得」的被告冤枉得以澄清。這將是第一次在大腦中看到犯罪人的「意圖」(intention),而意圖在量刑上是個重要的指標,有道是「無心犯過者不罰」。 用科學來辦案,用大腦來蒐證,是未來司法的辦案趨勢。美國已有神經法律學(neurolaw)了,台灣還待起步。但願科學能幫助法官做到歐陽修在〈瀧岡阡表〉中說的「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的最高執法正義。 ──本文摘自《理所當為—講理就好9》 |
|||||||
作家檔案|作品熱賣|名家看洪蘭|閱讀與教育|大腦與科學|回首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