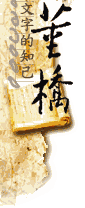![]()
中年是下午茶 蓍草等等 訪書小錄 張五常論文章清楚 讀《知識分子的乳房》
夏天裏鬧乾旱,入秋以來雨就下個不停,果然比較像倫敦。客中聽這些雨聲, 雖然不至於雅得「新愁易感,幽恨懸生」,心情確也不同平常。清初詩人金埴記自己潦倒他鄉,「即尋常書卷,無從假視,旅況之惡可知」。住在倫敦,更談不到貝什麼好中文書,閑中只好逛洋書舊書市,聊以解悶。這裹舊書舖古玩店很多的長巷短街原是灰濛濛的,艷陽下看著委實寒酸,秋雨一來,反倒有些韻味。這時,隨便跨進一爿舊書舖,經常會碰到三兩老頭,圍坐在亂書堆中,人人一付京華倦容的神情。他們說一口考究的英語,濃茶香煙,閒談梨園掌故,市井人情,藏書趣聞,乍聽恍如翻讀前人的筆記雜著。英國人的散文小品一向寫得不壞,當年世道繁華,筆下固然可以旁徵博引,煞有介事;如今是這樣慘澹的光景,所說所寫,可又另有幾分飄渺的意思,故意不去大搔癢處,淡淡白描就應付過去。這樣,算是得了散文妙諦,可也往往是為政的敗筆。
散文而談妙諦,實在相當費解。說是散文影響世道固然行,說世道左右散文也不錯。喬治.吉辛那本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記得有人把書名譯作「草堂隨筆」,古雅得很。後來我偶然想到,這本書既然分成春夏秋冬四個章目去寫,譯成「四季零墨」,大概也行。這本書一九○三年初版,當時吉辛剛死了幾個月,後來前前後後不知道出了多少種版本。前些日子,見過這部書的初版本,索價居然是三十英鎊。今年暮春,我在一個古玩市場上買到的,已經是一九一○年的本子了。那本書裏,意外夾了一張藏書人留下的剪報,是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五號星期天泰晤士報的一篇書評,題為「吉辛的傳世之作」,評的就是當時新印的「四季零墨」。作者考諾理在文末談到今天世人對這本書的觀感,他認為,吉辛筆下的萊克洛夫,其實是個極端小資產階級反動文人,是個和平主義者,憎恨民主,醉心莎士比亞、約翰森、史特恩和藍姆的作品,也喜歡古老英國的烤牛肉,後來決心寄情鄉野山水。與其說他的政治觀點正確,不如說他在性靈問題上的見地正確。他所談的自由、獨立,和文學,今天看來還是很對云云。
當年,機械文明還不像今天這樣囂張,一個人看破世態,往往還可以歸隱田園粗茶淡飯,了卻餘年。後來,機械文明稱霸,政治與階級意識上的分歧日深,讀書人跟社會格格不入,本身又不能突破重圍,擯棄物質的牽制,弄得上下求索,身心憔悴。前幾天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索爾.貝羅,他的小說寫的就是這種心境。至於普通汲汲以求生計的小人物,身在資本主義浮華社會裏,偏又嚮往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理論,心靈上的寂寞矛盾,也就不難想見。可是,這種嚮往,其實也未嘗不可以算是一種精神上的歸隱:萊克洛夫是歸隱山鄉草堂,這些人是歸隱主義理論的故紙堆中。這兩者同樣是出世的;有槍桿子或者有組織,那就比較入世了。當然,那些自甘受政客擺佈的文丑,又該當別論;或者說,乾脆不去論了。
世事原是不容過於苛求。做人做事,看上去乾乾淨淨也就算了。搜訪舊書也是如此。倫敦舊書市固然不乏善本書初版書,還有不少作者題款,名家品題的書,也有很多皮面手裱的百年古籍;這些東西,偶然過一過目,就是有緣,應該滿意。能夠像繆荃孫那樣「博見異書,勤於纂輯」的人,畢竟不多。我搜訪舊書,完全沒有系統,也沒有計劃,說穿了是一股傻勁而已。倫敦賣新書的大書店像超級市場,存書井井有條,分門別類;買書的人不是人,是科學管理制度下的材料。舊書舖裏的藏書則雜亂不成章法,讓人翻檢,讓人得到意外的喜悅,算是尊重人情。再說,新書太白太乾淨太嫩,像初生的嬰孩,教人擔心是不是養得大,是不是經得起風霜;新書也遠沒有幾十年前舊版書那股書卷氣:封面和書脊上的題字總是那麼古樸,加上不經機器切過的毛邊,尤其拙得可人。最要緊的是,開舊書舖的,大半是那些老頭,「其搜輯鑑別,研頤校讎,深詣孤造,各有其獨到之處」,起碼不像超級市場書店那些少爺小姐那麼膚淺庸俗;舉動語言,像電子計算機那麼無理。
【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