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以我個人的探索輕驗來,由於長期的哲學訓練,一向對於無關乎科學知性與哲學理性的所謂「神話」,毫無興趣,認為可有可無。我明明知古希臘神話對於希臘悲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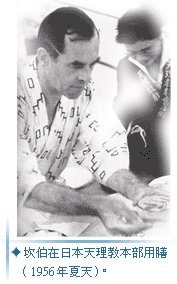 作品、莎士比亞戲劇、近現代許多歐洲文學作品,甚至對於弗洛依德心理分析理論等等,提供了創作靈感與思維資糧,卻未進一步探討神話(學)的價值意義。 作品、莎士比亞戲劇、近現代許多歐洲文學作品,甚至對於弗洛依德心理分析理論等等,提供了創作靈感與思維資糧,卻未進一步探討神話(學)的價值意義。直到三年前罹患淋巴腺癌而險過鬼門關之後,這才開始關注,關聯到有關死後世界或死後生命的宗教(學)或生死學問題的神話(學)探索意義。做為思想家,對於劫後餘生的我來說,死後世界仍然祇屬大乘佛教所說的世俗諦,並非屬於勝義諦,但是我已深深體會到,對於泰半人類來說,死後世界是個極其重要的超越性問題,我不能因為自己仍不在乎而完全抹殺此一個問題。 因此,這兩三年來我開始涉獵了世界各地的神話傳說,也閱讀了一些份量較重的神話學論著,尤其是開拓本世紀神話學探索新路的坎伯的著作,令我眼界大開,擴展了我的學問研究視野,十分了解到聯貫神話學與文化人類學、宗教學、比較民俗學、(超)心理學、心理分析理論、文學藝術等等,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各大部門的科際整合探討意義,我衷心盼望,讀者也能排除過去對於神話(學)的任何偏見,與我分享對於神話(學)探索的興趣。 我讀坎伯教授的一些主要著作,發現他的神話學探索對於我們現代學人偏重純知或合理性的思考方式,有其不可抗拒的衝擊或挑戰性,足以改變我們對於理知與非理知(甚至反理知)的硬性分辨,也足以改變我們厭惡所謂「非理性」的思維偏差。受過尼采鉅大影響的德國實存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與法國後結構主義思想家傅柯(Foucault),都先後指摘此一偏失,而開創解構理論的德希達(Derrida)也指出了,依據哲學理性所表達的「真理」,有時並不見得強過文學的(非理性)想像力所表現的「真理」,也就是說,文學真理與哲學真理難於劃分。 根據他那獨特的神話學探索,坎伯認為宗教與神話其實無甚差別,譬如耶教的天國與地獄之分,佛教的涅槃解脫與生死輪迴之別,印度教的梵我合一與業報轉世之分等等,概皆超越科學知性與哲學理性的限制,根本無從評價其中高低優劣,如將此類宗教信仰,統統看成有關超越性世界的「神話」,則能解放我們的主觀片面性立場,免於獨斷論調,有助於宗教與宗教之間的相互寬容與和平共存。 他尤其推崇印地安族神話傳說,認為此類原始宗教的信仰信念,常優越於各大世界宗教(尤其西方單一神論)的既成教條。我對坎伯此說,很有同感。 在各大世界宗教之中,坎伯似乎比較欣賞大乘佛教,蓋因大乘佛教分出勝義與世俗二諦,終能超越涅槃解脫與生死輪迴之(世俗諦)分別,強調「生死即涅槃」之故。在本世紀的耶教神學發展,曾有受過海德格(Heidegger)影響而的出「聖經解構」旗幟的布爾特曼(Rudolf Bultmann)「非神話化」(de-mythologization)理論,一方面把聖經故事(如創世說)看成一種神話,另一方面強調實存主體性的宗教(耶教)探索意義。這從坎伯解消宗教(教條)與神話之分的神話學觀點看來,並不難理解,雖然此說曾遭遇到保守派耶教神學家的強烈攻擊。 無論如何,坎伯的神話學獨特主張,至少能夠刺激我們重新考察,宗教與神話之間的分合所在,亦有助於我們不帶有色眼鏡,而從比較民俗學與文化人類學以及(超)心理學的嶄新觀點,重新探討神話與宗教的起源與形成過程的來龍去脈。 我從坎伯的神話學探索所學到的另一點是,每一時代、每一社會、每一民族乃至每一個人都有一種神話,問題並不在乎神話的是非對錯,而是在乎它對特定時代、社會、民族或個人所產生的生命意義。神話涉及死後世界、靈魂不朽的探索、文學藝術的想像性表現、夢的世界、英雄崇拜、永恒淨福、宇宙觀、現實與理想的分合等等,做為有限精神的我們人類無法袪除神話,而沒有神話的人生也就變成枯燥無味。 瑞士(超)心理學家榮格(Carl G. Jung),專就從原始社會開世界各地分別產生的神話傳說,發現到人類共通的「集體無意識」以及由此形成的「原型」(archetypes),做為神話學探索的理論根據。坎伯深受榮格此說的影響,且進一步對於各種不同的神話傳說,進行精細的研究考察,終於跳過榮格有限的神話知識,開拓神話學探索的新路,自成一家,功不可沒。 我們今天處在世紀之交,依據坎伯神話學給予我們的探索靈感,應在下一世紀創造出甚麼樣的神話呢?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一日晨四時序於 |
|
上一篇 │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