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嗎?你沒有被俘過嗎?在那個大勢已去的時代,國軍為了保存自己的實力,多少高級將領假裝跟共匪妥協,這有什麼關係?重點是他最後效忠不效忠國家。」
直到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懲治叛亂條例有明確的規定:凡是被俘過的人,不論軍官或士兵,一律判處重刑——從五年到無期。
「我沒有被俘過。」我說。
「你是哪一天被俘的?」
「我從沒有被俘過。」
劉展華的聲音漸漸的凌厲。
「你是哪月哪日被俘的?」
「我從沒有被俘過。」
「好硬嘴,」劉展華大聲說,「你是哪一天被俘的?」
我拒絕承認被俘過,並不是我聰明的知道一旦承認被俘,就全盤瓦解,只是因為確實沒有被俘過。可是,劉展華用一種得意的眼神盯住我,臉上露出不耐煩的表情,不斷的翻轉著拿在手上的米達尺,問說:
「好吧,那你逃出瀋陽的路條是那裡來的?」
「我們自己寫,自己刻印。」
「怎麼刻印的?」
「用肥皂。」
「是誰刻印?」
「孫建章!」
蒼天在上,我的供辭牽連出來孫建章,因為圖章確實是他刻的,而且他可以為我挺身作證。這時候,孫建章在苗栗警察局
當督察長,再想不到,我請他作證,不但救不了自己,反而把他也拖進火坑。孫建章立刻被免職,逮捕歸案。調查局正發愁缺少人證,是我親自把一個活證人送到他們的手中,因為法律上規定,同案被告的口供,可以作為證據。
後來,審問官又多了一位年紀較長的李尊賢先生,集中焦點盤問我被俘的經過。劉展華對我不肯承認被俘,十分震怒,我
可以從他臉上看出來他即將爆炸。這時,我被安排睡在臨時擺在角落的一張行軍床上。我還不知道就在這間審訊室裡,三、四個月前的一個夜晚,調查局把《新生報》的一位女記者,連當時副總統嚴家淦先生都稱呼她為「沈大姐」的沈元嫜女士,全身剝光,在房子對角拉上一根粗大的麻繩,架著她騎在上面,走來走去。沈元嫜哀號和求救,連廚房的廚子都落下眼淚。那是一個自有報業史以來,女記者受到最大的羞辱和痛苦,當她走到第三趟,鮮血順著大腿直流的時候,唯一剩下來的聲音,就是:
「我說實話,我招供,我說實話,我招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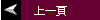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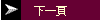
[ 野生動物 ][ 十年通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