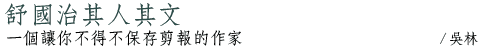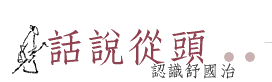
|
舒國治今年四十八歲,七十年代開始寫作,卻讓人不怎麼找得到他的書來讀。二十多年來,不少的讀者一逕保存著「人間副刊」中他的剪報。 他至今,二十多年來,不曾結集出書(所出版過的《1977生活筆記》中的〈人名索引〉、《讀金庸偶得》、《臺灣重遊》皆非歷年文稿結集者)。然他的散文〈自私瑣記〉被收在楊牧編的《中國近代散文選》(洪範);他的1980年時報文學獎作品〈村人遇難記〉被收在詹宏志編的《六十九年度短篇小說選》(爾雅版);他的深度詳寫七十年代漫無跟腳年少生活的〈台北游藝〉被收在楊澤編的《七十年代懺情錄》(時報);他以「舍或之」筆名寫的《小論金庸之文學》短文,被收在《諸子百家談金庸》(遠景版,遠流版更名《諸子百家看金庸(肆) 》),也因此使得遠景出版社的沈登恩邀他寫出一整本的《讀金庸偶得》(遠流);他的短篇〈饅頭與黑板〉被收在焦桐編的《心靈戀歌》(時報);他的華航旅行文學獎首獎作品〈香港獨遊〉被收在楊澤編的《國境在遠方》(元尊文化)及簡媜等編的《八十六年度散文選》(九歌);他的「長榮旅行文學獎」首獎作品〈遙遠的公路〉被收在初安民編的《縱橫天下》(聯合文學);他的〈人在台北〉長文被翻譯成英文,先收在Free China Review的月刊,繼收在《中英對照讀台灣小說》(天下),然讀者們硬是無法讀到一本全是他自己各時期作品的文集,這說來近乎怪誕;至少在臺灣文壇不大有這樣的例子。難怪有讀者必須一直留著他的剪報。 甚至可以說,二十四年前倘不是張照堂、高信疆邀他為《生活筆記》寫那五百個名人小傳、達八萬字的〈人名索引〉,十九年前倘不是沈登恩邀他寫《讀金庸偶得》,三年前倘不是將開畫展的鄭在東邀他寫《臺灣重遊》,他連這三本書也不能問世的。 有人視舒國治為出土的作家;若不是1997、1998他各得一次華航及長榮的旅行文學獎首獎,新上路的讀者根本不知道他是誰。又倘若不是他去年在「人間」副刊寫了一年「三少四壯集」,這些新起讀者對他的印象無法持續加溫烙深。 有人視他為嬉皮式的作家,因他頗寫過一些浪跡美國的文章如〈流浪漢〉、〈午夜特快〉、〈過河〉及〈遙遠的公路〉。也寫過七十年代台北頹廢年少煥散生活下的游蕩種種,如〈台北遊藝〉。 又有人視他為某一類的舊式中國文人,因《讀金庸偶得》及兩萬字長文〈江山依然如畫否──在旅行史料中的無限夢〉幾乎是用文言寫就。〈北方山水〉、〈十全老人〉、〈奇人奇書──高陽〉等小文亦是。 又有人視他為「生活趣味的雜項作家」。乃他寫過〈走馬舊書攤──牯嶺街〉、〈割絕不掉的惡習──逛舊書店〉等「逛」文;寫過〈燒餅〉、〈水餃〉、〈託友人代為嚮導台北小吃〉、〈美國亂吃〉、〈咖啡館〉等「吃」文;寫過〈一個七十年代青年回看搖滾樂〉、〈美國民歌之旅〉、〈再談美國民歌〉、〈公路上的音樂〉、〈三角洲/藍調/交叉路口〉等「聆」文;寫過〈在旅館〉、〈早上五點〉、〈在台北應住在哪裏〉、〈喪家之犬〉、〈哪裏你最喜歡〉、〈賴床〉、〈在途中〉、〈旅途中的女人〉、〈理想的下午〉等「居停」文「上路」文。 然他也不全然只在異鄉。有人根本以為他是專寫「老台北」的作家,因為〈水城台北〉、〈人在台北〉等單篇長文,及〈北郊遊蹤〉、〈永遠的碧潭〉、〈無中生有之鎮──永和〉。 然近年來他最被人們援用的職銜,居然是「旅行文學的作家」。殊不知早在他在1983年大規模旅行前,早已是創作圈內人矚目的純粹文學的耕耘者了。 楊牧在評審時報文學獎時說〈村人遇難記〉的作者: 「運用白話和文言技巧的能力不同凡響;兩種語法交融迭盪,聲東擊西,鑄成一種看似淡漠鬆弛,實則充滿藝術張力的文字風格。」 詹宏志在超過萬字的評〈村人遇難記〉文中說: 「最好的作品使理論家無言以對。因為他是原創的,獨一的,過去的理論與經驗,在它面前顯得困窘,批評家找不到類似的例子,也無法為它在評價中尋找一個適當的位置。」 然而後來舒國治去寫鄉土(如《台灣重遊》)、去寫公路(〈遙遠的公路〉、〈美國汔車〉),去寫台北、去寫吃、去寫武俠小說的風俗(〈武俠小說及其世代〉),去寫旅途、去寫音樂……其實皆是以他深蘊文學的筆力來縝密從事的。 只是舒國治至今成稿不多。套用他自己的話是因為「晃蕩」成性。他遊移到太多的區域及走逛至太遠的地方,結果弄到都忘了回家了。 譬如他被朋友拉去情商演電影,如余為彥導演的《月光少年》,如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及新近得坎城大獎的《一一》,其至楊德昌的《麻將》根本就用舒國治他家那幢舊公寓來拍張震、唐從聖這些遊蕩少年的起居所在。 智利裔的法國大導演豪烏.胡易玆(Raul Ruiz)在拍《追憶似水年華》(曾在台公映)之前兩年,曾來台灣拍了一部《影子喜劇》(暫定名,取材自皮藍德婁的尋找劇中人物的六個演員)的臺灣片,其中一個角色,就找上了舒國治,讓他飾演一個晦澀的隱士般的人物。 他的外務太多,遨遊走赴的地方又廣,又以他的年紀所遇的,所交往如朋友常已是社會上歷綀穩健之士,致使他的過日子方式頗稱悠游自在;他看的山,喝的荼,閱讀的書,聽的音樂,進的小館子,倚靠的城牆,撫摸的古塔,坐下的亭子,開車繞徑的小路等,往往是清幽簡美的;也於是他不免將這些事象寫出來,結果倒成了旅行文學,而也似乎不必是純粹的文學了。 他又安於簡樸,樂得輕便,竟連手機也不曾有。答錄機、傳真機、冷氣機、第四台、電腦,他全沒有。造成別人找他極不容易。 或許也正因為這些遨遊、這些晃蕩,我們才等到他這本《理想的下午──關於旅行也關於晃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