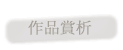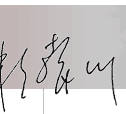|
本文原刊於美國首要劇場季刊《戲劇評論》(The
Drama Review)38卷第二期,該期特別以專題方式討論中國語文劇場,邀請各地中國語文劇場代表人物撰文進行對中國劇場現況和展望的論壇。
撰文者──賴聲川
◎ 中國傳統劇場對你們有沒有影響?若有,是如何?有試圖混合當代西洋技巧和傳統中國技巧嗎?若有,是如何?
傳統中國劇場對我們有過幾種不同的影響。歌劇《西遊記》(1987)的演員陣容中有京戲演員翟化信和黃志生,他們和歌劇演員以及劇場演員同台演出,所使用的動作和音樂是為他們獨特的肢體特技設計的。【表演工作坊】主要演員之一李立群也曾受過正統的中國武術訓練,也有過京戲的業餘基礎,這些訓練使他對於像《暗戀桃花源》(1986)及《回頭是彼岸》(1989)等作品的大段創作有很大的貢獻。
除此之外,傳統中國表演技巧在我們最流行的作品中被使用得最明顯。《那一夜,我們說相聲》(1985)、《這一夜,誰來說相聲?》(1989)以及在程度上小些的《台灣怪譚》(1991),大量引用了中國古老「站立式喜劇」對話藝術「相聲」的技巧。這一系列的第一齣戲是一九八五年透過即興排練而完成創作的,探討台灣失去傳統的現象,而相聲正是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之後諸多死去的傳統中的一個。演員,包括李立群,感到這種即興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它們一方面要建立主題和素材,同時要重現許多正要失傳的傳統相聲技巧。事情被我弄得更複雜,因為我企圖創造的基本上是一個嚴肅的作品,調子是悲的,但卻用的是那最經典的中國喜劇藝術──「相聲」,做用表演主軸。很反諷的,雖然這齣戲談論的是台灣傳統的逝去,尤其是相聲,這齣戲反而使相聲再度成為流行的。這個形式之下的其他實驗也一樣受歡迎,第二齣《這一夜,誰來說相聲?》的觀眾人數是中國大陸以外演出的任何一齣中國語文戲劇最多的。這個系列的每一齣戲也都錄成錄音帶,在台灣已成為白金唱片。我們似乎為相聲創造了一種現代演出方式,一種可以針對政治、社會和文化問題進行討論的型式。
◎你們的表演訓練是怎麼樣的?
在創作作品的過程中,我們並沒有特別指定時間來做所謂的「演員訓練」。訓練本身來自排練室中不斷引用即興表演的過程。如果我跟一群沒有用過這種方式工作過的演員一起工作,我會花時間和他們單獨做一些與進行中的作品分開的即興訓練,但通常我希望讓正在創作的作品變成訓練本身。當戲中需要一些特別表演技巧(好比說相聲或者京戲),我們會請相關的老師來訓練我們,或者我們會透過即興表演的過程讓這些表演技巧有計畫的形成。通常過程會成為這兩種東西的混合。我們工作的另外一部分就是表演者個別針對所創作的戲各種面貌所做的研究工作。這個工作比較屬於知性的,不是肢體的或情緒的,是排練室中進行即興創作的重要基礎工作。
在此附註說明一下我對即興的看法:我認為只有一種方式可以讓演員真實情感透過即興表演有意義的提煉出來,也就是當角色和狀況非常清楚的被定義之後,所有的界線也非常清楚的被劃上之後。於是我們可以花很多天或者很多星期在討論角色,但很少時間花在討論狀況(那是我所指定的),也從來不去討論戲劇動作。
◎ 最近的一些政治事件,好比說前蘇聯的解體、天安門事件、台灣獨立運動,有沒有影響你劇團的美學和劇本的選擇?若有,是如何?
政治事件永遠影響我們工作的方式,也影響我們工作的素材。在許多方面,我覺得任何一個社會中,政治事件通常是人民在個人層面內化的一些議題的一種大量放大的外在呈現。在台灣,所謂「獨立運動」本身外在呈現並沒有怎麼影響我們工作的方式,可是這個運動所代表的內在力量反而有。依我的觀點,這個運動不是想向任何人宣告獨立,而是一種欲向我們自己宣告獨立的掙扎。這種試圖掙脫我們自己的行為也可以說是另外一種讓我們重新定義我們是誰的方式。在台灣,這種過程不斷的在粗獷及含蓄的兩種層次上呈現,不只是在政治上,是在台灣生活的各個層面上。
像六四天安門一類的事件在很深的層面令我們感到不安,對我們影響很大。一九八九年六月,我們正努力創作《這一夜,誰來說相聲?》,一個台灣人和一個大陸人的長對話。六四改變了我們對這個作品的一切思想、情緒和結構。總而言之,我們希望能夠把台灣經驗提煉出來,將中國人經驗整體而言提煉出來,朝向一種對人類宇宙性的處境作一種表達。
───(以上摘自《賴聲川:劇場》自序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