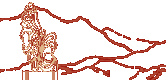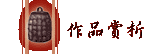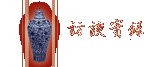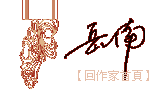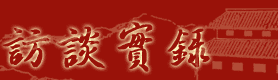時間: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五日∼一九九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地點:明十三凌北新村一家寓所中
人物:作家岳南 v.s 女大學生李振英
李振英(簡稱李):剛剛看過您和楊仕合著的《風雪定陵》一書,非常激動。您是不是談一談《風雪定陵》這本書是怎樣寫成的?
岳南(簡稱岳):大約一九九○年吧,我正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讀書,還是一個學生。
有一次,跟一個朋友來到了十三陵,是一日五遊,先到的十三陵水庫。那時,我就忽然有了一種強烈的創作衝動。這種創作的衝動和慾望是怎樣產生的,到現在我也還不知道。
很快又來到定陵。定陵那磅礡輝煌的古建築藝術,那通過黃瓦紅磚表現出來的超越俗世凡塵、拒現代文明於千里之外的安逸、高貴、肅穆空靈,突然深深地震撼了我。
後來,我就又聽到了關於定陵發掘的種種傳說。這些傳說或許聽來荒唐、怪誕,但它們就像不可抗拒的磁力,深深地吸引了我。而我又酷愛歷史,當我試圖把關於大明萬歷皇帝的生平跟現在坊間這些一鱗半爪的傳說故事結合在一起時,我知道,自己必寫一本關於定陵的書了。
從十三陵回來以後,我一連幾天都陷入了一種創作前的激動,久久不能平靜。經過多方聯繫,從北京大學的閻艾懦教授那兒,我知道了主持挖掘定陵的是他的學生趙其昌,根據閻教授提供的地址,第二天,我又找到了家住西四北大街二二九號的原定陵考古隊隊長趙其昌先生。趙老一開始對這個問題諱莫如深,後來我才知道他是不願意對這個歷史性的悲劇進行更多的訴說和回憶。事情眼看無望,我一籌莫展。但這時,趙先生的夫人楊仕女士說話了。原來,她手裡正搜集著大量的資料;已經有了關於定陵發掘的三萬多文字。我是搞文學的,她是精通考古的,我們商量了一下,覺得這合作完全可行。就這樣定了下來。
事情已經說定、趙先生也就不再堅持,他積極回憶,加上楊仕女士的鼎力配合,就有了《風雪定陵》的寫作。
寫作用了兩年的時間,三易其稿。一九九二年,《風雪定陵》一書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首先推出,當年就被評為「全軍二十大好書」之一,中央電視台還對此進行專門報導。1996年,此書由新世紀出版社予以重版,同年,榮獲「一九九六年台灣《中國時報》十大好書獎」,現在,此書已被譯成日、英、法、德等多種文字,在境外十多個國家同步出版發行。
李:先是《風雪定陵》,後來又有了《復活的軍團》、《萬世法門》、《日暮東陵》、《西漢亡魂》,應該說已經很有些份量了。對您來說,這些書的寫作,是不是都遵循著一種共同的規律?比如說「考古文學」?由此推想您是不是還有著一個更龐大的寫作計劃?
岳:是的,這些寫作是遵循著一種共同的規律。或許是二種感情,一種民族歷史的溫情,一種對創作歷史的激情吧。
李:《風雪定陵》也已被譯成日、英、法等多種文字出版了,作為中國少數幾個「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作家之一,您覺得應該再為中國文學做點什麼?如非要說幾句話,你會對中國作家說什麼呢?
岳:中國的文學並不是不行,早在「五四運動」之前,中國已有很多的文學作品馳世西方。之所以一直沒能獲諾貝爾文學獎,我想這主要是跟語言翻譯有關係。畢竟,漢語這種語言,太複雜了,每一個漢字的背後、都是有著五千年厚重深沉的文化根底為支撐的。中國文學所以不易為西方所接受,跟中國文化千年一貫的延續性和伸展性是分不開的。你看,羅馬、埃及、希臘,這些曾是古老文明發源地的國家,都發生了變化,發生了一種文明和文化的同化。
但是,中國沒有變,中國語言是獨特的,中國文化更是獨特的。簡單舉個例子,就是成語「黔驢技窮」的翻譯問題,這麼簡單的一句話,在英語中怎麼翻?「一頭貴州的驢沒有辦法了」,這讓人如何理解?為什麼貴州的驢沒有辦法了?難道密西西比的驢就有辦法?難道伏爾加河的驢就有辦法……
儘管這是一個比較荒唐的問題,但它反映的卻是個不爭的現實,那就是中國文學要走向世界,確實還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但是,這決不是中國作家的水平不行,中國文學的整體水準不夠,而是另有原因。當然也不是我非要為中國作家辯護些什麼。實事求是地說,非但中國作家,整個中國人,都是這個樣子。
有一個故事,是有記者把兩個蘇聯人和一個女人共同安放在一個荒島上,一月後,記者上島採訪,發現三人正圍坐在篝火旁喝酒跳舞,其樂融融。記者又換了兩個英國人,仍是這一個女人。一月後,記者再去島上,發現只有兩個英國人在一起喝酒,那女人則孤單單一人在很遠的地方。最後又換了兩個中國人,不到一月,記者第三次來島上,發現其中一個中國人已和那女人成了夫妻,而另一個中國人,早已不知哪兒去了。
這就是中國人。
至於要對中國作家說幾句什麼,那是有些誇大了。如果非要說,那就是
──不要再互相扯皮,互相推諉了,同志們,大夥兒還是踏踏實實,為我們國家的振興,為我們古老中華民族的騰飛,做一點兒什麼吧。
───(摘自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四日《中國民航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