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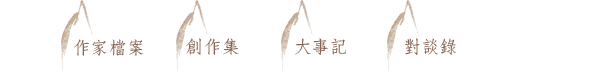 |
|
|
文/陳舜臣 |
||
|
身為一個常以歷史為題材的小說家,在史料調查方面,我建立了一個原則。那就是謹記史料往往是勝利者的記錄。勝利者常會將不利於自己的事實抹除或是重新修改。例如,周朝消滅殷商的理由是: ──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史記》 可是,二十世紀的現在,殷墟被發掘出來了,甲骨文大量出土。根據這些紂王經常祭祀的事實,一一呈現在我們的眼前。司馬遷寫《史記》時,根據的史料,很明顯的就是曾被修改成有利於周朝的記錄。因此被書寫下來的記錄是不能照單全收的。 此外,我認為推動歷史的,往往是擁有挫折經驗的團體。例如,殷商雖然被周朝殲滅,春秋戰國的大思想家,如孔子、莊子、墨子等,卻都是殷人的後裔。紀元前三二九年,亞歷山大大帝占領了粟特族的據點──撒馬爾罕。當時四散的粟特人,卻是對東西貿易有極大貢獻的商業民族。現在,我在《讀賣新聞》連載的〈紙路〉就是以這個為其中一個主題。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遭受了漫長又嚴苛的挫折。回顧台灣所遭受的挫折更是令人無法不掉淚。因此,我相信下一個世紀,一定是我們對這個世界有大貢獻的時代。這是我的「樂觀史觀」。 |
||
【回作家首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