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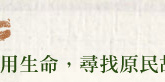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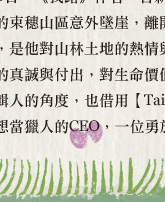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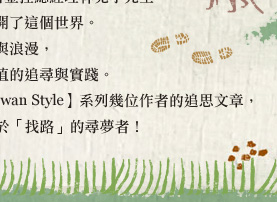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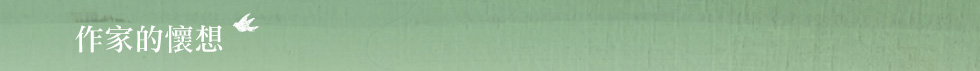
詩一般美麗的十七歲──再懷克孝
文╱劉克襄(作家,《11元的鐵道旅行》《十五顆小行星》作者)
十七歲時,你有無在野外旅行,體驗過出生入死的探險?
「人的求生慾,在此時發揮無遺。雖然大家已將近休克狀態,仍然沒人停下腳步,而機械化的移動著,一心要將
這條命保存出山。漸漸地,大家起了幻覺,不時將大石頭看成房屋,樹枝倒木當作獵寮,空歡喜幾場,失望幾乎
變成絕望。」
這是三十多年前,一位十七歲少年撰寫發表於(野外)雜誌,「斯馬庫斯古道歷險」(1977)一文的摘錄。
尚不及弱冠的高中生,便有如此驚心動魄的冒險敘述和文筆,這人是誰呢?他就是最近甫在南澳山區辭世的林克孝。
那年高一寒假,天寒地凍的元月,克孝跟成功高中登山社的六位同學相約,仗恃著年輕的旺盛體力,決心橫越斯馬庫斯古道。這條路探查的山友並不多,攀爬過的,多半也是經驗豐富的老手。他們年紀輕輕,竟敢深入陌生的山區,委實讓人捏把冷汗。綜觀台灣山岳的攀爬,遑論現今的年輕人,就算同一時代的高中生,有此勇氣者幾稀。
當時古道探查還未流行,我後來一直忘了探問,資訊不發達下,他們到底何來見識,又從哪裡獲得斯馬庫斯古道的資料。還有當時,每個同學又要如何說服自己的家人,才能果斷地結伴前往。
九月六日出殯之日,克孝的父親,袖珍博物館創辦人林文仁,在追悼儀式裡感傷地回憶,克孝在國小一年級時,全班到圓山動物園遠足。他因喜愛繪畫,看著動物忘情地寫生,後來落單了。糊塗的老師未清點人數,便帶隊返校。他竟一個人,沿著昔時猶是大排水溝的新生北路,走回長春路的家,從小即發揮了找路的本領。後來,林父也常帶他到台北郊野爬山,還曾在七星山迷路。
父親熱愛山林,常會影響孩子的性向,甚至決定他一生的生活價值。但一般孩子到了青少年時代,常因課業繁重,逐漸與野外疏離。克孝相當特別,仍繼續熱愛山野活動。國一時不僅參加溪阿縱走,日後就讀成功高中,還籌組登山社團。高一時橫越聖稜線,高二時更有了斯馬庫斯古道的踏查壯志。這些事蹟,都讓人看到克孝對山的癡愛,充滿與生俱來的自然原力。自然教學多年,在現今七八年級的孩子裡,我也只見過一位擁有這等天賦。
其實這條古道並不難爬,但那一年他和六名同學遇到了惡劣天候,因而有了較為艱困的旅次。我為何會特別提起這段往事,因為克孝日後談及為何長年來去南澳山區,常會溯及這段少年時期獲救的往事。更因為,1991年寒冬,我和焦桐、陳列、馮建三等友人前往時,走過同樣的古道。同樣遇到惡劣天候,也有著相似遇險的境遇。
最巧合的是,那回橫越前,我浪漫地編了一本這條古道探查的小冊,裡面不僅收錄早年的古道地圖,還有許多相關的攀爬記錄。其中第一篇便是克孝撰寫的遇險文章。
當大家坐在古道最高點的雪白山山稜,筋疲力竭地休憩,還有找不到水源和路徑,因而坐困山谷時,我都氣定神閒地拿出小冊,一邊看著文章對照地圖。此時還被大夥嘲笑,已經大難關頭,還在紙上談兵。
那次我們的隊伍經過斷崖時,有人深陷崖谷險遭不測,有人被大量落石滾滾追擊。因為一路倉皇過關,回去後,對這篇遇險的文章更懷有奇妙的共鳴,一直保存在檔案夾裡。後來寫了「斯馬庫斯探勘」,發表後,隨即收到了克孝的來信,提出我在記錄上的可能錯誤。那是初次接觸克孝,也才赫然發現,自己驚奇拜讀的文章,竟是他十七歲時的行山經驗。
1979年暑假,建中高二學生,已然有文藝青年特質的楊照,花了大約十天的時間,在梨山和武陵農場間徒步往返。年過半百後,楊照回憶,「孤獨、走路、深山,一條不可能不應該存在的路,這些都是我少年時認定跟詩有關,最浪漫的元素。」
年代相近,十七歲時林克孝的古道橫越,也是另一種形式的詩之旅。他選擇以探險,尋找那條可能應該存在的路。以面對險境和絕望,淋漓地表現自己年少的狂狷。整個古道的橫越,就是一首探險的詩。
克孝和六位同學是如何走過的呢?接下來,我要從這篇四千字的短文擇錄幾段。從這些記述,讀者或可從他年少時攀爬山林的心境,更加了然他日後屢屢前往南澳探險的精神吧!
雖說年輕氣盛,此回行前的登山準備,卻已做足功夫,因而文章一開頭,便毫不拖泥帶水的切入,十足展現克孝不僅是位早慧的岳人,更擁有成熟的綜觀視野和文采:
斯馬庫斯古道,是隨著雪白山發跡而引人注意的路線,然而一般登山隊登雪白山後便原路退出,真正走完古道全
程的不多。我們持一份九小時完成的資料和一份五萬分一等高線圖,在風雨中掙扎了十八個小時,才能僥倖完
成。我們不否定前人資料之準備,只是覺得太幸運了。
我為何未會對此文情有獨鐘,除了起頭展現不凡的登山激情、遭遇相同危險的情境。一開始走進去後目睹的蓊鬱森林,也一如他所敘述的森冷、溼漉。當年我雖已有數本文學著作,但都不見得有此書寫山岳的精確文筆:
高度正值森林茂密處,所以仰不見蒼穹;又因溼陰,菁苔至少五公分厚,空氣凝重得很難受,所經之處均是支稜
尾根,坡陡而彎來彎去,方向不易把握……
我們經過時棧道和獨木橋大部份都朽斷,天雨路滑,走來有點驚險。同時倒木往往截斷路面,有的樹徑一公尺以
上,既不好跨,又不好鑽,加上山崩、谿水將路基流失,形成重重阻礙。……
誠如克孝所言,走進這條古道,馬上被北台灣中級山的潮溼陰鬱所籠罩。松蘿苔蘚密佈,一條條彷彿精靈披覆著樹毯,檢視著你的到來。電影《魔戒》裡那些幽黯森林的畫面,恐怕都不及此。
從未想到,我們的境遇竟是如此接近。都努力地找路,都在半途遇到大雨,卻也都迷失了。那一年在寒夜的大雨中,我們就著一塊斜坡,勉強撐起營帳過夜,裹著雨水溼透的睡袋,強撐著到天明。他們的運氣更差,半夜中,找不到可能平坦露宿的地點。在這段不知位置和前方的摸索過程裡,克孝生動地描述了七個高中生的惶恐:
……藉一點點光線找路,大家已是全身溼透,心力俱疲,一坐下休息便冷得受不了,有的已是半睡眠狀況,只有
叫大家互相注意不能昏睡過去,硬撐著摸黑。
……走到九點多還在深山中。幾乎每人都有輕微抽筋現象,有人體力已呈不支,面色蒼白,只靠一股毅力在走。
有人主張先找個營地挨一夜,明天原路撤回。問題在連可以挨的地方都沒有。
幾乎每個人都有墜崖記錄,幸好草樹茂盛,最多滾個五六公尺,東西掉了只有眼睜睜地看著它滑落,心裡想只要
保住命能回去就好了。
到了午夜,他們實在過於疲累,不得不取出哨子猛吹,尋找可能的援助,卻無任何回音。絕望下,勉強找到一處約三十度的平緩空地紮營,就著溼透的衣服和睡袋過夜。隔天醒來,才驚喜地遇見上山打獵的泰雅族獵人。獵人引領他們,安然抵達了台灣最原始的部落斯馬庫斯。幾個大男生在這兒受到熱情款待,滿懷獲救的感激。
或許是中級山林相錯綜的森林,或許是泰雅族人深山部落的經驗,在這次的山行後,少年林克孝對北台灣的隱密山區,終而有了生命裡最重要的印記。盡管日後還有攀岩、海外山健行的經驗,甚而激起攀登珠穆朗瑪峰的壯志,但最終,他還是回到北台灣,在陰森的二千公尺中級山,在枝椏密覆的草莽中,持著山刀,翻尋著自己的古道,完成自己的長征。
古道那端,沙韻或許是路的盡頭,但開頭應該是這裡。這樣發亮的,永恆的,詩一般美麗的十七歲。
2011.9.20
── 同步發表於2011.9.20《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
歷史山林的找路人
文╱張小虹(台大外文系教授,文化評論家,《找路》作序者)
傳統對歷史學者的刻板印象,總是孤燈斗室,案牘勞形,但會不會也有另一種歷史學者在博覽群書之後,背起竹簍,穿上登山鞋,在莽莽山林中掄起山刀,砍出一條時間的古道。
金融家林克孝先生墜崖辭世,震驚整個台灣社會,這份震驚不僅來自他多重交錯的身分讓人驚呼不可思議,詩人CEO,獵人經濟學家,泰雅化的平地漢人,更來自他親切良善的性格與浪漫人文的情懷,集台灣人最美好的品質於一身,讓所有相識與不相識的人都為之不捨。
但在我們哀悼傷痛之餘,更該認真去問一個問題,克孝先生不在台北金融圈運籌帷幄,休假之餘跑到人煙罕至的宜蘭南澳束穗深山做什麼?他不是在登山休閒,不是在尋幽訪勝,他是在找路,用身體在崇山峻嶺間找台灣史,那淹沒在荒煙蔓草中的古道,三百年前泰雅祖先的遷徙路徑。
而這次他跌落在歷史山林的深淵,沒再回來,就如同他一生崇拜景仰的日本博物學家鹿野忠雄,詳繪台灣高山的動植物地質山形後,消失在硝煙瀰漫的南洋戰場,沒再回來。他們都是台灣山林的吟遊詩人,對他們而言,山林不是歷史的隱喻,山林就是歷史的現場。他們必須以滿腔的熱情與勇氣走入山林,用渺小脆弱的血肉之軀,胼手胝足一步一腳印,攀爬在山壁間懸空的秘徑,找出被大自然無情吞噬的歷史。而他們從不張狂,一如克孝先生在《找路》一書中所言,「我的活動不過是螻蟻在一片山水的幾度爬梭而已」。
克孝先生作為一位台灣原始山林的歷史考掘者,始終有著發自內心深處的巨大謙卑。面對山的不可測、大自然的無情,他早已了然於胸,鬼門關前來回,還是要繼續找路。他佩服讚嘆泰雅獵人的山林神技與原始本能,他滿心歡喜願認真學做一個沒有泰雅血統的泰雅人。
在族群融合口號喊得震天價響的台灣,在社會公益上山下海愛土地的當下,誰能像他這樣真心誠意、心悅誠服地「回歸」原住民文化,並且深信原住民的歷史就是台灣的榮耀,原住民本非弱勢,原住民是山林的王者。但同時他亦憂心忡忡,看著耆老凋零、老部落加速廢墟化,他想要趕在森林安葬一切、遺跡灰飛湮滅前的那一刻,找出有如魔幻寫實般的歷史現場。於是他下定決心,加入古往今來找路人的探險行列,在深山部落前仆後繼,因為他深信「這些人的勇氣與好奇心,最後如同絲路沙漠邊的人骨,一起撐起人類文化的光輝」。
所以他的離去,不是一語成讖的山難,不是預知死亡紀事的傳奇,而是早已懂得「命運本身就是不須解釋為什麼,這個事件就是命運最極端的呈現」。他曾在書中用這句話來回答世人的無限惋惜,為何泰雅少女沙韻就在目的地已然在前的剎那失足落水,而此刻是否也可借用這句話來回答我們的無盡思念,為何克孝先生會忍心留下高堂愛妻稚子,在他最心愛的南澳山區化身為追風捕星的泰雅獵魂。
山林無語,歷史最靠近生命哲學的地方是詩。
2011.9.6
── 引自2011.09.06《聯合報》
![]()
林克孝的找路
文╱劉克襄(作家,《11元的鐵道旅行》《十五顆小行星》作者)
林克孝的不幸意外,無法簡單地只視為一位名人的不測。更難以只是一個喜愛登山的金融高階主管,因為不慎失足,罹難山區。
有三個重要的意義,隨著他的離去,或許值得大家省思。一,在高度競爭激烈的金融界裡,很少有這樣單純質樸的人物。二、弱勢的南澳泰雅族,失去了重要的外界依靠。三,他充分地展現了一個探險人物,追尋生命價值的意義。
台灣工商企業和財團投身公益的並不少,對偏遠弱勢族群的照顧,也常持續不斷。但多半是物質的注入,較少投入自己的休閒生活。他是一個特例,不僅將個己的精力全部放進去,甚至帶著妻小,在例假日時,融進這個被登山界稱為失落一角的地方,學習跟當地人一起生活。
他對南澳的熱愛和回饋,雖起因於一首登山人耳熟能詳的「莎韻之歌」,但遠因來自於廿多年前,在司馬庫斯遇險,被老獵人獲救後,懷著感恩圖報的心,想要幫助這個像異域的家園。經過長期的來去南澳山區,看到當地生活的寥落,他一直思考著,採用什麼樣的方法,讓南澳地區的年輕人能夠獲得更好的謀生機會。
後來他為何會不斷地投身,在這區域的古道探查。不因單純是個人尋找探險的刺激,還有更多是想透過對這個區域的徹底了解,挹注更多外來的援助,重新建立這個族群的傳統文化。一個外來者的他,跟此地泰雅族的友誼情同兄弟或父子,這是何等不易。在城市,我們的族群關係,一直缺乏這類生命的質地,在彼此間互動、信賴著。
現今社會鼓勵年輕人壯遊,尤其是野外探險。他的離去,可能讓不少家長充滿疑慮和不安,反對年輕一代進行類似的生命探索。乍聞其大去時,喜愛古道踏查的我亦充滿挫敗。但這幾日不斷地再翻讀《找路》,我逐漸獲得安定的力量。多年的行山經驗,對生命的死生,他其實很豁達,很了然。
新聞報導,說他的離去是一語成讖。我不以為如此,那是一個人長年行山後,對山巒懷著謙卑之心,才會表述的心境。一個平時穿著西裝體面,掌握台灣重要財經脈動的重要人物,換上素樸的勞動衣物,綁頭巾肩大背包,在荒野裡大汗淋漓,卻露出滿足地微笑。那意味著,物質的力量再如何豐腴,都不如一次登山的簡單和美好。
透過自然洗淨城市的職場忙碌,那是最大的幸福。面對野外的危險,坦然接受自然給予的安排,更是最動容的生命抉擇。《找路》不只是在原始蓊鬱的森林找路,而是在一個最衰敗貧窮的山區,想要尋找一個主流社會的更好出口。
除了他摯愛的家人,相信當地泰雅族人是最哀痛的。他們失去了最鍾愛的漢人朋友。不,是失去了他們至親的族人。林克孝給了我們異地內化的美好啟發。族群要如何和諧,唯有透過利人忘我的互動。多年來他的不斷南澳山行,早已綽綽顯示,他已內化為這裡的泰雅族,如今更成為勇士,回到祖靈安息的家園。
這絕不是一個登山探險的執著事蹟,或者是夢想的追尋而已。在這個族群文化衝突不時引發的時代,他嘗試走出一個認同弱勢異己的生活價值。他身處主流社會,卻以異於主流的風格,留下一個不同於大家離開人世時的背影。
台灣應該有更多這樣的背影。
2011.8.17
── 引自【人間,一顆星球】blog
![]()
懷念克孝——勇於活出Taiwan Style的夢想實踐家
文╱范欽慧(教育電台「自然筆記」製作主持人、作家、影像工作者,《跟著節氣去旅行》作者)
上週四的夜晚,鮮少看電視的我,突然想看新聞,也因此意外得知克孝墜崖,直升機搜救無功而返的事情。我走向窗邊,看見那一輪高掛的明月,正散發著溫柔的月光,我相信,在南澳的克孝,心情應該也是溫柔的。
故事,由月光開始,難道,也在月光中結束?
週五清晨六點,我搭火車到玉里。行經南澳時,我凝望著那層層山巒,雖然心繫此事,卻無法得知最新狀況。接下來的三天,我陪著孩子在山林海岸穿梭,跟外界資訊隔絕。週一上午,訪問孟琬瑜時,由她口中得知克孝的狀況,當場兩位女子淚眼婆娑。一個是從來沒有看過克孝,只拜讀過他的著作的讀者,一位是曾經專訪過他一次的的電台主持人。
我們難過,因為我們深知那份愛山的心情,我們懂得那份來自山林、來自內心的深沈召喚。
我跟克孝的書,都是由遠流出版,也都是Taiwan Style書系的作者。他的"找路"是第六本,我的"跟著節氣去旅行"是第七本。我們的編輯是同樣一群人,當初副總編輯靜宜把克孝的書拿給我,希望我為克孝做專訪。幾天後,克孝來到我的錄音室,他剛結束一個會議,西裝筆挺的正式外表,讓人感覺有些嚴肅。不過很快的,我們談到了山,我才看到了屬於田野記錄者的探險靈魂。
昨天,我把去年三月專訪克孝的這段錄音找出來,並且重新剪輯,成為紀念克孝的專輯,希望能獻給所有關心克孝的朋友,以及所有熱愛這片土地的人。
我細細地聆聽,重新回味他所走過的路徑、當初遇上南澳的心靈悸動、對於傳統獵人身影的崇拜與嚮往、追溯在歷史人文光影間的浪漫情懷......正如克孝所說的,如果沙韻的故事,是一段傳奇,那克孝的行旅無疑是創造另一段更令人撼動的傳奇。
克孝說,他不畏懼大自然,其實是這幾年的事。他與原住民朋友有無數在黑暗森林中行走的經驗,他再也不怕孤獨置身在黑夜森林中。他真正覺得,來到大自然中,有讓他回家的感覺,他甚至說:" 如果真的遇到了什麼事,也不就是重新來過一次。想想我們過去的老祖先,當初看上這片山林,也不就是如此存活下去。"我問克孝說,是不是覺得反正就是能量循環的一部份呢?克孝笑著說:"是啊!我真的覺得自己更自在了。"
如今,我相信更多的人,會因為克孝"找路"的身影,而認真的走上屬於自己的"找路"之旅。我透過克孝的專訪與著作,讓我看到的是人生幸福又美麗的風景。
克孝,真的活出了Taiwan Style。
2011.8.16
── 引自【立地台灣(NATIVE)】blog
![]()
找路!選擇你願意捐軀的山頭
文╱洪震宇(作家、企業與媒體創意顧問,《旅人的食材曆》作者)
我相信林克孝一定同意這句話:「選擇你願意捐軀的山頭」,我也相信許多含著淚水、不管認識或不認識林克孝的朋友,也能感受這句話的深意。
當初在閱讀林克孝的《找路》時,依稀記得他講了一句話:「找路,是為了迷路」 ,他不只將山林文字化,更將文字山林化,甚至讓自己獻給山林,成為山的一部份,永遠受泰雅祖靈的照拂。
我只見過林克孝一次,是多年前負責策劃與編寫《天下雜誌一千大企業特刊》,採訪當時是台証證券總經理的他談總體經濟分析,非常溫文儒雅,也從女記者口中知道他似乎未婚,隱約藏著一個讓人心疼的愛情故事。
後來策劃319鄉專刊時,他代表贊助的台新銀行,也接受天下的隨身採訪,談他對南澳與莎韻之鐘,後來參加詹宏志新書發表會,林克孝匆匆現身,現場跑藝文的記者大概不知道他是誰,經過詹宏志說明後,才知道他們是台大經濟系的同學,也是詩社的同好。
直到去年初拿到遠流編輯送我的新書《找路》(我有幸和他同一個編輯),很意外林克孝是非常有魅力的說故事的人。如果大家看了這本書,會很清楚他的想法絕非浪漫,而是想找到一個出路,還原因為事故產生的人為故事,還原一個泰雅少女落水的單純故事。
還原之路,不是找路,而是更深更深的迷路,山林的故事、泰雅的故事,讓這個南島語系居住最北的民族重新站起來,重新被珍惜。
甚至在當時金融海嘯、險惡的世界經濟局勢中,林克孝發現,山林的迷路,不只是心靈寄託,甚至是放大視野與心胸,人生波浪,僅是滄海一粟。
他寫著:「人的一生無法完成所有的夢想,甚至無法完成任何的夢想。」
他謙虛了,我想他要傳達的是,只要出發,佈滿傷痕的回憶,也是一種夢想。
縱然一個不小心,抓住枯籐,墜落山谷,連夢想也抓不住。
他或許失敗了,我相信那個墜落瞬間,回憶如電光石火般湧現,故事長伴,甚至永不消失。
馬奎斯在自傳《Living to Tell the Tale》(訴說人生)開宗明義說;「生命不是一個人活過的歲月,而是他所記得、以什麼方式記得而訴說出來的人生。」
我們的人生不是用數字或業績、成就被墊高,而是被經歷、回憶寫下的故事所創造。我們要記得什麼?希望被人記住什麼?
打動人心、打動自己的那條路,就是自己的戰場,自己選擇願意捐軀的山頭。
那座山頭有自己的熱血、夢想與故事。魏德聖在《導演.巴萊》這本書說:「戰士應該在戰場上流血,獵人應該在獵場裡追捕。」
我在Facebook塗鴉牆寫著,你的戰場在哪裡?你現在站的地方是戰場還是牧場?也許換句話說,找戰場壓力大,但是知道為何而戰、為誰而戰,你站的位置 就是戰場,不知道為什麼要每天忙碌?做的事情沒有找到意義,沒有看到一個未來的整體觀,自己要在這個局面扮演什麼角色,可能就要思考戰場在哪裡?否則就是低頭啃枯草的綿羊,沒看到可以奔馳的大草原!
有朋友誤解戰場就是壓力與濺血,為何不能選擇快樂的牧場?我想說的是,自己清楚定位,要去找哪條路,或者,就是上路吧,面對荒蕪而繼續前行,站的位置就是戰場,就是自己的舞台。
朝那座願意犧牲、甚至捐軀的山頭前進。也許找不到出路,也許踏出另一條路,也許真的失足、失敗。
也許……太多的也許,仍阻擋不了出發的動機。
如果,真的感受到一種召喚,在所不惜的召喚,來自內心鼓盪的聲音。
村上春樹在《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藉著青蛙老弟說:「我們每個人都是有限的存在,終究要敗下陣去。但就像海明威看破了那樣,我們的人生不是看勝利方法,而是看失敗方法來判定最終價值。」
驕傲的失敗,就是謙虛的成功。失敗者一無所有,但成功者真的擁有一切嗎?
我們能擁有的,不是有形的功成名就,而是故事。像《挪威森林》講的,「死不是生的對立,而是生的一部份」。
瓦歷斯.諾幹在《找路》的推薦序結尾,寫著:「故事讓我們有所依歸,故事讓我們逐漸堅強」,這就是故事動人、讓人傷心、喜悅的祕密。
也是林克孝留下來最寶貴的出路。他只是先走,先通過彩虹橋(泰雅族死後的勇士與女性,會經過彩虹橋與祖靈相聚),成為山。
讓我們為自己找路,為台灣找路。
2011.8.14
── 引自【虛構的抒情筆記】blo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