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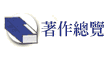 |
|
| 。•。•。•。•。•。•。•。•。•。•。•。•。 。•。•。•。•。•。•。•。•。•。•。•。•。 |
|||||||
| 陳捷先,江蘇江都人,一九三二年生,一九五六年畢業於台灣大學歷史系,一九五九年獲台大歷史研究所碩士,後應邀赴美加入哈佛大學訪問學人計劃研究,返台後曾任台大歷史系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等職。
一九八○年應聘為美國麻州大學客座教授,一九九○年榮獲韓國圓光大學名譽博士學位。一九九五年退休,移居加拿大,現任台灣大學名譽教授,中國南開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專攻清代史、滿族研究、方志學、族譜學,著有《滿洲叢考》、《清史雜筆》(一至八輯)、《清代台灣方志研究》、《東亞古方志探論》、《雍正寫真》、《康熙寫真》、《乾隆寫真》、《不剃頭與兩國論》、Manchu Archival Materials、The Manchu Palace Memorials及中英論文百餘篇。
他是一九五六年臺大歷史系畢業,我比他早兩年。雖然都繼續讀研究所,但同堂修課的記憶,只有廣祿老師的滿文課。廣老師身為錫伯族滿人,在執行立法委員職務之外,傳播母語,幫助青年學子研究滿文;班上學生,還有在圖書館工作的李學智及王民信。不過我一年後研究所畢業,滿文課也隨之畢業,而捷先他們都能利用滿文這一語文工具作研究。 第一年我住Maganolia街,捷先住Cambridge街1673號,第二年我也搬去。1673號是棟二層樓,加上地下室,除了一樓部分房間主人自住外,均出租。二樓有廚房,公用,房客自炊,主人不管,這是大家最高興的事。此外它距哈佛校園近,租金便宜一點。我從房東訂房記事本上發現,費孝通、劉崇鋐、楊紹震諸先生都在那裡住過。在外國是寂寞的,人不是機器,不能一天到晚看書, 所以中文武俠小說在教授間轉來轉去。同樣我們也玩玩橋牌,尤其是寒暑假南來北往的朋友來時。大概是第二個冬天,玩的次數多了點,我便將橋牌從窗戶丟出去。後來又看到那副橋牌,捷先老說是我去撿回來的。捷先,再說一遍,是發老(金發根)撿的,他還說「好好一副牌丟了多可惜,說不定過些時又用了!」 在哈佛讀書的朋友如張春樹、謝文孫、蕭啟慶等都做東請吃飯,而以在郝延平同學家那一次最熱鬧。他們一九五六年班在捷先的呼倡下打通關,向其他各班全體在場者挑戰。應該是喝地差不多了,他還在叫:「沒關係,你們都來!」我的酒量和捷先是不能比的,但聽到他的話,真不服氣,和他喝了幾杯。他睡了!從此他就說我好乘人之危。大概喝的真不少,連延平家藏的gin都喝完了。 曾經共享過微妙的喜悅。中共試爆核子彈時,Markmank先生提著個電晶體收音機走近我說:「恭喜,恭喜,你們有原子彈了!」中共當然不是中華民國,但即是研究當代中國問題的人也將我們當作一家人而恭喜。捷先也收到同樣的道賀。能說什麼?!只是心中有點不可表達的喜悅。同班同學謝培智說,蘇聯的Sputnik衛星上天時,寓美白俄將官倒了兩杯伏特加(Vodka)酒對夫人說:「來,為我們的衛星乾杯!」夫人說:「那是共產黨的!」將軍說:「不,是俄國人的!」不乾杯也知道那是中國人的。 就在那年暑期我們到Niagara Falls去玩,謝培智開車。他是賓州大學歷史學博士,時在緬因州Louistown的一個學院教書,暑期到哈佛作研究。同行者還有中研院史語所的管東貴、香港友聯社的趙永清。一路上將會唱的歌大概唱完了,喉嚨也啞了。夜宿Curacuse,在那裡讀新聞的臺大同班同學閻沁恆招待晚餐。現在Niagara Falls的瀑布聲依舊,而人事已非;培智數年前返臺省親遭車禍身亡,永清美國一別未再見,而捷先移居加拿大,我與東貴雖同寓臺北,然亦少有訪聚。都是古稀人了! 和捷先同在哈佛兩年,不知談過幾多理想,其中只研究東北亞一項算是落實了。自美國回臺後,我從研究中美關係轉到了中韓關係,在臺大開過這門課。捷先在臺南成功大學任歷史系主任時出版東北亞譯叢,兩個人並共同將留韓十四年,取得成均館大學博士學位的蔡茂松架到成大任教,使南臺灣有研究韓國的一個據點。此外我們與陳祝三、胡春惠、已故的繆全吉、傅宗懋等創辦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出版「韓國研究」,開國際學術會議。我作了第一、二屆理事長四年,捷先作第三、四屆四年。他活動力強,交際人緣廣,所以在他任職四年中,學會蓬勃發展。 捷先兄有兩項特長,第一是你總摸不透他的深謀遠慮,所以我常想他做參謀總長最適合。第二是他雖能喝酒,但未見誤事。開國際學術會議有時要以酒會友,尤其要應付那些日、韓好友;無論他怎麼喝,他總能寫出篇文章來,而且其中總有點東西。這真是項超高本領。 前年與內子去溫哥華,寄跡發老府上,承捷先兄接去他在西溫的高級宅第作客。庭園雅整奼紫嫣紅。夫人侯大嫂作畫,而臺北期刊、日報上不時見到捷先史文。這真是神仙生活。不過,捷先,你有不只一兩個凡人朋友,要勤下山來看望看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