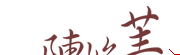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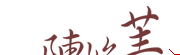 |
|
本文是實學社主編黃驗透過電子信函的方式,對陳峻菁所作的一段專訪。
問:請妳先向〈博識網〉的讀者們作一簡單的自我介紹,也談談妳的生活狀況。 我目前在一個電力公司從事企管工作,工作之餘讀書寫作。 我很佩服美籍俄裔女作家、《阿特拉斯聳肩》的作者艾恩·蘭達,她可以在打字機前一坐就是三十幾個小時。而我不是,寫作就像我每天的功課,幾乎每天都有一些思想和故事會產生,在寫完了它們之後,這一天才會正式結束。我無法在一天裏寫得更多,也無法停下自己的筆,從十四歲寫第一篇小說開始,寫作已經成了一種生活習慣,成了我一生最大的追求之一。
我是南京「東南大學」動力工程系畢業的,很奇特,這個系出了不少作家,如去年在「戛納電影節」獲得【評審團特別獎】的電影《海鮮》的導演朱文,就是我同校同系的師兄,比我早四年畢業;他的同班同學,作家吳晨駿,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他們在校時蹺課,狂熱地寫詩,畢業後都分發到很不錯的單位,數年後卻都辭了職,投入專業寫作。有人總結說,這是由於動力工程系是最枯燥的專業。 我在學校時並不知道前面已經有過榜樣了,我以為自己是唯一的叛逆,但我很懷疑自己能在背道而馳的路上走多遠。 直到有一天,我得知偉大的指揮家卡拉揚,是維也納機械學院畢業的,這給了我很大的自信。雖然在學校我也蹺課,也在力學課上寫詩,很少去理工科閱覽室,整天泡在社科閱覽室。同學們都在繪製鍋爐汽機圖的時候,我凝視窗外,默頌一大段莎士比亞,每天深夜讀小說和社會科學名著至凌晨一時,但我沒有勇氣像朱文、吳晨駿一樣辭職寫作,也許不是沒有勇氣,而是太多的顧慮,古人說「多慮害勇」,這就是了。 那時我的詩已經寫得不錯,93年畢業以後我就開始寫小說,寫了很多。那時還沒有電腦,在筆記本上寫,寫過的筆記本裝滿了整整一個密碼箱。有人讀了我的小說覺得很有趣味,於是我寄了一篇去應徵〈聯合報小說獎〉,沒想到竟獲獎了。 關於這一點我還想多說兩句,中國的業餘作家(是作家而非撰稿人),南京占了相當大一部分,他們熱愛寫作,人數至少幾百個,他們放棄了正當工作,大多靠父母或配偶來養活,每年的稿費只有五、六千元人民幣(這還是非常努力寫作的),吳晨駿就算得上其中一個,他的境況遠沒有朱文好,到現在沒有自己的房子。因為他們過分耽於閱讀,夢想寫出震驚世界文壇的作品。他們之中,大部分沒有過高的才能,卻有著豐富的熱情,令我敬佩。 在大學時,我很少讀中國書,基本上是看十九、二十世紀的西方名著,小說、傳記、哲學、歷史、社會科學類的書;中國書幾乎不看,連魯迅也很少看。我中學時曾手抄過唐宋八大家的大部分作品和詩詞。大學畢業回安徽工作,過了兩年,我漸漸很少看西方書籍了,不知道這種文化偏向與地域有沒有關係。寫歷史小說的名家都不住在都市,像內地的二月河、唐浩明,都是較偏遠城市的。也許大都市令我們體驗到更多西方文明的思想魅力,而小城市則能讓我們更深沉寧靜地潛入、體察古老的中國文化。 95年時,我開始試著寫中短篇的歷史小說,不知道寫得好不好,反正總有人願意讀,小說取材遍及各個朝代,戰國、三國、晉代、宋代、明代都有,我換用各種手法來寫,在寫作中有很多特別的體驗,比如拿著詳細地圖查找古代一場著名戰役的路線,這就好像在網路上進行遊戲攻關,有一種發掘的樂趣。
我在96年來臺灣,曾在接受《聯合報》記者採訪時說,自己下一步想寫歷史小說。因為這次採訪,我和當時〈實學社〉董事長周浩正先生有了見面機會,他帶來幾部剛出版的歷史小說,作了一次很有意義的談話,對我此後的寫作十分有益。談話前我已經打算進行《桓溫》的寫作,但由於我從未寫過長篇小說,所以我花了一年時間,閱讀了上百本有關魏晉時代的專著,通讀了《晉書》,98年才將書稿完成,當年獲得實學社舉辦的第二屆羅貫中歷史小說優等獎,這對我是個很大的鼓勵,也是我從事歷史小說創作的契機。
在98年以前,我的寫作喜歡使用男性化語言,大量使用古文,有人說,如果僅看我的文字,似乎像一個喜歡掉書袋的中老年男性。 其實,我的寫作一直在兩個極端之間搖擺,有時非常纖細,有時又非常雄渾,直到後來我發現,作者並沒有力量決定作品的風格和人物的性格,他們通過在歷史上留下的事跡和語言已經說明了自己。正史是為男人而作的史傳,凡是有作為的男人都已經在二十四史中留過情節生動的傳記,女人則沒有,她們的人生只能當作配料,誰叫她們無法接近政治、無法參與軍事、又大都被教育成不懂得真正的文化?(吟詩作詞只是小技,如班昭、謝道韞、李清照那樣的女知識分子極之罕見。) 但史家刻意的低調卻無法全盤抹殺那些個性鮮明的女性,她們有一種特別的力量,一種罕見的人格魅力,即使沒受過正規教育,也能在一些政事、宮事上產生強大的影響。 此外,她們作為妻子、母親,對自己家中那些了不起的男子發揮了不容小覷的影響。透過史書上簡約的文字,她們令我產生十分肅穆的敬意,同為女性,我甚至為她們自豪,這是我寫作系列女性題材的最初動機。 到現在為止,從事歷史小說寫作的大都是男作家,由於理解力的差別,在他們筆下的女性歷史人物,內心和命運沒有很好地被發掘描寫,她們性格發展的過程也被忽視了,甚至有被物化之嫌,我希望自己能為她們爭取這種被剝奪的語言權。
我很欣賞德國詩人里爾克的一句話:「一句好的詩,背後是十年的沉積和生活。」當然,對於歷史小說而言,要從人物那些簡約散亂的事跡裏抽出故事的本質和發展過程,更需要想像力。我本人是個喜歡閱讀晚報的社會新聞版的俗人,並能從中得到想像和推理的樂趣。作家余華說過,在小說技巧、生活觀察力發展到一定水平後,小報上的一段文字就是一部長篇小說的來源。資訊化時代,偏僻街道發生的一起夫妻打架,都會通過網路傳播到全球,這些讀不完的家庭故事、感情故事,令我感覺人性的真實,更令我產生豐富的聯想和感慨。
從全局看來,現代的愛情婚姻比古人先進得多,最起碼它有了相當的自由和選擇權,對男人女人來說都是如此。但個體來比較,則不是,比如卓文君私奔,她敢於衝破門第和貧富差別,與不名一文的司馬相如同居,甘於貧苦,這一點就是現在也不是人人能夠做到的,好像現代的徵婚啟事裏,收入和學歷都是必填專案。至於說兩性價值觀,21世紀的自由也帶來了不少問題,比如說未婚生子、婚外情越來越多,帶來了很多社會問題。隨著時代發展,新的問題滋生,這是規律。不過總的來說,文明的進步也帶來了社會價值觀和婚姻愛情觀的普遍進步。生在21世紀的人有福了。
在我看來,在歷史小說中,人物和故事必須是真實的,而場面和語言則可以虛構。評論家認為,二月河的歷史小說,從嚴格意義上說,是史料的堆積和考證;唐浩明的歷史小說,則近於演義。我希望能在史實和虛構之間找一個著力點,在不違背史實的原則下,重建歷史現場,復原故事本身的傳奇性,復原人物性格和命運發展,並能寫出其背後的深層原因、動機。 這四部小說中,我個人較喜歡《衛子夫》和《平陽公主》。衛子夫之女陽石公主,和衛子夫的大姊之子公孫敬聲,兩人的戀情實有其事,而諸邑公主與衛青的兒子衛伉,史上卻並未有戀愛的記錄,但諸邑公主、陽石公主、衛伉、公孫敬聲,這四個互為表兄妹的顯貴,連帶在一樁巫盅案裏同時被斬,很顯然,這四個表兄妹關係非常親密,所以,我大膽地做了推測:諸邑公主與衛伉的親密程度過逾常人,且由於她的年齡比衛伉大,所以我在書中虛構了這一起姊弟戀,並作為全書的一個戲劇性因素。
我寫的傳主,都生活在非常古老的朝代:西漢、東漢、東晉。去年寫完了一部南北朝時期的長篇歷史小說《北魏靈太后》,則與那四部書的傳主不同,是個完全掌握權力的獨特女人。目前我正在寫作一部古代人物傳記《突破長城--中國皇后衛子夫》,這部書將由英國文學代理商代理,在英國出版,該書完全拋開了小說方式,是"Non-fiction",每句話和人物、事件都經考證,雖然是不足二十萬字的篇幅,但寫得很辛苦,反覆修改了三、四次,實際寫作量近百萬字,目前已完成了大部分寫作,正在翻譯中。 在這些工作都結束後,今年只打算投入一本書的寫作,即《梁山伯與祝英台》,一般人都認為梁祝是民間傳說,事實上確有其人,是東晉時代浙江人,由於那個時代特別嚴重的門閥觀念,不能結合而產生愛情悲劇。我希望透過他們的故事反映當時的戰亂、剛剛進入中國的佛教、清流人物、南北文化的交融、過度苛刻的門第觀、古怪的時代風氣。希望能通過這部書的禪意和戲劇色彩,給大家帶來閱讀的喜悅。此外,將在今年四月的《皇冠》雜誌上,發表一部長篇小說《沙陀王》,雖然它不是嚴格意義的歷史小說,但小說詳盡地描寫了後唐莊宗李存勗傳奇的一生,有一定的風格。
我熱愛千年以前那古老燦爛的漢唐文化,並且在那些歷史人物身上,看到文化和人格的力量。 重溫那些偉大時代具有強烈個性的歷史人物,走近他們,永遠令人滋生敬意和自豪,永遠令人感覺典範的力量,這種溫習,有助於我們在人生的定位和奮鬥。英國哲學家培根說過:"讀史令人明智。"在歷史小說中,那些動人心魄的智慧和情感並非由作者創造,而是歷史本身提供的,我希望帶給讀者的,只是自己從史書中得來的強烈感動,並希望自己能夠準確地傳達這份感動。 [ TOP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