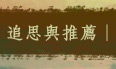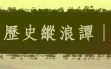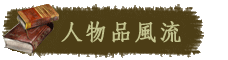
唐德剛對人物的描摹和評論,鮮活靈動,清新脫俗,自成一家之言,足為傳記文學寫作的典範。以下摘錄他所描述的李宗仁、梅蘭芳、胡適、張學良、孫文、毛澤東、顧維鈞等近代歷史人物的精采文字,以及引發老友夏志清教授與之大興筆戰的〈海外讀紅樓〉一文。

桂系靈魂人物李宗仁(右)與白崇禧年輕時合影。 |
▼李宗仁/摘自《李宗仁回憶錄》序
專就李宗仁個人治國用兵的能力來說,他應該說是位不世之「才」。他於青壯年時期,便能雄踞八桂,軍而不閥。全省勵精圖治,舉國有口皆碑。其才足以牧民,其德亦足以服眾。所以他才能穩坐「桂系」第一把交椅數十年而不傾。最後還要做一任「假皇帝」始收場,凡此皆足以表示李氏有不羈之「才」,有可歌之「德」,他的成就,不是一位「普通人」可以倖致的。
抑有進者。論將兵、將將,則李氏的本領亦非他底上級的蔣中正所能及。蔣公熟讀《孫子》,細玩《國策》。馭人每重權謀;將兵時輕喜怒。在疆場之上率數萬之眾,親冒矢石,衝鋒陷陣,於攻惠州、打棉湖等小戰役中,亦不失為一員猛將;然統大軍百十萬,轉戰千里,進攻退守,如在棋局之上,則蔣氏便不逮李、白遠矣。
李宗仁是赤足牧童出身,為人渾厚──有著中國傳統農村中,村夫老農淳樸的美德。為人處世,他不是個反反覆覆、縱橫捭闔、見利忘義的黨棍官僚或市儈小人。等到他時來運轉、風雲際會,享榮華、受富貴之時,得意而未忘形,當官而未流於無賴。遇僚屬不易其寬厚平易之本色;主國政亦不忘相與為善之大體。以此與一般出將入相的官僚相比較,都是難能可貴的。誅心以論之,則李宗仁在中國歷史上,也該算個德勝於才的君子。……〈閱讀全文〉
▼梅蘭芳/摘自《五十年代底塵埃》之〈梅蘭芳傳稿〉
二月十七日晚間,他(蘭芳)在紐約正式上演了。……這時樂聲忽一停,後帘內驀地閃出個東方女子來,她那藍色絲織品的長裙,不是個布口袋,在細微的樂聲裏,她在臺上緩緩地兜了個圈子。臺下好奇的目光開始注視她。
只見她又兜了個圈子到了臺口。那在變幻燈光下飄飄走動的她,忽地隨著樂聲的突變在臺口來一個Pause,接著又是一個反身指。這一個姿勢以後,臺下才像觸了電似的逐漸緊張起來。
也就在這幾秒鐘內,觀眾才把她看個分明。她底臉不是黃的,相反的,她底肌膚細緻的程度,足使臺下那些塗著些三花香粉的臉顯出一個個毛孔來。
她那身腰的美麗、手指的細柔動人都是博物館內很少見到的雕刻。臉蛋兒不必提了,蘭芳的手是當時美國雕刻家一致公認的世界最美麗的女人的手。
這時舞臺上的她,誠然全身只露出小小的兩個部分來。然而這露出的方寸肌膚已如此細膩誘人,那未露出的部分,該又如何逗人遐想呢?
隨著劇情的演進,臺下觀眾也隨之一陣陳緊張下去,緊張得忘記了拍手。他們似乎每人都隨著馬可孛羅到了北京,神魂無主,又似乎在做著「仲夏夜之夢」。
……曲終之後,燈光大亮,為時已是夜深,但是臺下沒有一個人離開座位去「吸口新鮮空氣」的。相反的,他們在這兒賴著不肯走,同時沒命地鼓掌,把這位已經自殺了的貞娥逼出來謝場一次接著一次,來個不停。尤其是那些看報不大留心的美國男士們,他們非要把這位「蜜絲梅」看個端詳不可。
最初蘭芳是穿著貞娥的劇裝,跑向臺前,低身道個「萬福」。後來他已卸了裝,但是在那種熱烈的掌聲裏他還得出來道謝。於是他又穿了長袍馬褂,文雅地走向臺前,含笑鞠躬。這一下,更糟了,因為那些女觀眾,這時才知道他原是個「蜜絲特」。……〈閱讀全文〉

胡適之先生全家福。胡適的「小腳太太」可能是中國傳統「三從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後的一位「福人」。 |
▼胡適/摘自《胡適雜憶》之〈「不要兒子,兒子來了」的政治〉
我問李宗仁先生對胡先生的看法,李說,「適之先生,愛惜羽毛。」這四個字倒是對胡先生很恰當的評語。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愛惜羽毛」的。愛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畏首畏尾的白面書生,則生也不能五鼎食,死也不夠資格受五鼎烹,那還能做什麼大政治家呢?
有一次我告訴胡先生一件趣事:那便是一位反戰的史學家也是前哥大名教授的查理.畢爾在他底名著《羅斯福總統與大戰之序幕》一書中,竟把胡適說成日軍偷襲珍珠港的罪魁禍首。畢爾大意是說美日之戰本來是可以避免的,而羅氏為著維護美國資本家在亞洲的利益,不幸的上了那位頗為幹練的中國大使胡適的圈套,才惹起日軍前來偷襲的。
胡先生聽了這故事大為高興。他連忙要我把這本書借來,並在對他「不虞之譽」的那一段下面,劃了一道道的紅線。但是當我問他當年究竟是耍了些什麼圈套終於使羅斯福總統上鉤的,他想來想去也無法對我的問題做圓滿的交代。其實我們這位「言忠信,行篤敬」的學者大使,哪裏會玩什麼了不起的外交圈套呢?羅斯福何等滑頭!我們胡先生哪有這樣的本領來請他入甕啊!
胡先生是反對「五四運動」的。他認為「新文化運動」的「夭折」,便是「五四運動」把它政治化了的結果。胡氏顯然不瞭解,文化運動和政治運動,本來就是一個銅元的兩面,二者是分不開的。……在他底四十年不衰的盛名之下,政治終於變成胡適的兒子,弄成個「不要兒子,兒子來了」的局面。晚年的胡適之真是「愛其少子,甚於婦人!」他對搞政治的興趣,確是老而彌篤的。
國府行憲之初,胡先生真有可能要做總統了。但他終於做不成。主觀的條件之外,他還缺少搞政治最起碼的客觀條件──與執政黨實力派的歷史淵源。胡先生是聰明的。他自知可以做總統而不能做行政院長。讀歷史的人,讀到胡適婉卻做閣揆這一段,真也要鬆口氣,胡適之如做了行政院長,豈不天下大亂?!……〈閱讀全文〉

1990年12月17日,唐德剛、張學良於張府花園合影。 |
▼張學良/摘自《張學良口述歷史》之〈論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
張學良可能是中華民國史上最有名的公子哥兒了。但是,治民國史者也不能否認他是一位統兵治政的幹材。把個花花公子和政治家、軍事家分開來做,則民國史上實是車載斗量,沒啥稀奇;可是把這三種不同的行業,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體,如魚得水,則學良之外,也就真的別無分店了。少帥張學良之所以成為歷史性的傳奇人物,其難就難在這個三位一體了。
漢卿、漢卿,我國近百年來的鳳子龍孫達官顯貴子弟,生活放蕩的,也是成隊成群了。若論吃喝玩樂的紀錄,真正有錢有勢有貌有才的鄧通潘岳也不難做到,而難的卻是大廈既傾、樹倒猢猻散之後,仍有紅顏知己,舍命相從,坐通牢底,生死不渝——這一點縱是《紅樓夢》裏情魔情聖的賈二公子,也無此福份,而漢卿你卻生受之,豈不難能可貴?我們寫歷史的、看小說的閱人多矣,書本上有幾個真假情郎比得上你?
一荻、一荻,你這個「趙四」之名,也將永垂千古。在人類可貴的性靈生活史上,長留典範,為後世癡男情女,馨香景慕。睹一荻之癡情,羨漢卿之豔福,讀史者便知,若漢卿只是個酒色之徒而非性情中人,他哪能有這個美麗的下場——公子哥兒不難做,但是古今中外的公子哥兒,有幾個不落個醜惡的、難堪的結局。慢說是像張學良這樣的大人物了,讀者閉目試思,在你所親見親聞的酒色之徒中,有幾個不悽然而逝?紅顏知己、學生戰友云乎哉?……〈閱讀全文〉

十七歲自檀香山返國的華僑青年孫
文。 |
▼孫文/摘自《晚清七十年(5)》之〈論孫文思想發展的階段性〉
在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孫中山的偉大,便是他抓住了兩個主題,領導了兩個階段。
今日我們讀歷史的這批後知後覺,來翻翻滿清末年的老帳,覺得孫文這一派所抓到的實在是那個時代的主題。……由民族革命從而建立「民族國家」,實是人類現代文明史上的特殊現象。這一民族國家在十九世紀之末季,由於德意志和義大利之統一,並產生了許多民族英雄的傳奇故事,民族主義竟成為當時的時代精神。白種帝國主義者尚且如此,則被壓迫民族就不用說了。
我國的滿清皇朝到十九世紀末年,實在是氣數已盡,無法再繼續下去;但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不擊中要害,它會無限期地苟延殘喘的。天王洪秀全的錯誤,便是他沒有抓住這個主題,而亂搞其不急之務的「天父天兄」,他那時如只搞單純的「民族革命」,恐怕曾、左、李、胡也早已望風披靡了!
從實力上說,孫中山比起洪秀全來,相差不知幾千萬里了,而偌大的清帝國不亡於洪、楊,卻被孫文的「驅除韃虜,建立民國」幾個口號叫垮了,何哉?主題使然也。孫中山把主題摸對了,幾顆炸彈一丟,滿清帝國就土崩瓦解了。
……自袁世凱死後,中山打了十來年內戰毫無結果,最後終於從頓悟中發現了一個新方法。「以俄為師」這口號是孫中山叫出來的。他抓到「武力統一」這個主題,最後也抓到了如何以武力統一的方法。他找出這法則來,雖無緣及身而見其成,他的繼承者蔣介石卻接了下去做。中國共產黨在「江西蘇維埃政權」時代,毛澤東的「槍桿出政權」的法則,在其著作中也講明「蔣介石是我們的老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蔣介石背叛了他的老師孫文「以俄為師」教訓的結果。

1959年4月二屆人大時,因毛澤東謙恭退出競選,劉少奇以全票當選國家主席。圖為二人步出會場。 |
▼毛澤東/摘自《毛澤東專政始末》之〈毛澤東簡傳要義評述〉
首先我們要問一下,在那遙遠的二十年代裏,為當時的革命浪潮所席捲的千萬個毛頭小青年中,毛澤東何以能脫穎而出。這一點我們就不得不歸功於「五四」(今日的「六四」)那個學潮了。在中國歷史上,所有學潮,都是政治訓練班。毛澤東便是這個訓練班中的學生頭頭。當學生領袖的人,首先都要有點政治性的組織天才。他也要具備若干有初級理論基礎的煽動伎倆。更重要的,他還要具有在青年同學之中當「老大」的權威。前二者多半出自天賦,而後者則是環境薰陶使然。
……筆者不學,讀中國近現代史數十年,遍覽兩黨史籍,我不能不說毛氏比諸其他各有所長的中共早期領袖們,硬是棋高一籌。謹為簡列十條如後:
●毛比家長陳獨秀更為「堅定」。陳教授說理,舌燦蓮華;一挫敗便成為孤家寡人。
●毛比瞿秋白這位詩人、名士、蘇州才子要「紮實」得很多。秋白拿筆桿都有輕飄之感,慢說拿槍桿也。
●毛比周恩來「毒辣」。毛或有殺周之心,而周斷無篡毛之念。「無毒不丈夫」,周總理太謙和了。
●毛比林彪更「奸詐」。林在黨內有奸詐之名,視毛則瞠乎後矣。林為孫悟空,毛則如來佛也
●毛比鄧小平「高大」。毛是漢高祖,鄧則是搞「非劉氏不王」的蕭曹二相國和周太尉的綜合體。……〈閱讀全文〉
▼顧維鈞/摘自《書緣與人緣》之〈廣陵散從此絕矣——敬悼顧維鈞先生〉
顧少川(顧維鈞)那時在冠蓋如雲的華盛頓外交圈中,是一位最年輕、最漂亮,可能也是最有風度、最有才華、最有學問的外交官,更是白宮主人早期的忘年之交、英雄識英雄的「老朋友」——真是出盡鋒頭,雖然他所代表的國家卻是當時列強的一個最老大、最腐朽、最貧困、最愚弱的「次殖民地」。
在此三數年前,一位哥大的東方學生威靈頓.顧(顧氏的洋名字)曾率領了一個哥大辯論團,遠征普林斯頓大學,擊敗該校的辯論團之後,由普林斯頓校長烏德奴.威爾遜,在官邸歡宴,賓主盡歡,相約「再見」。又有誰知道,數年之後,彼此真的「再見」了。「再見」之時,彼此都穿上大禮服,一位是美國的大總統,另一位則是古老中國的「欽差大臣」呢。
……他是世界上的第一流外交幹才、舉世聞名的國際政治家。但是他搞的卻是個「弱國外交」——他個人在外交界所代表的份量,往往超過他所代表的政府。檢討起來顧氏一生的成就,讀歷史的人,或許會惋惜他「事非其主」,為其才華抱不平。
「辦外交,不比打仗,」顧氏心平氣和的告訴我這位後輩,「打仗有百分之百的勝利,也有無條件投降。辦外交能辦到百分之七十的成功,就是最大的勝利了……,哪有百分之百的勝利?!」
這是顧先生辦五十年弱國外交的肺腑之言。五十年中凡他所經辦的外交事件,多半可說是百分之七十的成功吧——至少他沒有喪權辱國,在國際上丟人現眼。
他曾替「軍閥政府」服務,遭到國民政府的「通緝」(這點顧氏一直向我否認)。他也替國民政府當過外交部長、當過大使,而被共產黨宣佈為「戰犯」。但據我所知,他老人家晚年卻有好幾位北京駐外大使的訪客,他老人家也是他們的非正式的顧問和教師呢。
顧先生的才華真是國內國外,一時無兩。他是位功不可沒的愛國外交官。他本身傳記便是現代中國的一部外交史。緬念先賢,我想像顧先生這樣的才華和功業的巨人,他一死只可說是「廣陵散從此絕矣!」對一個教外交史的教師來說,顧先生在現代外交史上,實在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海外讀紅樓/摘自《史學與紅學》
傳統「白話小說」不特語言之使用有其必然性,其文章體裁發展之規律亦隱然可見。滿清末季之章回小說多至一千六百餘部,然就西方文學標準看來,除《紅樓》、《水滸》等數種之外,幾無可讀之篇。吾友夏志清教授熟讀洋書,以夷變夏,便以中國白話小說藝術成就之「低劣」為可恥(見夏著一九六七出版英文《中國古典小說史》導論),並遍引周作人、俞平伯、胡適之明言暗喻,以稱頌「西洋小說態度的嚴肅與技巧的優異」。
志清並更進而申之,認為「除非我們把它(按指中國白話小說)與西洋小說相比,我們將無法給予中國小說完全公正的評斷……一切非西洋傳統的小說,在中國的相形之下都微不足道……我們不應指望中國的白話小說以卑微的口述出身,能迎合現代高格調的口味……」(見夏著前篇中文版)
此一論調,實為「五四」前後,我國傳統文明轉入西化的「過渡時代」,一般青年留學生,不論左右,均沉迷西學、失去自信、妄自菲薄的文化心態之延續——只是志清讀書滿箱,西學較為成熟,立論亦較當年浮薄少年更為精湛,其言亦甚辯而已。然其基本上不相信,由於社會經濟之變動,我國之「聽的小說」亦可向「看的小說」方向發展,如《紅樓》者,自可獨創其中國風格;而只一味堅信,非崇洋西化不為功之態度則一也。
志清昆仲在海外文學批評界之崛起,正值大陸上由「批胡(適)」、「反胡(風)」、「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雷厲風行之時,結果「極左」成風,人頭滾滾;海外受激成變,適反其道而行之——由崇胡(適)、走資、崇洋而極右。乘此海風而治極右「時文」,適足與大陸上極左之教條相頡頏,因形成近百年來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兩極分化」之局。
此一「兩極分化」之可悲者,則為雙方均否定傳統、爭販舶來而互相詆辱,兩不相讓。可悲之至者,則為彼此均對對方之論點與底牌,初無所知,亦不屑一顧,只是死不交通,以為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