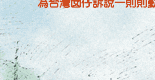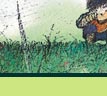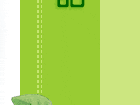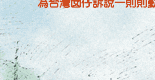我借居的這條巷子,有一棵六層樓高的玉蘭,真是巍峨嶔崎。生活在這樣一個高度商業化的市區,一入巷子,令人無法不看到它的存在。在我眼裡它何止可觀,它是這條巷子的精神所在。
 每年春天,花開時節整條巷子都香,二、三月起香息一日盛過一日,逐漸攀上高峰,它會一直香到七月。多麼富麗,城市商圈裡的季節感,春風散以花香,竟有這等排場。我每回在巷子裡進出,不經意間,總要因於空氣中浮盪的某些因子,心起震動。季節與時序,當設計師沸沸揚揚於,城市應如何對抗單調、同質化與標準化的設計觀時,其中有一個最為簡單、自然,卻深深影響個中的因子,那就是栽植。 每年春天,花開時節整條巷子都香,二、三月起香息一日盛過一日,逐漸攀上高峰,它會一直香到七月。多麼富麗,城市商圈裡的季節感,春風散以花香,竟有這等排場。我每回在巷子裡進出,不經意間,總要因於空氣中浮盪的某些因子,心起震動。季節與時序,當設計師沸沸揚揚於,城市應如何對抗單調、同質化與標準化的設計觀時,其中有一個最為簡單、自然,卻深深影響個中的因子,那就是栽植。
以一株玉蘭作為市廛生活的銘記
我住五樓,站在陽臺猶無法看到它的冠頂,但花香若有似無,陣陣縈繞不絕。我探首從巷子這頭遙遙望向那頭,心底不免發出驚讚,一株玉蘭如此高聳,立在此巷,它的年歲,怕比這兒來來去去的某些居民,都要悠長許多。春夏之際巷裡進出,循著花香回到住處,總期願有人和我一樣,以此做為市廛生活的銘記。喧嚷塵囂,市井巷道並不枯索,只因為有這一株玉蘭,不勞費心,日子也能燦然,自有雨潤花香。
然而某一日出門,它忽然消失了。
我幾疑自己弄錯了巷子。毀屍滅跡也要有個過程。
一株六層樓高的玉蘭,怎麼可能憑空消失,我走著這麼真實的場景,但它就是比虛幻還要虛幻。一如武陵人失落了桃花源一樣,我在里巷裡失落了一株玉蘭,竟連絲毫形跡也無。武陵人尋向所誌,一株恁大的玉蘭,從此在都市裡遂迷不復得見。
以一株青楓表彰安居定住的年歲
之前我住木柵,一個臨山的小社區。社區裡有新、舊公寓,也有獨門獨棟的別墅。花木扶疏的里巷人家,老住戶門前有齊樓高的青松與緋紅櫻;新住戶也不遑多讓,花臺、篷架滿蔭蔥翠。黃蟬、紫籐、青松、茉莉、紅櫻各有次第,植物本身就是門牌,註記著一種風格,表彰著各家各戶在此安居定住的年歲。
那時我住三樓。一樓人家通常都有個令人欣羨的院子,一戶人家在院裡安置了涼傘與戶外桌椅,很有閒逸風情。我雖是局外人,但是他們所營造的氛圍也滋養我的眼目,一方小小的美麗亦令人心領神授。
一日那家院裡,忽然植了一株青楓,一人多高,樹幹粗如手臂,一樹星星一樣的掌狀葉片,在風裡閃著星芒,美麗極了。我也忘了如何得知,那樣大的一株青楓是花市裡二萬元買的。但是它連一個寒暑也沒有過完,就慘遭連根拔棄。好端端的竟陳屍巷邊,不是因為年荒苦旱,而是因為失寵見捐。
這麼大的一棵樹呀!那情狀幾和殺生一樣慘烈。
我忍不住問了,好好的一棵樹,為什麼買了又要連根清除呢?
「因為每天都要掃落葉,好麻煩呀!」
那理由真是令我無語,啞然竟不能多置一詞。我輕輕「噢!」了一聲,有不落葉的樹嗎?
這讓我想起一年秋天,我在京都,那時節銀杏轉黃楓葉紅。置身於以銀杏為主的街道,一地秋黃,漫天飛金,走著走著,我幾疑自己也有萬道光華。每天下午一到四點,只見戶戶商家皆拿著竹耙子,在街道上把黃葉攏成金堆。無論行到哪兒,這時地上都是絲絲掃痕。生活的整飭,季節的莊正,不就在這樣的變易裡觀其一瞬與無盡嗎?
砍樹的人都有千百種理由,義正詞嚴。蔽蔭、美觀、造景、建築……一切不過為人役用,面對樹的存活既沒那麼迫切,科技萬能也早有取代之物,人為掛帥的時候,物種的聲音其實微弱得很。
環境倫理談了很多年,焚琴煮鶴,大片的綠早就蕩然無存,而今,我們還會在乎那小片的綠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