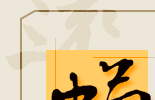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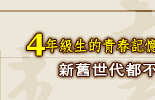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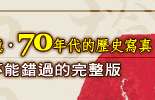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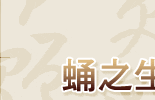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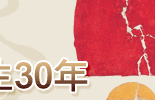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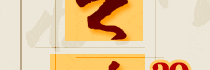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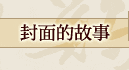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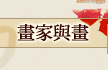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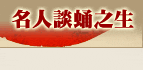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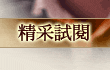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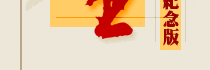 |
 |
| 「蛹之生」是小野的成名作,這個中篇自去年六十三年八月在中副開始連載後,立刻引起青年讀者們廣泛的討論和整個文壇的注意。何以至此?誠如以「新種的蝴蝶」為題,寫「蛹之生」讀後感的作者嵐哉致中副編者的信中所說:「許許多多的問題和看法,都是一般青年人積在心中許久許久的感情,都被作者冷靜的寫出來了。」這話可最是搔著了癢處。
事實上,通過文學評論嚴格的眼光來看小野的作品,也應該有其相當高的評價。我是「蛹之生」的第一個讀者,願在此述說一點個人的感想。 這篇小說,通篇節奏明朗,進行的速度輕快,開始就有一股引力把讀者吸住,使你非看下去不可。在小說的創作技巧上,作者顯然把握了先決的竅要。 書中人物的塑造,忠實而自然,不掩飾人性的弱點,不特別誇張各有的特性,倒是很著重心理上一層的描繪。因此使每一人物,都能給予讀者鮮活的印象,這些小說中的人物,就是現實的身邊人物。 其中貫串全的兩個年輕人,其一是「那個穿白上衣、黃卡其褲、塊頭很大但顯得有些邋遢的男孩。」他叫秦泉,讀政大中文系。另一是「留著平頭」,「高高瘦瘦,穿著藍條襯衫」的趙一風,讀師大生物系。故事從這兩個年輕人在北上的火車廂萍水相逢認識開始。 最突出的是秦泉,又狂又偏激,賦性率直而好打抱不平,熱情如火,真愛真恨,能寫一手好文章,也經常表現粗獷的一面,這粗獷的一面,正刻劃著他具有強烈的正義感和道德勇氣。至於趙一風,做事熱情,頭腦冷靜;表現出色,態度謙虛,是一個思想較早熟的青年人。他非常關心國事,曾熱心參加學生區黨部的委員競選,他認為「這樣可以使他更直接的替國家出一份微薄的力量」,所以「他暗暗告訴自己,這回一定要好好的幹,幹出一番成績來讓那些曾稱『黨棍』的人瞧一瞧。」他是全書的中心關鍵人物,許多影像,都來自他的輻射;許多重要觀念表達,都出自他的對白中。 另外的人物,如內熱外冷意志力十分堅毅的吳霜;有先天憂鬱感的藝術系高材生馮青青;癡情的楊祖業和天真純潔的楊小蘭兄妹;辯才無礙的白熙鳳;還有認真讀書的吳小強,也都各有不同的造型和個性,在整篇小說的比重都佔有很大的份量。 關於故事的結構。是以上述這幾個大學生的交往、戀愛、追求新知、社團活動和政治參與等組合起來的。忠實純樸,洋溢著人類最高貴的愛心。它的發展,順當而一氣呵成,從頭到尾,使人關心、使人感動、甚至使人拍桌子。尤其是其中兩個悲劇人物,一個秦泉,一個馮青青,作者對他們個人結局的安排,我想是費了一番苦心的。否則不會給讀者精神上天許多負擔,當然,這點負擔是讀者心甘情願去負擔的。 看完之後,我對這一代的青年人似乎充滿許多歉意。相信這篇小說不僅對青年讀者會有「會心不遠,自己正在書中」的感受,同時我認為也可供青年領導階層作為今後正確導航的參考。今日的大學生,固然有一部份萎靡不振,甚或徬徨失落,但大多數還是積極向上。有其尊嚴與對時代的責任感。讀完「蛹之生」,更能證明這一代的青年人,和開國時代、「五四時代」、北伐時代、抗戰時代的青年人一樣可愛、一樣勇敢、一樣有崇高的理想與抱負,一樣具有自我奉獻的精神。我們也更有理由相信,這一代的青年正是我們國家最堅強的復興力量。 這本選集另外十四個短篇創作,如「家教這一行」、「光棍船」、「周的眼淚」、「夜梟」、「長髮先生外傳」、「網」、「遺傳」、「笛、沙鷗」等八大篇,大都還是以當前大專青年生活為題材,但各有不同的主題與趣味。至於「財迷」、「第六個兒子」、「陳嫂的煩惱」、「紅門內的芭樂樹」、「白沙灣的驟雨」、「大義滅親記」等六篇,卻是已經部份或全部脫離作者原有的生活圈,而進入到社會人生和國是問題中去了。它雖然只是幾個小故事,然而作者的態度非常認真,彼端尤其揮灑著豐富的感情與文采,我們不難從這些作品中,窺測到作者對創作生活的熱愛及其潛力…… |
 |
| 六十三年一年中,常在中副上看到他的作品,但,今年來,幾乎完全「息文斂字」。他的名字仍然常可看到,卻是移到中副底下的文化廣告攔:「蛹之生」初版預約、再版預約……不到半年,竟然六版了。
身為一個讀者,我很高興「蛹之生」暢銷;同為一個投稿者,我更樂於知道「蛹之生」能廣受歡迎。雖然,小野的這本集子裏,十五篇小說不見得篇篇佳作,其中有一小部份筆法也很平俗。但是,他始終保持著正直熱忱的立場去寫。不是風花雪月,不是鴛鴦蝴蝶,更沒有誨淫誨盜無病呻吟。有的只是對生命的尊重、對人類的熱愛。一本有益青年學子的青年小說集能「叫座」到這種程度,這是我國近年來少見的。 小野的文章,幾乎篇篇都有「教化世人」的意味,而且十之七八與生物學有關。這,也許因為他是學教育,又是學生物學的,因此「不離本行」。不過,他「教化」時,並沒有像蕭毅虹那樣,把義理明顯的行之於文字──請別誤會,我並不是比較誰高誰低,個人筆調不同、各有長處。蕭毅虹在中副的「狂者魯彥」、在書評書目的評論文章、在時報的「一張舊報紙」等,都是令人激賞的作品。 小野時常把自己的見解,溶於文章中,表達在自裏行間。像「家教這一行」,寫外號「吃角子老虎」的家教中心老板;寫求家教職務的大學生,如同「難民潮爭奪救濟麵包」;還有家長要求應徵者拿證件「驗明正身」;學生呢,言語「海派」、穿著大膽,不過,在聽家庭教師的一番話之後,終於把唱機的音量轉小了。 「光棍船」這一篇,是以假想的船載著幾個大學生真實的感情生活 「禾仔,你以為愛情一定要轟轟烈烈而驚天動地嗎?要飽受波折才是真愛嗎?」 「周的眼淚」和「夜梟」寫大學生的「分數主義」,雖然離不了「怎麼栽培怎麼收穫」、「夜路走多必逢鬼」的結局,但是,寫的方法與內容則是前所未見的。沒有廢話、沒有贅語,一路發展下去,結果令人沉痛。 「第六個兒子」更使人感到慘然,「誨教兒子覓洋學位」的典型故事。一位老者,五個兒子都出去了,第六個「兒子」竟是一個海棉枕頭,當老人心臟病發作時,這枕頭是最好的依靠,當老人死時,枕頭在他胸口,醫生竟想起「不孝男隨侍在側親視含殮」這種句子。這一篇,諷刺意味極深,但是並不尖酸刻薄。小野很用心的去刻畫老者、刻畫那黃昏暮色,一株葉子落光的灌木、一張要垮不垮的椅子、一台舊的黑白電視、古鐘、夢中的老黃狗等等,無一不烘托那老境的淒涼。 小野曾經嘗試改變筆法。有成功,但也有失敗的。「長髮先生外傳」、「陳嫂的煩惱」寫的較差,「長」文,寫一個失落的青年錯誤的觀點,雖然傳神,但是不可取。「陳嫂」一文,將知識青年的口語裝到一個老女傭的嘴上,一點也不符合。 「白沙灣的驟雨」,把整個中國近代的苦難,縮影在一個海灘上弄潮人群中表達出來,十分著力。但是,閱讀者若不能仔細閱讀,則無法體會出那幅淒慘苦?的畫面,文中許多譬喻,非常貼切。篇首引用老子道德經的「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點出了宗旨──我們國家所遭受的苦難,不會是永遠的。 「笛、沙鷗」這一篇,也是要細細品味。論故事,很簡單,但是意境則深遠。 「雖然我不信神,可是我也從不敢對科學抱太樂觀的態度。人類常想藉著高超的智慧來駕馭自然,可是卻常常迷失了自己,這種犧牲未免太大。」 他們看沙鷗飛向永遠在延伸的地平線;在夜裡聽笛音,在笛聲中,心靈經過一番蛻變洗滌,而嗅到生命之泉的芬芳。然後,孟天爵回都市中,得知自己原先以為成功的實驗,其實是過程錯誤造成的誤解,根本沒有成功,但是,他並不傷心,因為他看過海鷗一直向地平線飛去,因為他夜半聽過那震撼心弦的笛音,全篇文章,著重在「聞笛」,描寫得相當細膩。 「網」和「蛹之生」在中副登載後,曾引起很多人共鳴。小野很能寫出一些令人回味不已的句子。「網」一文中也有許多。如: 「Love 在網球的計分上就是零的意思。」 從文中的句子,可以看出小野寫這篇文章時,相當用心。他自己在後記中說,這一篇經過五個月的時間才拿出來,萬餘字的短篇小說,如此謹慎,無怪乎「網」會繼「周的眼淚」再度入選中副選集。 「蛹之生」是中篇小說,小野安排了許多角色反映這個時代大學生的思想,雖然角度不夠廣闊,但是充滿了青年的熱忱。如: 「我覺得還是多充實自己、多唸點書,才有資格講話。並不是唸了幾本沙特或卡繆就可以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小野還特地借文中人物──趙一風的解悟指出:當前有些大學生的錯誤觀點,以為參予政事是「為名為利」。 趙一風很沉痛的感懷:「除了用事實來證明自己的理想和抱負外,其他一切冠冕堂皇的清談都是不可靠的。」 小野以蛹的蛻化來譬喻一個人由少不更事到青年、成家立業。有的蛹會羽化成瑰麗的彩蝶,有的蛹則成為又醜又髒的蛾!人,又何嘗不是如此?這個譬喻很貼切,而且也是前人所未有的。 他在文中說:「蛹之生,它象徵了一種突破,充滿了無限希望和生機的突破!」 (蛹之生第七版代序/書評書目三十一期) |
| 蛹之生30年│小野印象│徵文活動│延伸閱讀│我要購買/回首頁 |